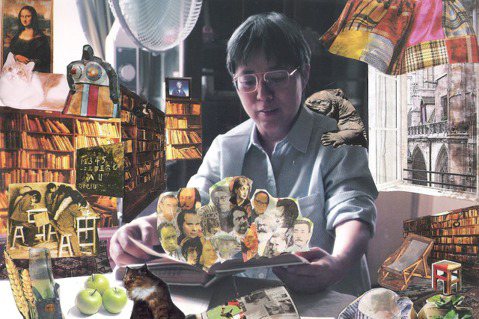反服貿的歷史定位:「民主/抗中」成為互為表裡的主框架

太陽花運動的十年之際,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拋出「重啟服貿」議題,並主張其「只反黑箱,不反服貿」,而引發該黨支持者以及網路輿論對於歷史事件的片面理解與錯誤詮釋。
任何社會運動與集體事件,尤其是動員規模越大、議題性質越複雜,就會有不同的立場與光譜;太陽花運動的參與者及貢獻者,原本就具有多元異質性。本文不著墨於特定個人的立場,也無法窮盡所有想法;而是企圖澄清「兩岸服貿協議」的倡議策略兼容著「民主程序」與「中國因素」的內涵,加上十幾年前有著長期關注各議題的社運組織與青年學生的動員操練,從而成就了這場「框架整合」的社會運動。
如何評價太陽花運動?分析數據與文本,驗證理論與洞察
本文所界定的「團結」的意義,除了既有網絡內組織的緊密凝聚之外,也帶有擴大範疇的包容性。從反服貿運動的構框本身帶有不同訴求層次切入,包括「中國因素」、「反黑箱」作為當時民意較高度支持的內涵,而能夠容納獨派組織和以公民意識為主訴求的新興網路組織。
「民主/反黑箱」議題框架整合了以往關於台灣認同或統獨意識形態不同調性的社運組織,尤其是獨派團體對於「抗中」與「中國因素」的強調。就此而言,太陽花運動之框架擴張的作用相當明顯,它至少整合了民主防衛、社會認同(階級與性別等議題)、與中國因素等原先分屬不同抗爭議題領域的組織,而同時擴大了認同的範圍與深度。
這個框架涵容了更多組織的過程,是從過去幾年內的社會運動與抗爭當中逐漸萌芽醞釀而成型,直到佔領爆發時才能夠作為促成團結的條件。
——《台灣社會學》第38期頁64
2019年,我跟吳介民、李宗棠、施懿倫等共同作者在《台灣社會學》發表了一篇研究論文,使用自建的資料庫進行量化的社會網絡分析,並以59名學生運動領袖及社運組織幹部的深度訪談,爬梳太陽花運動(作為台灣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何以能夠促成在豐富意義上的「社運團結」。所謂團結,我們以量化科學的方式去測量當時組織層面的結盟凝聚力高低;也從理論觀點去分析抗爭相關的公開文本及匿名受訪者的證詞,來理解「框架」(frame)及情感扮演的作用。
做研究,從數字圖表來確證現象,從大量文本做詮釋推演,就為了嚴肅看待一場人人都能說上幾句的集體行動,究竟具備什麼樣的價值與意義。當年,我們嘗試回答這個問題:該如何理解「太陽花運動」置身於抗爭風潮的意義及價值?而這一份嘗試盡可能嚴謹論證,並受到許多人的幫助與貢獻得出的研究洞察,與今日人們所談論的反服貿,有什麼對話的可能嗎?

民主跟抗中一樣重要,在「反服貿」之中「互為表裡」
反黑箱,並不是反服貿的擋箭牌,而是以2014年3月立法院佔領運動為代表的「社運團結」的框架整合之鑰。程序性訴求,何以在反服貿運動中佔有一席之地?因為當時反服貿運動主要的論述、組織及動員方,認為「民主」跟「抗中」一樣重要。即使當時的行動者不直接使用「抗中」這個詞彙,但對於「中國因素」的戒慎已經浮現,社運組織在當時對於「中國因素」這個概念的使用,實際上是相當謹慎,絕非逢中必反。
當時的訴求,不只是逐條審查、反黑箱,還有捍衛民主。這個「民主」的內涵,即使單單放回2014年的脈絡,都絕對不是「審查服貿協議的時候,要直播,要逐條審查,要公開會議紀錄」此類今日能輕易淺談的「反黑箱」而已,而是:在訴求中強調「民主」的同時,也同時對照出,簽署貿易協定的「中國」是一個「不民主」的政體。
當然,並非所有組織都向著中國政府訴求,更有青年團體、社運團體主要省思「自由貿易」對勞工的衝擊;然而,他們也沒辦法繞過「中國因素」此一重要影響。為什麼「反服貿」可以讓各種意識形態光譜的人參與進來?就因為服貿本身涉及到的利益影響層面是如此多元而巨大。「反服貿」議題發展本身,豐富了運動不同層次的訴求
反黑箱,是反對「受衝擊業者的被排除、被犧牲」
抗爭布條,也是大家最主要喊著的口號,是「退回服貿,捍衛民主」。事實上,在當時的語境中,「退回服貿」本身即能涵容相當大的訴求範圍。因為那既指涉到我們貿易協定的交往對象,是一個不關注服務業者勞動權益,也不關注任何民主人權的中國政體;也指涉台灣自身的服務業從業人員,可能受到特定資本主導而損害的工作權及生存權,以及媒體出版業可能受到與中國簽訂協約而損害言論自由等諸多衍生影響。
人們想像一個民主國家應當要先做衝擊評估,想像人民應該受到政府的保護,無論是經濟層面,或政治層面;尤其當時已經有許多例證指出中國「以商逼政」、「以經促統」的威脅。所以,退回服貿,才會指涉當時的代議士與台灣政府,輕視公共利益,輕視(在台灣從來不理所當然擁有的)民主程序。
無論上述的「指涉」之間,各佔了行動者多少比例,前後有什麼樣的變化。在太陽花運動當時運動的語境裡,人們簡稱,這叫做「反黑箱」。

回到歷史現場:反服貿的開始,就是「獨派與進步價值的合作」
反服貿運動初期,也就是2013年,被歸類為獨派組織的「台灣教授協會」原本要獨自舉辦抗爭活動,但在活動之前,得知賴中強律師將串連社運組織組成「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並舉辦晚會,便在活動前安排認識彼此的場合並溝通運動訴求。當時,「台灣教授協會」訴求是希望直接就將服貿「退回中國」,而「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作為眾多社運組織的聯盟,認為策略上應該以程序性訴求「逐條審查」為優先。
雙方確認了彼此大方向的訴求一致,具有整合意識的「台灣教授協會」組織者擔心外界因此產生不同團體之間打對台的印象,便決定配合整體聯盟的運動訴求,加入以包含了性別、環境、勞工、人權等進步性社會議題組織所組成的「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作為串連的樞紐,在擴大結盟的過程中,提供了社運組織社群的集體行動平台,並在2014年與學生團體、青年與更多的台灣公民共構了太陽花佔領運動,使得「民主/抗中」這個主框架得以「動起來」。
反服貿運動幹部:「沒有公開講台獨,但他對台灣的想像其實是一樣的」
服貿爭議所牽涉的中國議題,是倡議台灣獨立的獨派組織所關懷。從前,獨派組織與一般關心社會上各面向議題的社運組織之間,合作與互動的場合較少。然而,太陽花運動前幾年已有幾波中國因素相關的抗爭,議題性質相互緊扣;即有獨派組織意識到多元串連、加強合作的重要性,並認為許多社運組織只是「沒有公開講台獨,但他對台灣的想像其實是一樣的,不應該因為他沒有公開喊台獨,就不願意跟他合作」。
確實,我們的研究中59名不同身份的受訪者之中,有不少太陽花運動的成員都提到了對中國影響力滲透台灣民主的憂慮,並認為「中國因素」是發動大規模動員的一個重要因素,畢竟國民黨政府簽署服貿協議的對象是中國政府,也就是中共政權。
無論是回到那個百花齊放的歷史現場,或從今日的資料與證詞去爬梳,都能夠指出:無論是從2013年的反服貿運動源頭去檢視,或從2014年的立法院佔領起算,這些事件的內涵,都不只是今日2023年語境的「反黑箱」。

還不該被遺忘的十年:現在,守護的是什麼,反的又是什麼?
澄清了「退回服貿」在當時的意義;理解了「守護民主」作為運動動員之檯面論述上主框架的一個元素,能夠容納台獨意識與主權論者的需求,是反服貿運動至佔領行動中不同次群體能夠整合運作的一個關鍵。之後,再到了今天,「反服貿」意味著什麼?「民主」又意味著什麼?經歷代代跌撞而持續漂浮的符號「公平正義」又意味著什麼?研究以外,這是不同世代、仍在乎台灣的人們,仍值得省思的問題。
反服貿促成了一場解嚴以來最大規模的社運動員,百花齊放同時具有一定程度的共識及團結。那年,太陽花運動受到世界各地的聲援,包括參與獨立廣場革命的烏克蘭民眾;以「太陽花」命名雖然是一場意外,卻與烏克蘭的國花「向日葵」有所呼應,兩國處境在多年以後因為地緣政治及戰爭風險,而被國際視野所並列。
那時候,人們不乏對「大台」(握有運動話語權、決策權的人或團體)的批判,卻也多能找到自己的戰鬥位置,進步陣營結盟而讓「民主/抗中」成為互為表裡的主框架,還有更多價值的實踐與實驗,人們談論的是平等、自由的在制度層面的落實與深化,性別、階級與環境的正義,以及參與集體事務的組織實作與個人解放,以及更多的未竟。這些,都還遠遠不該被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