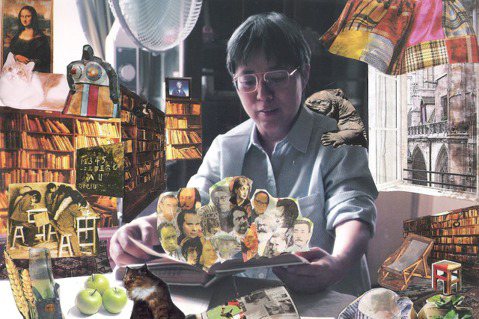《閣樓上的秘密》:在納粹集中營「灰色地帶」裡最美好的愛情故事

紀錄片《閣樓上的秘密》的導演馬格努斯・格騰在今年台灣國際女性影展的專訪中提到,電影裡使用了三種檔案影像:第一種是新聞影像;第二種是紀錄片主角的外婆奈莉(Nelly)與外婆的愛人訥亭(Nadine)在戰後拍的八毫米(mm)底片;第三種則是「詩意的檔案影像」,取自紀錄片大師亨利.斯托克(Henri Storck)所拍攝的紀錄片,據稱那是「為了拍攝,必須與比利時的納粹政府達成某種協議。因此存在著某種黑暗、詭譎神秘的氛圍,我們就加以運用,來配合日記的內容。」從生還者後代的閣樓出發尋索、相遇,以及三種檔案影像勾勒出來的真實故事加總,使《閣樓上的秘密》有非看不可的價值。
讓人想暫停、抄寫字幕的集中營日記
有幸先拿到試片連結的我,在第二次看《閣樓上的秘密》時,按下許多次暫停鍵,在第三種「詩意的檔案影像」停留。因為這些影像搭配的是紀錄片主角的外婆奈莉在集中營撰寫的日記內容,而那些內容的觸目驚心與柔情動人,足夠使人屏息,足夠使人感覺到單單是字幕上的文字本身即意義巨大。我按下暫停,抄寫下每一次電影引用到的奈莉日記,也抄寫了受訪者轉述訥亭在集中營瀕死時的自序。我認為,單單剪取這些日記內容與詩意的檔案影像,已經構成一部具有意義的電影。
在《閣樓上的秘密》裡所引用的日記段落,我們能看到集中營裡面,竟然也有著迸發愛戀而使人喜悅興奮的場景,而且是同性之間的,跨文化之間的愛情。搭配著詩意的影像,那些日記內容也仿若詩一般有著稠密的情感與意涵。
1944年聖誕節下雪了,天空就像聖誕禮物一樣美麗,圍住集中營的鐵絲網都像撒了糖粉。營裡放了聖誕樹迎接我們,樹上有銀紙裝飾。地板剛清洗過,火爐裡也難得傳出劈啪聲響。這是1944年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的聖誕節。我和法籍女囚一起去唱聖誕頌歌,就像是古時到城裡吟唱的吟遊詩人。我唱了〈聖誕頌〉、〈聖嬰誕生〉和〈聖夜〉,人群裡忽然有個聲音吶喊「唱《蝴蝶夫人》的歌吧」有何不可呢?我唱了《美好的一天》。情感在我皮膚上竄流,我感覺眼眶發熱,喜悅佔據我全身,有如酒醉般的喜悅。掌聲響起,一雙手臂抱著我,還在我臉上親了兩下。蝴蝶夫人就在我面前。她有著黑髮、鳳眼、汝白的皮膚,她叫訥亭。她說「老天今晚對我們很好」

同樣是奈莉在片中受引用的日記裡,有著集中營倖存者經常在口述記憶時經常提及的場景,如普利摩・李維《滅頂與生還》所述「幾乎無一例外地,我們記憶的起點總是從火車啟動駛向不明目的地開始,一方面是因為時間先後順序,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那些原本無害的普通貨車車廂,為了服務不尋常目的,成為莫名的暴力工具。」那就是納粹士兵殘酷而反人性的運送場景。然而,對奈莉而言還有一個痛徹心扉,因為只有她從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被移送至毛特豪森集中營。這段旅途分離了奈莉與訥亭。
1945年2月25日,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我被關進運牲畜的車廂裡,天快黑了,我很害怕。訥亭應該在吃麵包,她很常跟我分著吃。我還會再見到她嗎?車門關了,火車開了,黑暗中,80個身軀在車廂地板相互緊靠,所有人擠在一起,我動彈不得。一個緊挨著我的女人患有痢疾,身上散發惡臭,整整五天五夜後,我們在陰沈的車站下了車。毛特豪森集中營。士兵拖出車裡的屍體,在月台上排列。死了17個女人,還有一個嬰兒出生。
奈莉的日記裡,有集中營慘絕人寰的描寫,卻也有著比較反直觀的、帶有浪漫情感的句子,描寫著她在集中營與訥亭的相遇與相愛。這種「詭譎神秘的氛圍」無疑適合導演所選取的檔案影像素材,也讓人想起普利摩・李維《滅頂與生還》描寫集中營的「灰色地帶」:除了以被害者與加害者來區分人類,滅頂者與生還者之外,還有許多難以定義的地帶,人性還有許多複雜且難以簡化言說的樣貌。

灰色地帶:生還者、性少數,以及人性處境的光譜
聲樂家「奈莉」與名媛「訥亭」(Nelly & Nadine)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的相遇與相愛的故事,也是其中一個「抗拒簡化」的故事,呈現了特定的人類生存處境與親密關係故事。這場愛情則是另一種「灰色」地帶:從集中營生還的同志身份,以及其後兩人般到委內瑞拉生活數十年的非典家庭實作。觀眾如我,在接收這樣的集中營事實所帶來的衝擊時,也確實地受到了這則女同志愛情故事的震懾與感動。
1945年1月10日,拉文斯布呂克我從礦場工作回來,非常疲倦,腳都軟了。我等等要與訥亭見面。我愛上她了。我習慣以目光搜尋她白頭巾下的黑髮,當我們四目交接,她的眼神發亮。我爬上你在第三層的床,上鋪居然只有你一個人,這在集中營裡很難得。我們半躺半枕著手,就這麼交談,我聊童年、祖母的花園,聊音樂和我開過的演唱會。你聊中國,聊北京飯店,說有多麼富麗堂皇,你也聊到和娜塔莉巴尼和她的沙龍。你會訂下奇特的計畫,像是度過美妙的一晚歸來後,還有香檳和魚子醬等著我們。這讓我笑了。這天,朦朧天空投射出珍珠般的光芒,照在營裡,顯得很不真實。做夢的感覺非常強烈。我等著醒來的那刻。有天若能回歸原本的生活,我會再回視這夜,再想到你,訥亭,我枕著你的手臂,感覺到條紋制服中的手臂日漸消瘦。訥亭,我們真能長廂廝守嗎?

光芒的美,似乎是不真實的夢,在這裡的「做夢」,卻是指涉現實的集中營惡夢,所以接到下一句是「回歸原本的生活」。場景之美對映現實的殘酷,貴為「夢想」卻只是生還。這些愛情詩句所跨場景、反直觀甚至表面上矛盾的意思,凸顯了真實。
奈莉被移送到毛特豪森集中營時,爬了186階沿山鑿入的巨大階梯,她描述「下去是採石場,也是我們的墳墓」並探問「如何找到活下去的勇氣」,也仍在內心呼救著訥亭「你在哪裡?之前幫助我活下去的是你」;並在另一篇「死亡佔了上風」的日記開頭,仍寫著「我用盡力氣喚出有你的記憶」、「等我,我一定得再見你」。
紀錄片也找到訥亭的友人轉述,說訥亭曾被迫卸下火車的貨、背著貨走,路程累人又寒冷,她暈眩而倒地,如果被發現的話就會被殺掉:「她聽到『喀拉』一聲,她說在那一刻,『我想到生命裡所有快樂的時光,幸福的每個瞬間,接著意識到我還是能夠擁有這些。就是這個信念支撐我站起來,背著貨繼續前進。』」受訪者說她們兩人之間的友誼令人敬佩,「因為看得出來她們兩個之間,有我無法解釋的東西。」
這是真正的,出生入死的愛情故事。那「無法解釋的東西」是集中營中生死扶持的分食麵包;是集中營第三層床鋪的談天與共枕入眠;是在狀況還未全面惡化時曾擁有過的聖誕樂曲,更是堅定的情感。而在那個她們還須以「表姊妹」作為同居身份遮掩的時候,那無法解釋的,也是尚未被主流社會肯認的性傾向與伴侶身份。

「抗拒簡化」,呈現奈莉與訥亭的複雜性
電影裡的「第二種影像」,也就是訥亭所拍攝的八毫米底片,可以看到兩人逃離歐洲的戰爭陰影而移居委內瑞拉,陽光燦爛,充滿笑容,有些短片命名「卡拉卡斯的一天」,那是紀錄片中的家庭紀錄片。這些影像是《閣樓上的秘密》跟著奈莉的孫女席樂薇從家裡的閣樓翻找出來的。有著日常平實而美好的氛圍,如同所有情人與家人會拍攝的紀錄一樣,對照著她們共同經歷過的恐怖過去,這段情感更使人動容。
更可貴的或許是,《閣樓上的秘密》這部紀錄片本身亦保留了灰階敘事的複雜性。席樂薇說出她的母親並不喜歡奈莉(也就是她母親的母親)的情人,以及她因此搬到委內瑞拉的選擇;這可能是為什麼日記與底片檔案長達數十年的束之高閣。拍攝團隊也跟席樂薇一同拜訪美國女性主義作家瓊.申卡爾,而提到訥亭曾替一位在法國從事女同志沙龍的娜塔莉‧巴尼工作,據述也擔任她的情人之一,而那沙龍是帶有性解放活動的實踐。這場沙龍的存在與訴說,又更增進了我們對於當時性少數知識份子狀態的理解。
讓人膽戰心驚的一幕,是身為知識份子的瓊.申卡爾對著倖存者後代席樂薇說出「沒想過她們是情侶嗎?」的尖銳。鏡頭對著沈默的席樂薇,也使觀眾反思與想像這些素材公諸於世前,那些空白時光裡的壓抑與複雜性。影像有意識在抗拒簡化的誘惑。

訥亭與訥亭,透過生還者後代所見證的生命力
最後,我們才對主角席樂薇有更立體的認識,她看似是一個被動的素材保管者,被取消了行動的主動性。但電影也選取她一個頻繁出現的意象,也就是她所選擇的丈夫的田園(電影特別提到她從哲學家跟農夫之間,選擇了農夫)以及他飼養的動物,種種即使不是拍攝「人類」、「自己的後代」畫面,也都是以愛驅使的生之鏡頭。
接著,也是情感張力最高的一場戲,我們透過席樂薇與當年受到訥亭幫助的猶太人倖存者視訊,看見了「年輕的訥亭」。因為訥亭在從集中營獲救前的生死未卜時刻,對那位猶太倖存者說「如果你活下來,你女兒也活下來,如果你女兒以後也生了女兒,可以用我的名字命名嗎?」這段故事穿插著拍攝團隊多年研究的同一段集中營女子獲救影像。每個人的臉都有名字,某一位面孔中的後代,又生下了新的訥亭。
這竟然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看到這一幕時,我只能素樸地感激於我能夠知道有這樣重要的故事存在,感激於這些故事及影像透過電影而來到我的認知裡。在二戰集中營的悲劇之後,竟也有這段帶著浪漫且人性光環的故事,讓訥亭再次出現在我們眼前;而且還是以一種通常與「同志」(尤其在那個年代)無關的「傳宗接代」的意義上,我們看見了跨越戰爭與集中營,女兒所再生育的女性,以生還之喜悅所命名而活著的人。席樂薇掩面掉下眼淚說「是年輕的訥亭」,我們也透過電影,見證了具有生命力的訥亭與訥亭。
即使在屍臭環繞之中,在寒冷倒下之時,愛讓她們活下來。愛在那裡衝破了時間。我再次想到手抄下的電影字幕,奈莉的日記,她說牲畜的車廂,士兵拖出屍體,死了17個女人,但「還有一個嬰兒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