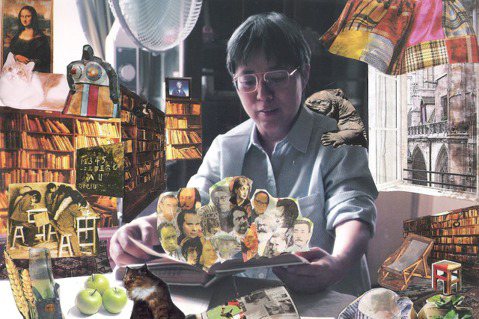女性、生死與藝術的交織:田中絹代《永恆的乳房》如何繞過疾病的隱喻

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隱喻》(1978)批判人們以特定的隱喻加諸於疾病,而使病人蒙受痛苦與污名,並解構著「很多人相信,癌症是一種激情匱乏的病,折磨著那些性壓抑的、克制的、無衝動的、無法表達憤怒的人」的二十多年前——田中絹代執導的《永恆的乳房》(乳房よ永遠なれ,1955)處理的疾病題材,已寫下日本電影史的重要一頁。
作為日本首部由女導演、女編劇製作的電影,《永恆的乳房》也是以乳癌為元素,卻早已繞過了後世如桑塔格筆下的諸多疑慮,冷靜而堅定地翻轉父權社會裡的乳癌隱喻。電影毫不猶豫地直直朝向其故事核心走去:女性、疾病(生死)與藝術的交織。
落入「情感壓抑導致癌症」的設定,卻凸顯癌後的解放
桑塔格的觀察相當精準:「根據癌症的神話,通常是對情感持續不斷的壓抑導致了癌症。」這也是《永恆的乳房》女主角(文子)的背景設定。文子有一段貌合神離的婚姻,無能的丈夫對她的詩歌興趣百般嘲諷,還趁她參與詩歌聚會時外遇舊情人;離婚後,丈夫把兒子帶走,只留給了女兒給文子,失去一個孩子的文子倍感哀傷,只能寄情於詩;從文子與友人對話之中,我們知道文子在大學時是充滿創造力的人,但是受到婚姻框架下的妻職與母職所壓抑。
離婚後,文子遭逢連番打擊,她不時掩著胸口,面露痛苦,裸露的乳房在電影中只有出現一刻,那就是手術台。術後文子與重病患者同房,病院環境的死亡氣息十分明顯,她的親友都覺得不適合讓小孩子來探望。
出乎觀眾意外的是,文子經過割除乳房的手術之後,在癌末病房的生活之中,才顯得神采奕奕,意志堅定。文子的詩作在罹病後終於獲得文壇肯定,但她對於遠從東京來北海道探望的記者,表現出十分堅定的抗拒,只因為那名記者提到了她的病危,彷彿要「唱衰」、要帶走她的生命力。

東京記者則不懈等待著與文子的會面,於是文子終於穿上義乳,謹慎會客,將自己的脆弱透漏出來:「我不要當女詩人,我要當個女人。」乳癌在一般意義上帶給女性的恐懼與摧殘莫過於此,文子也對其失去了乳房而感到自卑。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電影中,這樣的自卑情感僅透過這一場會面與短短幾句台詞表現出來,而不是角色表演出病後的肢體活動遮遮掩掩、面貌表情的喪志頹廢。不如說,反而是開場還在擔任人妻的文子,才是遮遮掩掩、對自己的詩作毫無自信、對命運帶來的挑戰感到喪志頹廢。喪失乳房以後,她無需肩負任何人命運,只要為自己活,文子說,她就是刻意要表現出有生氣、有活力的樣子,有意識地抗拒癌症所帶來的恐懼與死亡氣息。
所以電影裡,在手術及癌末住院之後,文子的舉措與談話活潑明亮,她的容貌美麗,這是電影作為敘事方法而能使得角色所象徵的意志充分表現。這種表現方式固然無法全盤還原病患的真實,因此,作品是否能夠以詩人、母親的角色鼓舞患者觀眾,還未可知,但這也無需是電影的意圖。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永恆的乳房》繞過了許多桑塔格所批判的、會使得患者及其家屬更加痛苦的隱喻神話,例如「癌症被認為是減退性慾的」以及「『憂鬱的婦女』比『樂觀的婦女』更容易患乳腺癌」云云。

從《阿吟大人》回看《永恆的乳房》兼具的傳統與前衛
桑塔格說,疾病常被用以象徵社會上的混亂與災難,而這種作法有著將複雜問題簡化的風險,但《永恆的乳房》未落入這種冒進的指涉。如果真要這樣做,確實也大可以把父權社會對於女性作家的打壓給帶進來,讓疾病指向對於父權社會的批判,結合若干社會動亂等事件。然而,在這部設定在北海道的故事中,主流社會中的符號只有一個,那就是刊登詩作、撰寫文子報導的東京男記者。這名東京男記者,是重新賦予文子生命力的人,淋漓盡致的愛情促成了情感故事的最高潮。
這裡我們又可以再注意一件事:無論是無能的前夫,或者執著而帥氣的東京男記者,他們的角色都是工具性的,電影相當聚焦在文子身上。(我對女性執導且電影主題聚焦於女性角色的電影之中,發生「理所當然且工具性地使用男性角色」的這件事相當著迷,因為那就是現今大多數電影對於女性角色的作法。詳細可參閱我去年為李美彌導演《未婚媽媽》所寫的文章。)東京男記者替文子帶來的東京文壇訊息、讀者支持以及情感關係,都是回到文子作為受探望病人、作家與女人的需求。
總之,帶有壓迫性的主流社會結構,未必要在女性作品之中被刻意指涉、被全盤批判與被推翻,而可能是賦予女性角色重生意味的契機。即使我們大概可以想像《永恆的乳房》劇情,在1955年的日本或已被視為反叛不羈,往後,田中絹代的作品其實還有更直接的表述:例如《阿吟大人》(お吟さま,1962)在劇情上,輕巧翻轉「宗教的神聖性」與「世俗的(愛情)神聖性」;角色上,領養子女與開明父母的設定,也輕巧挪開了父權;而主角的父親奉獻於茶道,茶道才又更體現了「信仰」,以這樣的真誠信仰來促成愛情的神聖,顛覆了有權者的想望,是相當工整的思想論述。
但在較早期的這部電影《永恆的乳房》之中,交疊著與傳統女性吻合的身體及愛情意象,也有「將失去乳房後的樣子袒露於閨蜜面前、坦承對其夫的愛戀」這樣前衛而突破性的場面;傳統價值與創造破壞之間,並非沒有共存的空間。作者在當時未必有這樣的創作理念,但我們或可以此角度去欣賞這種收放與內斂。


不是乳房象徵著性慾,而是性慾的展現使得乳房成為永恆
回到疾病的隱喻,同樣值得一提的是,《永恆的乳房》沒有落入桑塔格所批判的「意志力可以治療疾病」的反智。在劇情安排與角色調度上,也沒有讓疾病以「懲罰性的意義」加諸於文子身上,頂多就是「壓抑」,而壓抑的力道不是她自己,而是讓她被迫走入婚姻的父權體制。這番壓抑的結構與起源,即使沒有在電影中被刻意強調,透過幾幕日本夫婦之間的互動、男女之間的分工,甚至包括舅舅與閨蜜的其餘角色的使命,都能夠窺見電影將這些意識細膩地擺放在其中。
當《疾病的隱喻》中,桑塔格言明她寫書的目的「是平息想像,而不是激發想像。不是去演繹意義(此乃文學活動之傳統宗旨),而是從意義中去剝離出一些東西。」在這番論述出現的數十年前的《永恆的乳房》,以恬淡而平實的手法,早就落實了桑塔格所強調的「平息想像」,讓疾病只是疾病,沒有多餘的意義——除了詩。
電影中,文子病後繼續寫詩,也偷偷去探望孩子;她袒露術後的身體於其閨蜜,坦承她對已逝的閨蜜之夫曾有愛意,後來又靜靜躺在閨蜜的大腿上,有如親子。文子與東京男記者漸漸醞釀出了情感,當癌末病房只剩下她一個人,室友接連去世之後,她主動走下病床,與東京男記者一起躺在病房的地板上,邀其擁抱。此時,不是乳房象徵著性慾,而是性慾的展現使得乳房成為永恆,確立了她的女性存在。

繞過「疾病的隱喻」:文子不是一名癌逝的女性,而是一名成功的女作家
這段情感的萌芽與發展,歸功於東京來的記者不懈地拜訪與鼓勵,而記者本身其實也是一名忠實讀者,期盼著文子繼續創作;於是,這是一場詩人作家與遠道而來的讀者之間的性愛。到這裡,乳房與疾病隱喻的作用已經「演繹完成」,所謂不倫戀愛與男女間的權力關係,呈現了病患的性慾等禁忌枷鎖,也都給「翻轉完成」了。
最後,文子臨終前,陪伴身邊的不是這名男子。病床左右兩邊是她的兒女,兒女由她的閨蜜安撫著;床尾是她的弟弟,也就是擔負照顧責任的兒女的舅舅;她的母親、兒女的外婆則忠於文子的想望,替她以臉盆接水,洗著她的長頭髮。癌末終究一死,沒有離奇的另類結局,大人推送著遺體出病間,兒子與女兒在柵欄的這一方牽著手,大喊「媽媽」,電影響起了應當有的催情音樂,動人熱淚。
然而重點是隨後的真正落幕,在湖面上有連綿的島,形如乳房,彷如恆久矗立。兩名兒女與東京男子,將花丟下文子生前心心念念的洞爺湖,畫面是早先劇情中埋下的伏筆,文子留給兒女的遺書也是一首短詩:「媽媽沒有遺產,唯一留下的,就是請你們接受我的死亡。」疾病已逝,詩則留下,除了女性,文子更是一名作家。看見女性創作者與她們的作品,既是文子的故事,也是田中絹代的故事。

所以,如果導演田中絹代與編劇田中澄江,乃至於這部電影所取材改編的日本詩人中城文子,她們在這個作品之中,仍然離不開疾病的隱喻,那也是因為女性堅定地存在於文學與藝術之中,而且以豐沛的創作能量及富有情感的生存狀態而活著。癌症之死亡恐懼、疾病之殘忍痛苦,對照著乳房之美、女性之堅毅,隱喻成立。
透過女性的乳房與其隱喻的一切,《永恆的乳房》表演出人類對於詩歌等美好事物的想像力,既無美化疾病,亦無再現污名,而是體現了人的主體性。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所傳遞的意志,仍對我們今日的觀看有所提醒:「使疾病獲得意義(以疾病去象徵最深處的恐懼)並使其蒙受恥辱的那個過程,相沿已久,似乎不可遏制,但挑戰它總還是值得的。」我想,透過創作與行動的翻轉,而非沿用既有的詮釋,也是一種挑戰的形式。這樣的挑戰,早在六十七年前的日本,就已經成功過了。


▲ 第29屆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於光點華山電影館盛大舉行!(點圖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