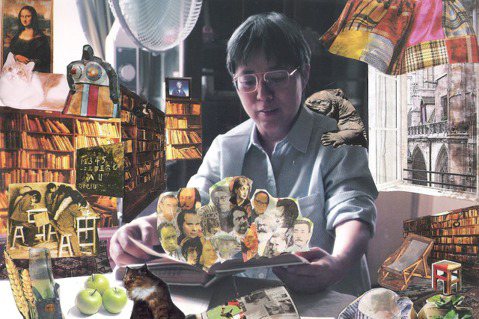我們看不見電影裡的壞人:《巴黎屬於我們》精準詮釋「何謂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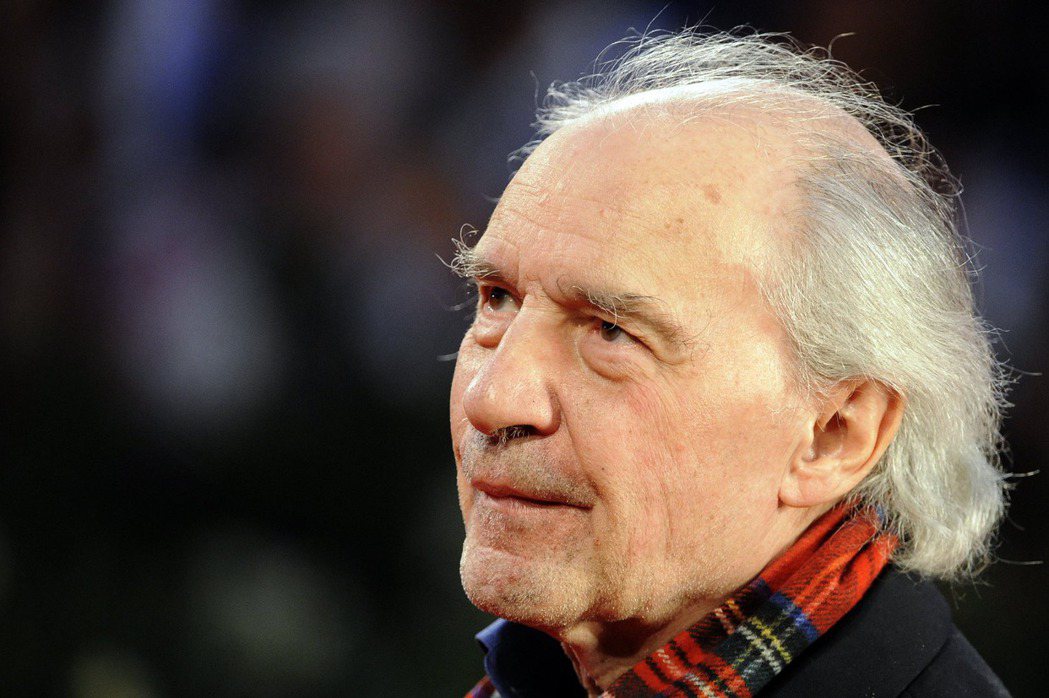
即使不懂1960年的歐洲、不懂莎士比亞的《波里克利斯》(Pericles)、不懂巴黎、不懂冷戰、不懂麥卡錫主義、不懂《大都會》(Metropolis)、不懂佛烈茲朗(Fritz Lang)或希區考克——我們依然可以看懂1961年的《巴黎屬於我們》(Paris Belongs to Us)這部由法國導演賈克希維特(Jacques Rivette)執導的首部長片。正因為「即使不在脈絡內,依然能被這部片打動」,在2021年台北文學.閱影展看到這一部片之後,我認為《巴黎屬於我們》是一部最有效傳遞「何謂政治」的鉅作。
如片頭引用了「巴黎不屬於任何人,也正因此,巴黎屬於所有人。」實際上《巴黎屬於我們》一點也不美,幾乎可以輕浮比喻「政治不屬於任何人,也正因此,政治屬於所有人。」劇情講述一個文青大學女生安妮,因緣際會進入某些交際聚會,得知一個素昧平生的男子自殺/謀殺的謎題,接著就如破案解謎般地捲進調查真相的過程,同時受到劇場導演傑哈的邀請而開始在舞台上練習演戲;過程中,她受到可疑美麗的女子、帶有愛慕之情又好似有著生命風險的劇場導演,以及親人朋友的對話互動所牽引;最後,安妮還是無法阻擋接二連三的恐怖慘劇發生,被指控「還不都是因為你想調查真相才會導致今天的結果」,她虛空地坐落原地不語。
若要簡單傳遞這部片的旨意,可以俗氣地涵括為三句話:你不關心政治,政治也會來影響你;然而介入政治,可能帶來非意圖的後果;個人跟政治的關係,便是抽絲剝繭之後,模模糊糊的一場空。
但是,也有三個理由,使得《巴黎屬於我們》完全跳脫了政治主題作品的俗氣,甚至比任何更「美」的作品來得更接近「個人」與「體制/共同體」之間關係的樣貌;而這樣的真實,使得跨越數十年、任何國家的觀眾,都有機會普世地受到這樣一部電影的震撼。
台詞、動作與情境完美具現「捲入政治的人會長成的樣子」
每個場景的「氛圍」都太精準了:打從一開始女主角安妮意外參與的聚會,男性角色們穿著正經,嘴吐知識份子文本跟輕浮玩笑之語;再到流亡至巴黎的美國人菲利普的神色緊張,舉止怪異,以受迫害姿態欲拒還迎地要「傳遞真相」,且期待他人的幫助又擔心害到對方;還有成熟風範又有致命氣息的女子泰莉及安妮的兄長、欽慕之劇場導演傑哈,都用一種「你不懂但我懂」的驕傲講話姿態,用代號跟符碼在說話,彷彿日常談吐也需要「創造性模糊」;但他們面對年輕純真的安妮時也會遮掩成知識份子禮儀般地「帶有前提、給你選擇、我不要太說教」的話語風格。
這些種種角色談吐、動作的情境,即使我們不懂法文、不認識法國人及其脈絡,也能感覺到「對,政治涉入者的說話方式就是這樣,搞革命或受秘密壓力的人說話就是這樣,兩面不是人的中介角色說話就是這樣。」而且如果我們是這場談話桌的初心玩家,我們必須知道那些代號跟符碼是什麼。資訊就是權力,大局勢的政治判斷,或是人們的親密關係、生命經驗等種種小道消息,只要在這個賽局裡,首先就要通過語言的考驗。安妮所經歷的一切,就是任何想投入政治的人會經歷的一切。
這是我在看《巴黎屬於我們》綿密的談話、舉止,以及我所不能全然理解的莎士比亞在意味著什麼的同時,仍然點頭稱道的原因,這些戲裡面精準地捕捉了「捲入政治的人說話互動起來,就是長這個樣子」。我不知道這些表演及調度是如何做到,但每一個串接與對白,都讓我覺得過分合理,包括劇場導演傑哈寫給安妮的(不知是真是假的)自殺字條,及隔日與另一女子的輕浮親吻後,突然迎向死亡,這樣混亂倒錯的情節,都能膝反射感覺到「權力關係就是這麼一回事」而被說服。

陰謀/壞人/主事者的全無線索:「後面」沒東西,所以可以是任何東西
電影最後半小時,安妮經歷了親人愛人的莫名死亡之後,好像終於要水落石出地挖掘出真相,誰是間諜、大家在幹嘛、任務是什麼、背後是誰主導,但在一個郊外房屋之中,神秘的女子泰莉只是在一個樸實的房內場景,用一連串哲學囈語式的詞彙列舉著所謂掌控人類行動、忠誠與背叛及其後果的「東西」,既不能只限縮是一個組織,也不只是國家政府,而是一個控制性的意識形態,也可能是戰後的思潮或資本主義商業社會的集體運作邏輯。
是的,泰莉有說跟沒說一樣,而女主角安妮只能聽完這一切,無所適從,跌坐。
這種「後面沒東西」,或說只把陰謀/壞人/主事者的比例與線索降到最低的手法,為什麼有用且高明?舉一個前面的場景為例或許會更清楚,安妮有一次到菲利普家,外頭突然一陣騷動,安妮被安置到隔壁女子房間,隔著房門,我們聽到門外樓梯聲有一群人來追查,女子貼著房門聽到那群追查者說沒有找到人,她們就鬆了一口氣「他逃掉了」。
在這個場景裡,我們沒有看見「警察」,或者是「秘密警察」,或者是「手握資源或暴力的某個組織裡面派來的人」長什麼樣子,我們(至少台灣人)卻完全知道那是什麼。電影刻意不將任何陰謀/壞人/主事者及其碉堡或同夥的「影像線索」透漏出來,因此那就可以是所有國家/組織/黑道派系/恐怖組織的軍人、警察、探員或什麼特攻隊,例如國民黨、或者白色恐怖時期的體制幫兇。但是,萬一我們在電影最後半小時的「真相」或是過程中的「成員」中以影像看見了任何蛛絲馬跡,我們可能會投射到一個具體的國家或組織,進而很難想像投射自身的文本,就更進不去廣泛性的政治本質指涉。電影顯然刻意要避免這件事發生。
這就跳脫了任何意圖指涉政治本質的政治主題電影,因為幾乎全無線索,所以誰也別想輕易把這部片拿去動員在任何的組織、體制、共同體。電影給你一個完整的結構,你可以投射所有的素材,帶入這個公式,都會有效,而這個公式竟是一部縝密的電影。

美麗的巴黎,只發生在創作者的飄飄然
安妮在受到純真的真相困惑及情感關係的趨力之下涉入調查真相,同時開始在劇場練習演戲,這一組對比再清楚不過,現實的展演與劇場的展演之虛實交錯,大人場域的社會化與舞台表演的熟練化,本來就是同一回事。而我想談的是,雖然文章前面說「《巴黎屬於我們》一點也不美」,但其實有一個遼闊巴黎風景的鏡頭非常美,就是傑哈在勤換場地苦苦排練莎士比亞的《波里克利斯》之後,終於得到大劇場的肯定,得以保證一定場次的放映權,形同創作者終於出頭天。
此時傑哈走上了屋頂,我們看見整個巴黎,富有文化美感建築的巴黎。那種飄飄然的喜悅刷洗了電影籠罩著不安與疑慮的氛圍。然而接下來,我們看到傑哈在咖啡店裡與安妮坐下來,安妮欣喜地抱著台詞劇本,想要從一個素人演員迎頭趕上成為夠格的舞台演員,卻被傑哈告知「因為放映劇場的要求,要讓更紅的演員來演......沒辦法讓你演。」剛點的飲料一口也沒喝,兩人便離開了這個地方。
這種極為少數的「從高空俯瞰美景巴黎」只出現在劇場導演的飄飄然之時,更凸顯此片比例如精緻調酒一般精準:酒精濃度的多寡不會決定一杯調酒是否成功,酒味必須剛剛好。傑哈的這一幕珍稀且剛好,在大螢幕看電影(跟劇場一樣作為創作形式)時,也看見了作者某種自嘲或藝術領域的自我反省之意。這是政治主題的藝術電影,然而藝術也是政治的。這場戲的企圖相當聰明且成功。

小結:追求「解釋力」的電影
電影可以不只追求美,而更追求解釋力。《巴黎屬於我們》就是一部解釋力超高之作,即使如我一個60年後遠在亞洲島國的台灣觀眾,也可以一邊看著長達近三小時的巴黎電影,一邊在腦內同步帶入我所經驗過的「台灣政治」。台灣人怎麼會看不出來,有些情境多像所謂「白色恐怖」時期的樣子,有些情景又多像「搞革命的人神秘兮兮講出來的話」,那些台詞又多生動體現了「政治人物開會講話高來高去的嘴臉」?縱然我們的島國調性跟巴黎作為世界文化的中心大相徑庭,但在政治展演與政治解讀的能力上,該有多麼容易投射、沉浸與讚嘆《巴黎屬於我們》的電影體驗。
最後,這部長達兩個半小時的作品,前面兩個小時都在迷迷糊糊、亂七八糟、焦躁不安地「調查真相」,直到最後大約半小時才「水落石出」(只是那水後之石仍籠罩在霧中)。這個電影「結構」如此寫實:我們任何一個人,開始對政治啟蒙、藉由場域內的人引介、參與或介入某些事件、有所體悟之後會懂得什麼叫做「非意圖後果」,最後並帶來破壞性創傷與虛空。那種節奏,就是《巴黎屬於我們》裡面平凡的女主角走過的這兩個半小時,前面有八成時間都在以個人生命去碰撞、體驗、探索、情緒化、裝模作樣、犯錯並調整,但到了最後,又很快地就收束到一個「我做的事情再怎麼公共(屬於這個城市),與我個人的生命、生活,實際上仍是兩件事,甚至可能矛盾。」
最打動我的是,電影最後半小時,接連發生兩個死亡的劇烈轉折,以至於女主角回顧自己過去「行動」的不明與困惑時,電影就結束了。主角所經歷的消耗與疲累之感,電影是沒有用任何台詞、場景,去做任何多餘的說教、嘮叨,沒有對觀眾下以指導棋的價值判斷,反而拍攝了湖面動植物生態自然之景,交給自然,交給觀眾。
因此,兩個半小時的時間分配除了貼近真實,作者又是有意識地收斂展演,把議題丟回給觀者,既不落入通俗便宜的符號指涉,也不落入虛無主義的陷阱,只是去指出這一切。該將《巴黎屬於我們》稱作是一種「有解釋力的電影」,這樣的電影,就跟最美的意象、最好的劇本、最聰明的調度、最動人的表演、最不落俗套的形式風格之作,同樣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