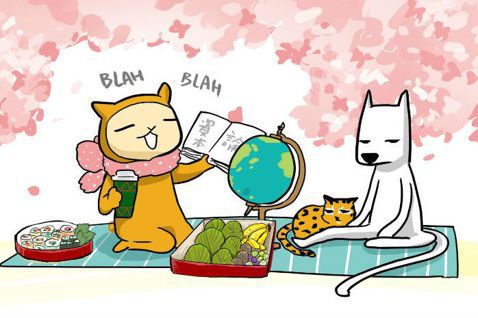蕭上晏/建中人社班停招:這社會對「人文」的成功想像到底是什麼?

我在2006年時進了人資班,是當時的第二屆,也是第一屆開放外招考進去的人。這大概是我那座國語文競賽演說冠軍獎盃的高光時刻了。
從課程內容,我可以感覺到當時的國科會對於這個嘗試是富含野心的。好比說,我們是第一個入學即文組的班級,有額外的大學人文八大領域引介、導讀課程,應該也是當時最早學習研究法、寫論文的高中生。為了查資料,還讓國圖幫我們開了未成年的通行權限。
可以說,我在這個班累積了日後我所需要的一切基礎。我的恩師在歷史課上直接開始用新歷史主義的方式詮釋多元文化脈絡。高二那一年我們最後成形的24個成員們,大概是日以繼夜的在寫論文。一直到下學期準備發表跟相互觀摩時,我們才發現只有我們學校是一人寫一篇。我一直認為那是當時建中主持與參與計畫的老師們故意不說的。
沈甸甸的升學主義,迫使我們「證明」自己
然而,人社班的存在畢竟充斥著滿滿的,從內而外的壓力。好比說,外招那一年的29人,在高二時轉走了十幾個,補進來的人數記得只有個位數。從入學時就聽到「旋轉門」、「次等生」的耳語喧囂塵上,結果也正如他們的猜測一樣。
這樣的事情或許也影響了校方繼續外招的動力?短短兩屆以後,就又回到了內部選拔的形式。
當時剛好在進修社會學領域的我隱然察覺到不對,但政治的相關資訊也讓我意識到,感覺到不對,不見得能改變。
好比說,我們班上有一些家長在高一時主張:「還是要均衡學習吧」,硬生生的在學期中插入了化學、物理與生物課。二年級後他們的孩子有不少飄然轉向理組的懷抱,恰恰驗證了外界的看衰。
尤其,我們高二時,第一屆的學長們學測成果不佳,多半都成為了指考戰士,在放榜與準備論文發表會的時刻,我也能在不頻繁的接觸中,感覺到來幫忙的前輩們,似乎在那個當下,多少對於自己這三年的投入有所懷疑。
人文到底怎樣算是資優?當時的我們似乎背負起必須回答這個問題的責任。所以我們無所不用其極,在人數劣勢下去面對合唱,話劇競賽,在論文發表會上燃燒我們的青春。可能也許,是我們,不,大概是我當時對於這個世界的回答:我們會變成這個實驗值得的證明。
未來是不可知的,17、18歲的我們,要去承擔走了一條不尋常路徑的後果,在那個當下,確實是有些過於沉重了。

人文教會我柔軟,但大家在意它能不能賺錢
後來我們那一屆,24個人,22個國立,其中過三分之二是台大。我因為數學的緣故,最後去了北教,意外的開啟了我下一段的奇幻旅程。
偶爾回母校,會聽到各種關於人社班的變化。當然,都不是那麼好的部分。投入變少了,不再成班了,其他家的人社、語資班陸陸續續停招,或者又再一次的,變成了升學保證班。
有趣的是,這些東西的縮減,調整,似乎都建立在一些很奇怪的原因:例如說學生們畢業後可能並未從事「大人們」想像的「人文專業」工作之類的。雖然我也很想問,人文專業工作是什麼?
我想我應該可以算是這個體系中的成功案例,一個自我增能、賦權、習學各類專業,不走尋常路的學者、創業者、障礙倡議者。人文的思維教會了一個理論上應該要無比固執、不做溝通的亞斯,成為現在的樣貌,仍然持續學著柔軟。是人社班的訓練造就了現在的我,沒有這段時光,我可能變成完全另一種樣子。但即使如此,我好像也沒有辦法確定,我現在的工作算不算是用到了「人文專業」。
建中停招人社班,先前耕耘再次歸零?
這是一個超前時代太多的計劃,在運作的過程中始終都面臨那些名為傳統價值的第一線衝擊,擊打與侵蝕。但我要說,這是有意義的。當年畢竟是有人頂著各種麻煩,主動開闢了一塊試驗田,灑下了一批種籽。
始終,我認為讓這些嘗試最終沒能持續下去的,並不是想法的錯誤,而是過程中更加複雜且巨大、系統化的東西。
我想大部分的有志之士都知道,因為缺乏一個精準的量化指標,人文的培養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但另一方面,一旦進入了政府的體制,在行政體系的監督、鑑別與運作下。人文的相關教育政策都突然似乎必須要能夠對社會「有所貢獻」。
別國有成功的IP,我們也要有。別國有好的文化行銷,我們也要有。別國有好的體育文化,我們也要有。可是,成功案例的背後,別國數十年來在多少大量看不見即刻成效的地方,加入了人文基礎學科的投入?沒有「這些」投入,要怎麼有「那些」?為了做到「那些」IP,又該投入多少在「這些」?
停招的人社班,是不是意味著,我們在相關領域裡的基建又要再一次歸零?或者,這種慢性的消逝早就在發生?

不斷與社會既定的價值觀對戰
在2019建中將集中成班改成分散式資優班時,時任建中教務主任的蔡哲銘校長在聯合新聞的報導中這樣說:「人社班部分課程也開放讓普通班的學生選修,人社班學生也可選修普通班課程,達到資源共享,讓課程效益能夠最大化。」
然而,在2020年台大意識報的人社班報導〈【人社班專題】一個人社班畢業生對計畫的回應與反思〉裡,作者陳人豪對於這樣的轉變,提出了他的看法:「分散式受制於高中教育框架,無法像大學班擁有高自主的教師選擇權,且因為仍依循人社計畫的結構,亦無法推廣到每個班級皆能有參與專題的機會,學生僅能選擇不熟的指導老師,又同時失去專班的社群扶持,呈現相當尷尬的磨合狀態。」
欣慰於學弟論述條理分明的同時,我也為教育制度裡所有的挫敗都能被轉換成冠冕堂皇的「共好」說法感到無奈。畢竟,在教育體系裡,我們不能爽快坦然地承認外部因素引致的失敗嘛。
我一直認為,是否有學習,察覺,有系統建構起人文素養,在義務教育階段是無法全面推廣的。不是不可能,而是投資的性價比。每個往這方向努力的推行者們都必須不斷與社會既定的價值觀對戰,取得階段性的勝利,取得被東扣西減帶有但書的資源,用一個尚不存在具體實踐標的的願景作為kpi,然後要在很短的週期裡實踐。
不到位的資源,只能用熱血與有志之士的愛與理念來填補,但愛無法解決所有需要資源去處理的東西,於是在挫折中,有人離去,剩下的只好繼續努力。然後缺衣少食的努力成果,就會變成反對者用來驗證他們正確性的東西。儘管缺衣少食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無所不在,且必然有辦法參與這些計畫的設計、驗證與執行。
人文殘響,餘音繞樑
即使如此,身為受益者,身為人生被改變的人,我仍然深深的對這個計畫,還有它打算推行的理念與願景報有樂觀,從不猶疑。
人文給我們一雙善於發現問題的眼睛,這雖然不夠,但卻是一切的起點。當然,我們還需要一些其他的東西,才能解決這個複雜的問題。理解到這一點以後,或許就能放下當時為了要維持平衡而不斷拔高的自衿,真的往前持續累積吧。
希望同期的夥伴以及後輩們,都和我一樣仍然保有這種頑強的意志。
那就暫別,我們來日再見。
(※ 作者:蕭上晏,1990年⽣,臺師⼤台灣⽂學博⼠班就讀中。⼤學兼任講師、2008年第⼆屆建中⼈社班成員。亞斯伯格症障礙倡議者,著有《我與我的隱形魔物》⼀書。原標題為〈建中人社班停招以後:這個社會對於「人文」的成功想像,到底是什麼?〉。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

|延伸閱讀|
※更多精彩報導,詳見《獨立評論》網站。※本文由天下雜誌授權報導,未經同意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