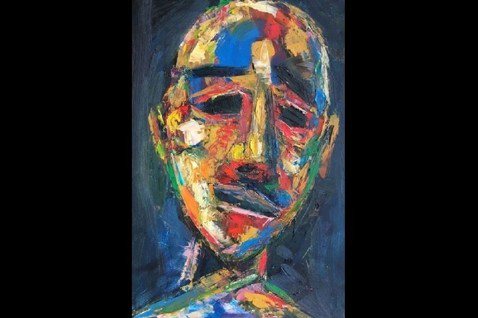只要觀眾,不要民眾?大劇院時代下的「數字管理」

在「扶植」「贊助」「策展」「公辦民營」等等的魔法布幕後正流失一點一滴的殘存想像能量,美學生命。論述者更為匱乏貧困,論述沙漠當然會急速擴張;而更微妙的是,因為這個事件的發生,方才讓人意識到論述沙漠的存在與擴張,只是論述沙漠的負面效應依舊被忽略。論述者自動撒手,放棄想像抗拒,退縮成為被動、無助的空洞觀望者。國家堂而皇之佔據想像領域,殖民論述想像者。——陳傳興,《道德不能罷免》
2018年10月,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正式上路,此舉亦宣告「大劇院時代」的開始。
《PAR表演藝術》總編輯黎家齊於〈大劇院,新藍圖〉一文開首即如此描述及提問:「1987年,兩廳院落成,是台灣第一座國家級的表演場館。30年後,隨著臺中國家歌劇院的正式營運和即將落成的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長期南北傾斜、僧多粥少的表演藝術生態,即將重新翻轉。再加上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臺灣戲曲中心,台灣將新增四座擁有千人席次的劇院,總座位大增近1萬4000個。面對大劇院時代的來臨,場館與場館、場館與團隊、場館與觀眾的關係,都將全面改寫,我們如何勾勒大劇院時代的新藍圖? 」
閱讀衛武營正式開幕記者會前後的相關報導,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下稱「國表藝」)董事長朱宗慶宣示衛武營「開幕起一年室內觀眾應達25萬人次」,並對其他國表藝轄下的行政法人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下稱「兩廳院」)與台中國家歌劇院(下稱「歌劇院」)兩位總監劉怡汝與邱瑗同樣有所要求,設定不同的數字管理目標,喊出沒做到就下台的口號。
其中的不和諧之處在於,當衛武營應然做為記者會的新聞主體,但舉目相關報導,主角卻更像是位在中央的國表藝,新聞(稿)的關鍵詞之一則變成「數字管理」,這倒把我們帶入了一個歷史情境。

政治支配文化的治理構造
自1987年兩廳院落成以來,歷任主事者的經營理念與國家文化治理的關係隱晦。之所以隱晦,源自政府組織上的政治與文化分流,國家劇院的領導者不可能直接等於國家文化的代言人,對當時脫離戒嚴體制及黨國威權體制逐漸鬆脫的台灣社會來說,更不可能如此。但既冠上國家之名,又不可能完全擺脫,此間的灰色地帶,正是主事者們思考劇院、國家、社會之間關係的危境。
朱宗慶的數字管理式發言,一來與其行政者的經歷有關,再者,也將我們帶入從2004年由兩廳院引入行政法人制度開始所積累的制度思維。名義上,行政法人制度源於時任總統的陳水扁於2001年起大力推動政府組織再造,即任務化、地方化、委外化和法人化。行政法人即為其中一環,「意外降生的」文化創意產業則被視為新經濟的可能。
在國家治理思維的連貫性上,至少要回溯到前一階段時任總統李登輝,召開國家發展會議且通過〈政府再造綱領〉的主政時期。與此相關的政經變化是精省、戒急用忍政策及亞太營運中心的挫敗等。
而與此相互連動的國際公共行政改革的大背景,則是各國的政府組織再造、公共行政改革計畫等,當時面臨的情境還包括資訊全球化的擴張、填滿效率與國際競爭力的需求,例如美國的新政府運動即為一例;英國、日本、新加坡等地皆重新以效率、精簡為準,修正政府組織。
換句話說,台灣的行政法人制度誕生的背景是經濟低迷的財政危機時期。兩廳院的經濟體質始終先天失調,「虧損」的命運從一開始到現在都沒有改變,只是在制度結構上是從給不夠錢(國家撥予母金不足)到賺不夠錢(行政法人制度自籌比)的差別,這在在反映台灣所謂的「民主轉型」迄今,政治仍然支配文化的治理構造。
新公共管理:主張績效與市場
行政法人的制度思維來自90年代以降全球化的「新公共管理」學派(New Public Management),主張績效與市場。更聚焦地說,行政法人制度是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下新公共管理的一項國家公共行政改革方案。朱宗慶當時大力推廣行政法人制度時表示:
行政法人是一個充滿理想性與前瞻性的制度,它使得執行國家公共任務的組織機構,可以藉由人事會計制度的鬆綁,增加專業競爭力;「行政法人」不一定是因應市場機制下的產物,但它卻賦予組織機構企業化經營的思維模式,強調創新、變革、效率與執行。——朱宗慶,《法制獨角戲——話說行政法人》
新公共管理的理論特質有二,一為管理主義,一為市場取向。其管理主義的內涵基本上注重的是:「公共事務運作的良窳似乎單純地只是組織原則與管理技術的優劣所致,此實質上已將政治從公共行政當中予以剝離。而此種去政治化的身影,不難在該論述中採取市場機制替代國家機關的思維中發現。其次,新公共管理秉持管理主義的基調,將成本效能以及對顧客的回應性視為公共行政的價值,或可將前述二者總稱為績效。新公共管理仍舊堅守政治與行政分離論的基調,而且是政治與行政分離論的更高層次展現。」

新公共行政:著眼於公共利益
回到台灣引入行政法人的時空,公共行政學者許立一即於2002年為文發出另一種聲音,指出美國於1990年代推動新政府運動的時期,在新公共管理的相對面亦有「新公共行政」(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相互抗衡、辯詰。
相較於新公共管理的去政治化、企業化以及市場傾向,新公共行政的思想源頭為1983年〈黑堡宣言〉(Blacksburg Manifesto),新公共行政以社會公正、公共利益著眼,探究、實踐公共行政在當代的政治性與公共性。
他們質疑:「公共行政可以既有效率而且又符合經濟的要求,但是效率和經濟卻無法解答以下的問題:優良的管理為誰而做?為誰而有效率?為誰而符合經濟的要求?換言之,政府總是輕易地假定了公民皆能夠獲得平等的公共服務,因而使得公共行政只顧及服務傳輸(即管理技術)的精進,卻未能深思服務的內容是否符合民眾所需,甚至對於社會當中不公和不義的病徵視而不見,新公共管理顯然地陷入了此種窠臼當中。」
換句話說,新公共管理需要的是不斷進場消費的觀眾,而不是具有批判意識的民眾。而在當前的台灣社會,至少還要加上,當代的新公共管理及社會的公共無意識,會培養出「被多元文化相對主義挾持,偽批判意識」的觀眾。
這裡的管理主義思想越是強調藝術與眾人的關係、藝術的美好,就越有可能顯示出其專業化及領域化的危機。今天,因為補助文化的壯大,扶植表演團隊考核績效化、藝術機構「捨民眾就觀眾」的潛在市場傾向、以及文化始終落於政治下風等因素,反而造致越來越多人做劇場,整個劇場卻因此越反文化的悖反作用。

對藝術知識生產的輕忽
對我這樣主要以書寫參與劇場的工作者來說,兩廳院發行出版的《表演藝術》於2004年4月號更名為《PAR表演藝術》之轉變,更是新自由主義擲來的訊號。
從該期開始,封面改以藝文名人化為設計導向,內容上也從原先較獨立於兩廳院之外、半研究的性質,更靠向機構化與推廣化。自此,兩廳院的自籌比壓力等比例地壓在《PAR表演藝術》身上,其潛在影響正是知識生產的空間窄縮。而衡諸現今歌劇院、衛武營都將各自的通訊、刊物《大劇報》及《本事》編輯工作外包的現象,是不是延續了新型藝術機構在知識生產上的匱缺、輕忽?
已經在多方上路的行政法人制度自然無法推倒重來,然而從前述行政法人的制度思維及其潛在影響(更不用說「藝術」對台灣人的日常認識來說仍屬新生的事物),據此閱讀去年8、9月《PAR表演藝術》分別對歌劇院藝術總監邱瑗、衛武營藝術總監簡文彬做的專訪,再辯證地檢驗其實踐。
無論是前者說的「歡迎大家走進來,也要走到世界交朋友」,抑或後者說的「眾人的藝術中心」,乃至臺灣戲曲中心及一再延遲興建進度的臺北表演藝術中心等,皆待眾人「帶著獨立思考距離、民眾性視角的深度參與」這些新型藝術機構策辦的林林總總。
而當新自由主義藉由各種制度盤據、植入藝術圈,「只要觀眾,不要民眾」,藝術機構該如何反身性地面對如此陰魂不散的資本主義幽靈,進行創造性與公共性的再生產與再分配,遂成了今天無法迴避的,且在台灣一直延遲的課題。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開幕是為去年藝文大事之一,原因之一即基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