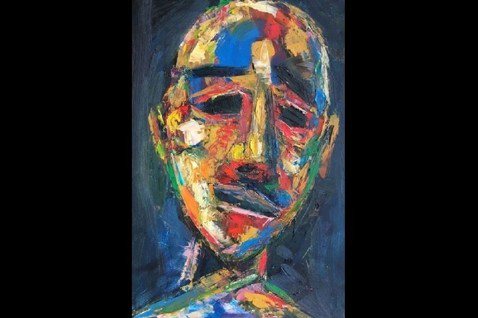「跨國共製」方法論何在?從臺中歌劇院招募訊息談起

近日,臺中國家歌劇院刊出的一則「素人影像演員」招募暨工作坊訊息,在網路上引起熱議。此為歌劇院與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合製的劇場《複眼人》(改編自台灣作家吳明益同名小說) 之招募訊息,該劇將由德國劇場導演執導,並帶領工作坊。
關於招募的動機、工作坊的目標,招募訊息只寫:「導演盧卡斯.漢柏(Lukas Hemleb)將規劃兩階段工作坊,工作坊將由導演帶領參加者以集體發展的方式,共同探索《複眼人》的意象,成果將轉化為舞台演出的部分影像。」就這則訊息,工作坊報名者只會參與演出的一小部分,並非主要演員。
但問題不在參與演出的比重,而是這場工作坊本身就包含倫理、勞動權益,乃至藝術文化的面向。招募訊息及歌劇院在粉絲專頁的回應,卻顯露了藝術機構對此缺乏意識,不知如何與外界溝通。

招募原住民素人演員之爭議
就招募訊息的內容而言,藝術機構顯然輕忽了原住民在歷史過程中積累的受殖情結,以為介紹導演「三年間多次臺灣部落進行田調」,以及選擇《複眼人》這個已有多國譯本的小說文本,就可以用字面上簡化的誠意,取代需要進一步說明、進行社會溝通的細節。
回顧歷史,不乏西方人類學家將亞洲的原民部落東方主義化的例子。而台灣劇場界所謂的「跨國共製」,亦很少擺脫西方往往佔據話語權、強弱分明的不對等關係,譬如具有藝術主導地位的導演,大多都是西方人。如果製作方缺乏自覺、協商能力、劇場美學認知,很容易無意識地鞏固這種不對等關係。
另一點,主題打出「素人影像『演員』」招募,卻只說報名者參加完工作坊,製作團隊會「支付3000元車馬費」。這筆「車馬費」對原住民,甚至劇場工作者來說,又情何以堪?用與實際工作坊時數差很多的低廉費用,就可以「買」到一個原住民在影像裡的出現?如果身分的定位是演員,即便是毫無經驗的人,3000元的演出費一樣低廉,何況這節目還是兩個在台灣相對大規模的藝術機構合製。
雖然歌劇院已經在粉絲專頁回應質疑,自認不夠周全,但這一說只是把事情推到單純的技術失誤。然而,當我閱讀該則招募訊息時,相對於「寫得不周全」的技術問題,我最詫異的仍然是:歌劇院的藝術方向是什麼?製作的方法是什麼?

欠缺民間與原民劇場的耕耘
且讓我們回到2016年,很多人應該記憶猶新,歌劇院的開幕,經由大眾媒體的報導,基本上被開幕現場的座位有限,政商名流先坐,外賓與資深藝術家卻沒得坐的「座位政治學」新聞覆蓋。
撇開這個新聞不談,我以為當時歌劇院的開幕系列節目頗有持續發展潛能,而且能走出與其他藝術機構不同的路,包括邀請民間劇場派的邱坤良製作結合民俗儀式、藝術展演的《淨.水》;以及邀請離開雲門、返回台東創立舞團的排灣族編舞家布拉瑞揚.帕格勒法,呈現新作《Qaciljay 阿棲睞》 。
這兩個作品所屬的路線——民間劇場與原民劇場——其實都有很寬廣的發展空間,兩條路線各自的獨特性也很明顯。但歌劇院營運至今,就我所見,雖然歌劇院持續與布拉瑞揚合作,但比較侷限在劇院與單一團體的長期關係,尚未擴及對於原民劇場的整體認識。
甚至從原民劇場出發,串連一個國內外的交流場域,僅守在一對一的關係相對封閉。況且布拉瑞揚挾帶在雲門舞集累積的知名度,本來就比其他的原民劇場團體來得有操作的「效率」。而民間劇場的路線,這幾年也沒看到歌劇院在耕耘。
台灣劇場生態的「公共無意識」
我的意思不是說,歌劇院非得耕耘原民劇場、民間劇場不可,而是追根究柢,藝術機構很少制定藝術方向,並透過自我論述以示公眾。自己不論述,便以為可以避免任何爭議。對於民眾及觀察者來說,很難與其對話,因為藝術機構在藝術論述上的匱缺,是台灣劇場生態的「公共無意識」的成因之一。
把這一點觀察跟招募事件連結起來,歌劇院若以布拉瑞揚舞團為基礎,擴及對於原民劇場的認識與整合,理想上《複眼人》的製作計畫正可以延續這樣的發展,並創造合製的深度,但現況顯然相反。
要把這件事歸結為「技術問題」很簡單,但這樣只是把事情草草了結,以為船過水無痕。但實際上卻無助劇場藝術的發展,也無助眾人思考機構的(跨國)共製方法論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