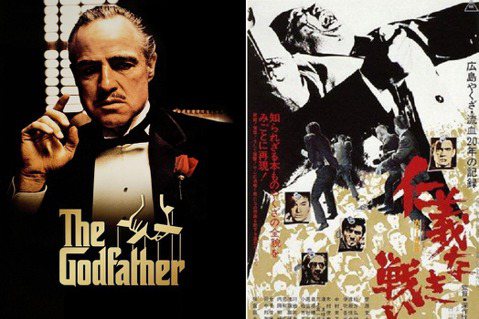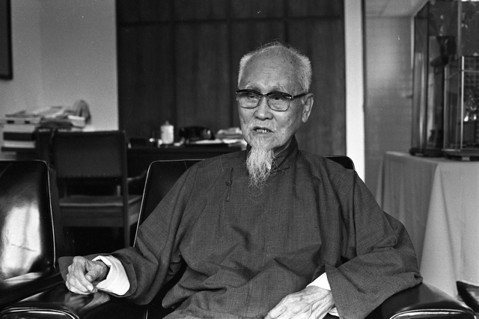懷舊是麻藥還是解藥?《胭脂扣》的香港歷史鄉愁與身分認同

張國榮與梅豔芳1987年主演的經典電影《胭脂扣》,近日伴隨「榮情蜜意張國榮影展」重新上映。雖已是35年前的作品,梅豔芳與張國榮也早已不在人世,但巨星與作品的魅力卻未隨歲月流逝。
《胭脂扣》改編自香港作家李碧華1985年的同名小說,李碧華在1980年代寫作了多部以中國與香港為主題的暢銷歷史小說,堪稱異數。其中,不少作品都搬上大銀幕。作為重要文化現象的小說與電影經典,《胭脂扣》自然也吸引眾多不同路數的電影與文學評論者的解讀。
20多年前的評論文章當中,香港出身、在美國杜克大學任教的周蕾的〈愛情信物〉,與東京大學教授藤井省三的〈小說為何與如何讓人「記憶」香港:李碧華《胭脂扣》與香港意識〉評論對象不同,前者是電影,後者是小說,但提出的視角卻可互為參照。周蕾將電影放在1980年香港的懷舊熱潮下進行反思,質問電影《胭脂扣》是否為一種想像的懷舊?藤井省三則對香港歷史與社會的考證,指出小說《胭脂扣》表述了香港共同體的前世今生。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1980年代中英談判開始,外加香港電影的興盛,香港電影中的身分想像與認同已是電影研究中的重要議題。《胭脂扣》也可以放在這個脈絡下解讀,不過,在懷「舊」與「新」的共同體之間,看似矛盾,然而,貫通舊與新,卻可找到解讀《胭脂扣》的另類方式。

在80代回望30年代:「想像」的懷舊?
《胭脂扣》的電影版與小說版結構大致相同。
1930年代,家業興盛的南北行之子十二少愛上青樓女子如花,因家人反對相約自殺,如花死去,但十二少苟活人間。死前兩人相約3811作為見面代號。如花在陰間等不到十二少,於是來到人間想要刊登廣告找尋十二少。報社記者袁永定與凌楚絹見到如花後,從恐懼到相助,最後協助在片廠找到落魄的十二少。
張國榮與梅豔芳分別飾演十二少與如花,自是電影焦點,1980年代中後期,兩人已開始綻放巨星光彩。不過,萬梓良與朱寶意所飾演協助如花找尋十二少的現代情侶,也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透過他們,一方面架構了1930年代愛情與現代的對照,前者是生死相許的濃烈,後者是愛情與工作交雜的無以安定。另一方面,也透過他們見證香港地景從1930年到1980年代的變遷,諸如風月場所倚紅樓已成幼稚園、太平戲院則變成7-11等。隨著香港經濟的發展,建築風貌快速變遷。
此外,小說《胭脂扣》出版的前一年,《中英聯合聲明》發表,確立香港將於1997年歸還中國,在「一國兩制」下「五十年不變」。在這樣的脈絡下,彼時香港洋溢著懷舊氣氛,昔日的明信片、廣告、電影海報等突然流行,成為市場上的搶手貨。
懷舊,源自精神醫學的名詞,意指人遠離家鄉多年,其所想像的家鄉,總是純淨美好。然而,想像與現實卻可能有很大的差距。面對香港的懷舊情緒,周蕾的提醒便在於電影《胭脂扣》裡的懷舊,會不會單純只是一種富饒社會下的懷舊?簡言之,是一種想像的懷舊。從1980年代的時空點,想像婀娜多姿的1930年代,尤其電影中對於風月場所乃至廣東傳統戲曲都有相當細緻的描述,《胭脂扣》像是一個包裝精緻的神話。

懷舊的意義是「懷」還是「舊」?
關於懷舊,我們可以試著更細緻地解讀。
前蘇聯出生,而後移民美國求學並任教於哈佛大學的文化理論家斯維特蘭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2001年的重要作品《懷舊的未來》(The Future of Nostalgia)當中,提出兩種類型的懷舊:修復型懷舊與反思型懷舊。修復型懷舊側重的是舊,而不是懷,透過舊來重建失去的家園與填補記憶的空缺。反思型懷舊側重的是懷,而不是舊,透過懷來建構個人與文化的記憶。博伊姆強調,這兩種類型的懷舊有時會有重合的現象,並非黑白二分。
如果以台灣為例,威權時期教科書當中的「臥薪嘗膽」、「少康中興」、「田單復國」等「歷史生聚教訓」,就是修復型懷舊的最好例子。政府不要大家思考這些歷史事件的內涵、來龍去脈,只須將之視為戮力以赴的政治目標——反攻大陸即可。至於反思型懷舊,近年來,不少文化工作者致力於日治時期為背景的小說、戲劇等創作,這些創作,正帶著對過去的反思(而非過去永遠美好),試圖建立個人與集體的文化記憶。
博伊姆所說的反思性懷舊,讓我們對《胭脂扣》可以有另一條詮釋的路徑,起點是袁永定。袁永定面對如花訴說著1930年代的種種時,當下判斷她是鬼,嚇得說「我的歷史不好!」這句話是雙關語,一方面指袁永定不想知道如花所說的那些事,另一方面更是暗諷香港人對過去不了解。但也正是歷史不好的袁永定,為了協助尋找十二少的下落,到處打探情報。
電影中,暗示了歷史找尋並不容易,袁永定到南北行,打聽有沒有人知道當年十二少家族的南北行,店員回答「我父親可能知道,但他死了」。當現代香港人想知道過去歷史時,卻可能面臨來不及了解的可能。不過,在古董店裡,他看到《骨子報》這樣1930年代報導風月場所的小報,在協助如花的過程裡,他也得知現代建築物背後的種種歷史背景。

通俗力量大:找尋昔日香港的樣貌
從袁永定的角度出發,正可以看到尋找香港前世今生的過程。
香港身分想像與認同的形塑過程中,媒體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港英政府統治下,香港成為殖民地是一段不方便明言的歷史,因此在學校教育裡,香港歷史並不被重視。1970年代電視台開播,電視劇「獅子山下」系列,再現了各式各樣的群體到香港立足的故事,這些庶民故事正是活生生的香港歷史。香港電影當中,更有許多通俗有趣的作品再現香港歷史與身分認同,這些電影在1997年九七大限前夕數量達到高潮,諸如《新難兄難弟》(1993)、《甜蜜蜜》(1996)、《虎度門》(1996)、《香港製造》(1997)、《南海十三郎》(1997)等,彼時香港電影極富活力,遠遠不只這些作品。
不過,可以看到,關於香港歷史與身分認同的時間軸,基本上從戰後開始。然而,《胭脂扣》別出心裁將時間軸往更前面的歷史推移。藤井省三透過小說《胭脂扣》的研究指出,關於《胭脂扣》的評論,部分論者認為李碧華架構了如風月場所導覽的1930年代,不過,在藤井省三看來,與其說是供人遐想的風月獵奇,不如說是對香港本身「戀愛」的歷史覺醒。
延伸藤井省三的觀點來說,小說《胭脂扣》如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當中所說的通俗小說。通俗小說的功能,在於提供讀者同一時間與共同空間的想像,進而成為「想像的共同體」。
回到懷舊。當遠離家鄉多年的人們渾然不知家鄉的劇烈變化,腦海裡依舊是單純美好的家鄉意象時,想像與現實是斷裂的,懷舊只是暫時安慰的麻藥。反思性的懷舊可以成為解藥,當我們帶著思辨透過對歷史片斷的蒐集,可以建立起個人乃至集體的記憶。
《胭脂扣》給我們的啟示是,通俗力量大,即便今日,香港還有人持續探索著《胭脂扣》當中所提到的塘西、太平戲院等地方,尤其是香港在中國因素下家園變異,人們更進一步在歷史中找尋昔日香港的種種樣貌。懷舊可以不必是麻藥,而是解決認同困頓的解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