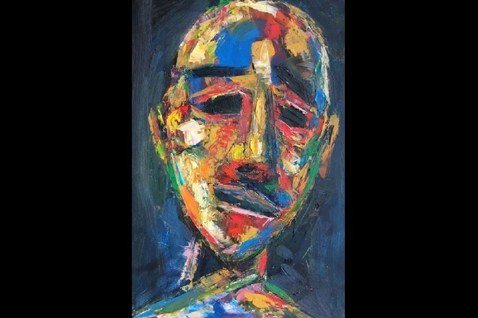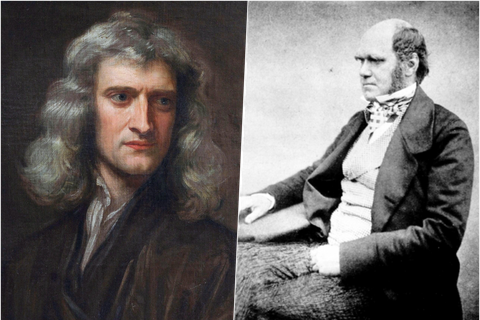我不是「白人」:一個人類學家的難題

(※ 文:郭佩宜,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芭樂人類學》主編。)
傳統人類學的主張,認為田野工作是透過學習當地語言、長期與當地人一同生活,慢慢進階理解當地文化,甚至「成為當地人」(becoming natives)。如果我只是個「白人」,那就很難真正進入當地文化脈絡去思考,也不可能做出好的人類學研究。這樣的「理想」在近年受到許多批評,我也不再天真地認為透過一年多的田野工作有「成為當地人」的可能;但或許儘量「去白人化」是我該努力的目標吧?當下我也只能朝著那漫長而忐忑的路走下去,看著辦了。
當地人如何看我
雖然不再超級在意「白人」的稱呼,但那樣的刻板印象卻是我每天生活直接面對的。從進入村子的第一天開始,我是誰——當地人如何看我,而我想做一個什麼樣的人——就是田野的實際課題。我翻了田野日誌,回想起數天前,經過幾番波折,連繫、等待,終於到了搬入村中的日子。
我被安排暫住於牧師家,那是村中最「高級」的住宅,為南島語族常見的杆欄式建築。一樓充當幼稚園,二樓是居住空間,包括客廳和幾間臥房,因為大兒子在外地工作,有一間空房能租給我使用;牧師夫婦英文流利,也解決了我初期語言不通的問題。
剛把行李搬進去,對面鄰家的年輕媳婦就過來打招呼,熱情地詢問。我很開心地接受她的善意,羅莎琳是村中少數能自在講洋涇濱的女人,我在田野前自修過所羅門洋涇濱,因此基本溝通無礙。聊沒幾句,她說:「你衣服拿給我洗。」我楞了一下,不確定這句話的意思。她解釋:「我可以幫你洗衣服。」我急忙說:「不用了,我自己洗就好。」
她再度表示沒關係,讓她洗就好。我還是推辭了,覺得很尷尬。在所羅門群島僱工很便宜,從殖民時代開始,當地人就常受僱於英國、澳洲等外國人,擔任打掃、煮飯、園藝等工作,同時,廣東移民來的商人很快地都開店當老闆,僱用當地人當店員。
「waetman」一詞在洋涇濱裡有個同義語,是「mista」,源自英文的「Mister」(先生),即反映了殖民的權力對等關係——白人被尊稱為「Mister」或「boss」(老闆),而當地人則是「house boy」或「house girl」(男傭/女傭)——這樣的權力結構在所羅門群島於1978年脫離英國殖民而獨立後,依舊難以改變。在城裡,人口比例低的非原住民普遍經濟階級高於原住民,幾乎每戶都聘了當地人幫傭。或許羅莎琳因此覺得我也會請個「house girl」吧?
然而我對這樣的階級結構感到很不舒服,同時,作為人類學者、從事田野工作,不就是要和當地人過一樣的生活,才能進入當地的脈絡?因此我壓根不考慮請人洗衣服,很快轉移話題,免得不好意思。
白米飯和泡麵「大餐」
我希望與當地人一起生活,因此決定搭伙,房東家吃什麼,我就跟著吃。午餐時間到了,牧師太太煮了白米飯,還有泡麵。
當地賣的泡麵是最陽春的那種,只附了一小包調味料,有幾種口味選擇。她另外還炸了地瓜條,我超愛吃炸地瓜薯條,聞到味道食指大動,但發現白飯和泡麵是給我和牧師太太的,炸薯條則是給牧師讀小學的兒子和女兒。面對看來有點奇怪的一餐,我不太確定要怎麼吃:是要扒白飯,還是吃泡麵?人類學者學習能力最強,所以我按捺著,想先看狀況再拷貝「正確禮儀」,很快發現泡麵是「一道菜」,用來配飯吃。
當下覺得這真是非常有「創意」的吃法,但不合我的口味,只能客氣禮貌地吃一些,同時看著薯條流口水。我發現小朋友似乎很想吃我的那份,就建議大家一起吃一起分享,於是我也吃到了薯條,覺得很欣慰。接下來好幾餐,牧師太太還是煮了白飯和泡麵給我,我感到頗為難,雖想當個不挑嘴的好客人,但又很納悶:為何每餐都吃這個?
後來我還是忍不住探探牧師太太的想法,終於搞懂了,他們以為「白人」一定不喜歡當地食物,地瓜很廉價,而白飯和泡麵都是進口食品,牧師太太為了特別照顧我,於是每天準備「大餐」伺候。我趕快解釋,只要照平常煮就好了,不要麻煩,我什麼都可以吃,食量也不大。

「白人」洗衣服
因為沒有自來水,這裡家家戶戶都在屋簷下擺了盛接雨水的容器,一般多是原本用來裝石油的大鐵桶。不同的容器乾淨程度不同,最乾淨的雨水用來煮飯洗碗,其次用來沖澡和洗衣。傍晚時我提了桶水快快沖了冷水澡,然後問牧師太太在何處洗衣。牧師家的洗衣用水就在門前的方形廢棄冰櫃中,村子裡沒有電,冰櫃是他們先前住在城裡時用過的。於是我把髒衣服和肥皂、刷子放在菜市場買來的藤編籃中,開始在門前洗衣,其實也不過是內衣和T恤、長裙罷了。
不一會聽到大聲笑鬧和嘰哩呱啦的聲音,抬頭一看,屋前路邊聚集了很多人,大家正在「參觀」我洗衣服。婦女們指指點點,興奮不已,她們七嘴八舌問了牧師太太,牧師太太急急地講了什麼,似乎有點緊張,但大家又很快笑成一團。我有點吃驚,心想是否犯了什麼禁忌,做了什麼不該做的事情?難道在Langalanga洗衣服要偷偷洗,不能給別人看到?還是女人的衣服要偷偷洗?
看我一頭霧水,牧師太太很熱心地翻譯和解釋。原來剛剛幾個婦女從田裡回來,看到我在門口洗衣服,她們覺得很新奇:「看,白人在洗衣服耶!」因為牧師家位於村中主要道路旁,從學校回家、從田裡回來的人大都會經過,於是聚集了一群人,像看馬戲一樣開心。有人問牧師太太怎麼讓我自己洗衣服?她怎麼沒幫我洗?於是她急忙解釋,是我堅持要自己洗的,可不是她怠慢。另外她也順道八卦了我中午不愛吃白飯愛吃地瓜的怪事。
我鬆了口氣,幸好不是做了什麼蠢事,只是打破了當地的刻板印象。她們第一次看到「白人」洗衣服的事情很快就傳遍村內,連續好幾天,我都是在眾人圍觀和大笑的狀況下洗衣服。幸好新鮮感很快就過去了,人們只會在經過時和我打招呼:
妳在洗衣服阿?(Koe sau kaleko o gi?)
對阿,我在洗衣服。(Eo, la kae sau kaleko gi.)
這也是我很快就學會的「實用會話」。人類學田野工作強調學習貼近當地人的生活與思考方式,關鍵的工具就是當地語言。在文化的研究上,許多概念必須要透過母語,才能精準地呈現,因此學習當地語言對深度了解當地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在實際使用的層面也是如此。
雖然曾受英國殖民,目前義務教育的小學課程也有英文,但大部分村民鮮少使用英文。所羅門洋涇濱是各族間的通用語,然而村中女性多半不願意說。村民的對話都是以Langalanga語進行,因此若只會英語和洋涇濱,往往只能鴨子聽雷。我在進入田野前已經先自修過所羅門洋涇濱,田野初期進行的基礎家戶調查需用到的簡單問句「你叫什麼名字?你有幾個小孩?年紀多大?」等,以洋涇濱和大部分成人溝通不是問題,但真正要研究當地文化,不學當地話是不行的。
「去海邊」是「上廁所」的意思
Langalanga語是所羅門群島八十幾種語言之一,使用的人口大約五千人,這麼小的群體可沒有現成教科書或語言學資料可用,一切得自己摸索。我一到村子就開始尋找能教我Langalanga語的老師,牧師太太立刻自告奮勇。首先是簡單的招呼與問候,早安、午安、晚安,這個容易,但接下來她立刻要我跟著重複長長的句子,結果聽到句尾時早就忘了句首,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這樣教我實在學不來。幸好過了一週,找到了理想的老師——塞勒斯。
第一次見到他就印象深刻,他個子矮小,光著腳,留著像雷鬼歌手的髮型,穿著自己手染的波西米亞風彩色T恤,但講話非常溫文,與造型截然不同。他是村中少數能說流利英文的人,但更重要的是,他是公認懂得深奧而古典的Langalanga語的人;大家認為我應該要學習最正確、最優美的Langalanga語,而他是最恰當的人選了。於是我開始每天早上到老師家的走廊上課,下午則做基礎家戶調查,有空就背單字和句型。
由於沒有課本,雙方都沒有經驗,塞勒斯與我一起摸索,幸好在研究所上語言學時打好了底子,倒也順利愉快。猶記國中英文課時老師教我們背每日一句,從實用的句子入手,我也把這招帶進來。那麼要學什麼實用對話?很快地我發現要先背好下面的句子:
你要去哪裡?(Koe la i fe?)/我要去海邊。(La kae la i asi.)
你剛剛去哪裡?(O io mae i fe?)/我剛去了海邊。(Lau io mae i asi.)
每天平均要進行上述對話四至五輪,每輪遇到五到六個人,大家都會問同樣的問題,因此我每日總共重複二、三十次這套對話,背得滾瓜爛熟,作夢都會夢到。的確,這裡的海景很不錯,落日尤其迷人,但不是我超愛「去海邊」。其實在Langalanga語中,「去海邊」是「上廁所」的文雅說詞。
Langalanga是靠海生活的民族,聚落臨海而建,如廁處自然選在海邊,讓海水帶走所有不要的東西。一般村民都是走到村子南邊的紅樹林,選擇隱密處如廁,男人一區,女人一區。現在比較有錢的人開始學城裡的做法,在海邊蓋「小廁所」,有門有牆,甚至還有馬桶,但沒有沖水功能,要自己舀海水沖掉。
無論去哪種「廁所」,都得往海邊走。我住的地方離廁所距離兩百公尺左右,上個廁所可是大工程,半夜要去的話就慘了,還得找伴拿手電筒摸黑去,因此我精密的算好飲水與如廁時間,降低跑的次數。每次去廁所,一路上大家總是問候個不停,「你要去哪裡?」就和台灣人問「呷飽沒」來打招呼一樣,大洋洲很多地方流行問「你去哪裡」。

「溜溜罷了」
剛開始我對於這樣的問候覺得很新鮮有趣,而且使用頻率很高,很快就能流利地背出那幾句對話,假裝一副好像學會Langalanga語的樣子,很有成就感。而且有些人聽到我說「去海邊」,還很讚賞那是優美的Langalanga話,而非粗魯地回答「去上廁所」(kabara)。
然而一陣子之後覺得有點厭煩了。距離廁所太遠,每次來回都得不斷問答,讓全村都知道我要去上廁所,或是剛剛解放過,實在是很沒隱私!而且小孩子發現這是我們唯一能「溝通」的語句,更不放過這麼好玩的事,他們特別愛問,沒完沒了,然後笑成一團。
有一天,我忍不住和塞勒斯抱怨此事。「你也可以回答別的阿。」他說。對啊,我怎麼沒想到呢?真是死腦筋。就像在台灣,路邊歐吉桑隨口問「呷飽沒」,也沒必要認真回答「我從早上忙到現在都還沒空吃東西快餓死了」。但在這個人際互動密切的小村子裡,亂答很容易拆穿,要如何不撒謊地回答?「就說你溜溜罷了。」(Liliu mola.)
於是那成了我最喜歡的制式答案。而這個問候語的小困擾,再度成為我一窺當地文化的窗口。我對於這樣的文化差異感到很好奇,什麼樣的文化特性,會以到過哪裡、或要去哪裡作為相互問候語?(同樣地,為何傳統台灣人愛問「呷飽沒?」)後來我發現,「liliu」(走走、溜溜)在所羅門群島是很重要的一種人的移動:無目的、休閒性的閒晃,但具有建立並維繫人際網絡,以及交換資訊的功能。而Langalanga的問候語也是有重要文化意義的,一個人去了哪裡,是連結人、地方和歷史的記憶機制。
在Langalanga文化中,人在地景上的作為——旅行遷徙、建造房屋、開墾農田、種植作物、命名地方等——都是個人力量與能動性(agency)的展現,祖先的遷移尤其是當地歷史記憶的核心。在反覆練習問候對話時,我完全沒預料到看似簡單的語言學習第一課,竟啟發了我對Langalanga文化認識的重要突破,而人與地景的關係後來也成為我博士論文探討的核心課題。
※ 本文摘編自《田野的技藝: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更多內容請參本書。
《田野的技藝: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作者:林開忠、張雯勤、郭佩宜、王宏仁等著出版社:左岸文化出版日期:2019/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