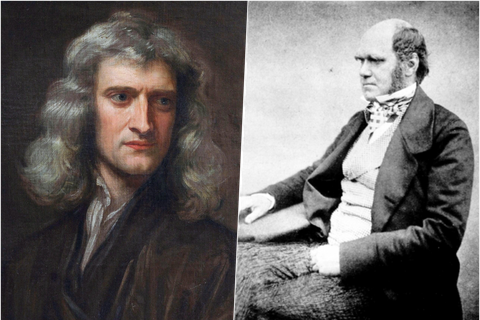上海夢的幻滅:被「驅逐」的社會底層,只能返鄉或遷離?

2016年6月16日,上海迪士尼樂園開幕了。開園第一年的遊客人數就達到一千萬人,遠超過目標的百萬人次,業績似乎蒸蒸日上。
另一方面,在接近「夢幻王國」迪士尼樂園開幕的2016年春天,發生了一個鮮有人知的現象,一群過去為了追尋夢想而來到上海的人們,正如雪崩一般大舉遷離上海。遷離的人潮多到有的幼稚園甚至因為大量孩童離開上海,面臨經營不下去的危機。
這群人就是在上海從事基層勞動或體力勞動的農民工。失去工作與住處的他們,在上海著實失去容身之地後,歷經了一番艱辛波折,最後如遭驅逐一般離去。他們是一群即使想走也不知往哪走,一群走投無路、進退兩難的人。一群被迫妻離子散的人。在上海屬於貧富差距社會底層的他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其中存在的真相是,在海納百川的廣博胸襟下逐漸膨脹的上海,如今面臨成長極限,終於開始痛苦哀號,把容納不下的地方出身者驅逐出去。
在這個「夢幻王國」成功引來人潮的城市再也看不見夢想的一群人,上海的無情切割蘊藏著急速失去光輝的危機,畢竟這裡向來以「來者不拒」的態度,塑造出其作為一個都市的魅力,並吸引人潮與錢潮的投入。然後上海的這副模樣,在國家憑藉強大經濟實力,企圖以「一帶一路」將勢力擴大至歐洲或非洲,並大手筆買下希臘港口或非洲資源等強勢行徑背後,也與整個中國努力掙扎,連在非洲都試圖創造出國民就業機會的模樣遙相呼應。
在歡慶夢幻王國開幕的上海、在不願再予人夢想的上海,以及再也看不見夢想的人群中,也可以見到拚命扶養四歲女兒的單親媽媽喬女士的身影。
「或許這次真的撐不下去了」
「剛才房東來趕我離開公寓了,叫我五天後搬出去,或許這次真的撐不下去了。」
我的智慧型手機在2016年剛開春不久的三月初旬,收到喬女士在緊要關頭傳來的這封短訊。
「連她也這樣啊。」回撥電話的同時,我嘴裡喃喃自語著,內心確信「他們周圍正在發生什麼事」。
我所謂的他們,指的是農村出身並從農村地方來到上海工作的人們。長久以來,他們都被統稱為「農民工」,但如今農民工也有了第二代、第三代,其中也有不少第二代以後的人念到大學畢業,進入都市企業工作,成為所謂的白領。
只是目前在整體比例上占壓倒性多數的,還是最初農民工從事的工作,也就是在從「改革開放」進入高度成長的1980至1990年代的中國,在都會地區從事因「辛苦、骯髒、危險」而面臨人手不足的建築工地體力勞動、倉庫作業、工廠產線工人、服務業外場、富裕階層或中上階層家中女傭的人。

工作開始減少
前文也提到過,上海的家庭女傭工作大約從2015年秋天開始減少。喬女士原本的兩家客戶,也是在2015年11月減少為一家。就在她擔心新的一年會面臨什麼狀況時,又遭到房東的驅趕。
我聽聞喬女士被驅趕的消息後,確信「他們之間正在發生什麼事」是有理由的,因為那兩、三個月以來,除了喬女士之外,也有愈來愈多在上海從事基層勞動的地方出身友人說過「我在煩惱房租要提高一倍的事」、「感覺好像快被趕出公寓了」、「我被解雇了」之類的話。
沒有足夠經濟能力為妻子準備婚宴上的婚紗,只好讓她穿優衣庫紅色羽絨外套出席的長順,也是其中一人。來自安徽省農村的他,在高中升學考試落榜後,15歲就到母親工作的上海,透過親戚的介紹開始在花市工作。他的父親思順和我同為1965年出生,今年(2017年)52歲,母親比父親小兩歲,今年50歲,兩人都只讀到小學畢業而已。思順曾經對我說:「雖然我上了六年小學,但最後只讀到三年級而已。」在現年40歲以上的中國農村出身者當中,思順的學歷並不算少見的特例。
言歸正傳,15歲就到花市工作的少年長順,因為受不了工作太辛苦,做了兩星期就辭職回到父親以務農維生的老家。附帶一提,我就是在長順辭去第一份工作,失意地搭車返鄉時,在長程巴士上認識他的。其後,他三番兩次變換職業與居住地,一會兒在東北遼寧省的瀋陽幫親戚帶孩子,一會兒又到浙江省沿海城市寧波的海鮮餐廳當服務生,然後再度回到上海當髮型設計師,最後在2012年,來到上海浦東機場附近的物流倉庫當作業員。雖然薪水視加班程度而定,但平均下來也有4,000元(新臺幣17,600元)。
那一年,他認識了在附近電子設備組裝工廠當作業員,而且同樣來自安徽省農村的17歲少女,兩人認識之後在隔年的2013年結婚,並於同年生下女兒。若加上妻子的薪水,家庭總收入是7,000元(新臺幣30,800元)。
我還記得那一陣子,長順曾用稍微多了些自信的表情對我說:「我在工作中學會操作電腦,薪水也調升了。這是我第一次覺得工作很有意思。」
他說將來想買自己的車,載女兒去兜風,為此必須先考到駕照,於是在2015年花了10,000元(新臺幣44,000元)考到汽車駕照。他成為一個孩子的父親,工作上也愈來愈得心應手。從15歲出社會起算已經第九年了,到2015年年中為止的兩年多期間,也就是22到24歲階段的長順,出社會以來第一次感覺生活充實,並過著可以描繪未來夢想的生活。

世博與迪士尼的美夢
擔任家庭女傭的喬女士雖然從成為單親媽媽開始,就過著相當辛苦的生活,但從擔任商場銷售員的2008年開始,到大約2010年為止的那幾年,每天都過得相當充實。「薪水方面,底薪非常少,業績抽成所占的比例比較多,但只要努力就會得到相對的薪水。當時即使把一半的薪水交給鄉下的父母,在上海還是可以留下一筆充足的生活費,也能存得到錢。我那時覺得要存錢重新裝潢老家也不算太困難,心想我有來上海真是太好了。雖然懷了孩子以後,必須辭掉工作,但如果繼續待在那裡的話,我想即使經濟不夠充裕,應該也不會有什麼困難。」
出社會八年多來每天為眼前生活忙得不可開交的喬女士,第一次對自己的將來感到樂觀的那一年,就是北京舉辦中國第一場奧運的2008年。兩年後的2010年則是舉辦上海世博。然後華特迪士尼公司也在這一年,與中方正式簽訂建設上海迪士尼樂園的合約。
長順的父母那一代人,也就是出生於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的第一代農民工,大約從1990年前後開始離開故鄉,前往北京、廣州、上海等大都會。然後大約從2005年開始,喬女士、長順等第二代農民工開始往上海聚集。世博和迪士尼樂園所創造出來的需求,將他們吸引到上海,支撐著他們的美夢。
然而到了2015年,這些動向卻開始變調。在中國經濟減速的同時,上海市中心的都更也暫緩下來,於是我愈來愈常聽到在建築工地從事體力勞動的農民工朋友抱怨說:「最近工作減少了,害我閒得發慌。」
此外,由於都更開始減少,因此以往靠著收集拆除現場廢材料或廢棄物維持生計的農民工,也面臨可回收品項驟減,不得不改行換業的狀況,或是在找不到新工作的情況下,因為無法維生只好離開上海的人也大幅增加了。除此之外,在接近年底的時候,我也開始從家庭女傭口中聽見工作減少的哀號聲。

市郊房租飆漲
就在那個時候,長順告訴我說:「我租的公寓要更新合約了,但房租說要漲一倍,還說:『付不出來就滾出去。』真令人頭疼。」而且差不多就在房租說要漲價的那一陣子,公司突然解散,他頓時成為失業人口。
他住的地區相當靠近上海市郊的浦東機場。雖然是屋齡才兩年的五層新公寓,但因為交通不便的關係,所以兩房一廳只要700元(新臺幣3,080元),在市中心有不少億萬豪宅的上海算是破格的房租。房東重新提出的房租是1,400元(新臺幣6,160元),不過以上海市中心的行情來說,仍然算是便宜得不可思議。但相信不用我強調也知道,人會依自己的所得水準規畫生活,租金一夕之間翻倍,要人不慌張是不可能的,更遑論還同時陷入失業狀態。
長順任職的倉庫公司在浦東機場的海關委託下,專門招攬和他一樣來自地方,學歷只有初中或高中畢業的年輕人,靠著人海戰術比對報單與貨物的內容是否一致。然而近年來,由於人事費用高漲,檢貨也改採自動化,於是仍舊維持人工作業的他們公司,工作量便因為效率差的理由逐漸減少。因此,公司的經營者決定,與其花費一筆昂貴的初期費用推動自動化,不如趁著手邊還有盈餘時收掉公司。

集體消失的幼稚園生
另一方面,擔任家庭女傭的喬女士也收到通知說,從2016年一、二月的開春時期起,房租將從以往的500元(新臺幣2,200元)漲到700元(新臺幣3,080元)。對於全家只有一人在賺錢的喬女士來說,突然調漲四成的負擔相當沉重。只是雖說經濟成長趨緩,中國在2015年的成長率依然達到6.9%,因此喬女士還是接受了房租調漲一事,並說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但如今事情之所以演變成,喬女士必須在春節後搬遷出去,是因為公寓的拆除工程定案了。那幢公寓在三年前確定將在都更案中拆除,以前住在那裡的居民雖已在取得補償金後撤離,但承包拆除工程的建設公司老闆和一部分的前屋主,卻在工程尚未開始的期間違法將房屋出租,租戶幾乎都是和喬女士境遇相同的農民工。
進入2016年以後,上海市郊陸續出現許多和長順或喬女士一樣,因為房租漲價或拆除工程來得如此措手不及,所以不得不重新調整生活規畫的農民工。
喬女士女兒琳琳上學的幼稚園,在春節結束後,園生人數減少為放假前的三分之一。在那所幼稚園上學的園生,幾乎都是和喬女士面臨相同境遇的農民工的子女。「老師驚慌失色地說:『假如這附近沒有地方可以給你們住的話,我們幼稚園早晚也會倒閉的。』」喬女士說。
他們究竟消失去哪了呢?向喬女士探問之下,她說有一半的人為了尋找跟以前差不多水準的房租,遷移至上海更郊外的地方,另一半的人決定趁此機會離開上海,暫且回去家鄉觀望一陣子。只是在遷至更郊外的人當中,也有不少人因為通勤路途太遙遠而辭掉工作,改在新居附近求職。「也就是說,」喬女士說:「工作已經不可能講究什麼意義了,因為光是找到一個住的地方就耗盡我們的心力了。」

驅逐地方出身者的上海
那麼被迫撤離的長順與喬女士又做出了什麼樣的選擇呢?
長順搬遷至稍微郊外的地方,找到與以往租金相同的房子。因為長順夫婦都才20幾歲,所以也不是不可以選擇搬到市中心,尋找商店員工、大樓管理員、清掃等工作。例如在我家附近的出租公寓,當時房租還沒像市郊那樣飆漲,因此若夫妻兩人齊心協力,也不是沒辦法生活下去,但即使是那樣,房租也會吃掉長順一人份的薪水,甚至是更多吧。「房租占去家庭收入一半到三分之二的生活實在太勉強了,所以我害怕得沒辦法繼續下去。」長順說。
喬女士決定讓女兒和幫忙照顧女兒的喬媽媽一起回老家去,自己一人留在上海繼續做家庭女傭的工作,理由是:「上海已經是個無法靠一個人養活三個人的地方了。話雖如此,鄉下的薪水比都市還少,所以我自己一個人是沒辦法存錢供孩子上大學的。」
幸好她在距離目前住處不遠的地方,又找到一間確定將拆除的房子。房租和去年一樣都是500元,但和以前那個寢室放得下三張床,還有客廳可以和室友共用的家相比,這次的公寓小到只能勉強塞進一張單人床而已。
在上海迪士尼樂園開幕那一年,大批來自地方的人開始向上海市郊移動。聽聞被迫搬遷的他們,有一部分人考慮返回家鄉時,我心裡想到的是中國當局近年來雷厲風行地推動中國版新幹線,也就是高速鐵路網的整備一事。喬女士和長順的家鄉,也在前一年夏天開通高速鐵路了。
只是開通後沒多久,喬女士與長順就被迫撤離,並面臨到工作減少或失業等波折,簡直就像算準時機似的。見到他們這副模樣,我不禁覺得耳邊聽見一個不曉得從哪裡傳來的聲音,好像在試圖甩開他們般地說:
「上海沒有各位的容身之處,你們的任務已經結束,辛苦了。不過你們看,返回鄉下的高速鐵路已經備好了,接下來請在家鄉繼續努力吧。」
但高速鐵路是否真如當局所願,對於地方出身者的新生活有所幫助呢?
※ 本文摘自《不存在的3億人》第四章,原標題為〈夢幻王國與夢的幻滅〉,更多內容請詳參本書。
《不存在的3億人》作者: 山田泰司譯者:劉格安出版社:聯經出版出版日期:2020/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