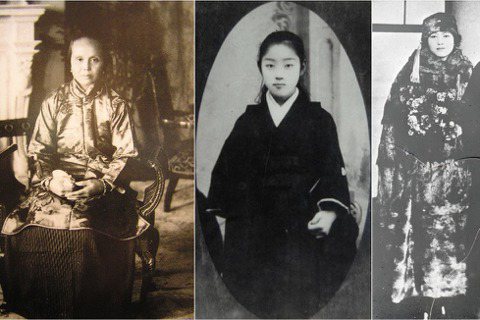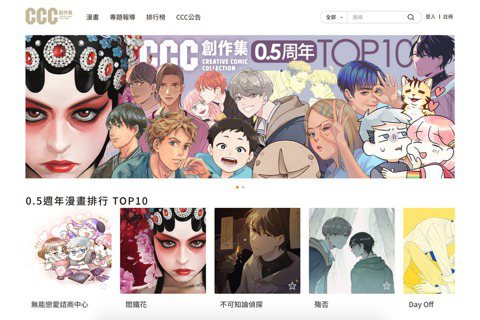《小丑》:超級英雄只是,一個凡人自願選擇瘋狂

陶德・菲利普斯(Todd Phillips)執導的《小丑》上映後,票房佳績,好評不斷,但也有一些評論指出,《小丑》沒有走出1976年《計程車司機》(Taxi Driver)的影子。沒錯,兩部電影主題確實相似:一個充滿敵意的社會,以及身在其中而無法不習得絕望,任由憎恨與暴力橫流的人類。
然而,不必只從電影藝術角度來看《小丑》。這部電影畢竟起源於超級英雄漫畫,特別是DC宇宙中林立著哥德式尖塔,及以象徵主義磚石所建築的老舊高譚市(Gotham City)。《小丑》提問了一個,在超級英雄大眾史詩中反覆被談論的難題:那些立足於黑暗邊緣的英雄與反英雄,他們究竟來自何處?
一處名為「高譚」的精神病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也許我們稍微回憶,美漫愛好者所熟悉的高譚市。這個總是籠罩在漫漫黑夜之下的罪惡大都會,本身就是一處開放式精神病院。
在蝙蝠俠的世界線,超級英雄與超級惡棍的角色意義,通常不是馬克思談的剝削與奴役,而是根源於佛洛伊德所強調的,比現實更加恐怖的深層潛意識。蝙蝠俠長年困擾於極度嚴重的創傷後症候群。企鵝先生、謎語人、雙面人、貓女、忍者大師更不必說,這些傢伙徬徨厭世的靈魂,早已放棄治療。

在其他多媒體,例如絕對有資格並列蝙蝠俠系列經典的電子遊戲《蝙蝠俠:阿卡漢城市》(Batman: Arkham City),高譚市長甚至在舊市區內部設置了高牆圈起的保留區,將所有的精神病罪犯隔離在內。
該遊戲採用此一設定,與蝙蝠俠世界的政治哲學緊密相連。因為,國家並沒有資格介入關於「正義」的種種裁判。既然人類的最大困境,來自於他們歪斜偏差的心靈深處,那麼,乾脆把所有患者丟進無序深淵。無須做作的道德或法律,只要人類繼續對自我忠實,互相爭鬥的地獄就常駐此世。
所以DC漫畫才要創造出布魯斯・韋恩(Bruce Wayne),一位奉行「人道主義」的孤獨法外英雄。
與典型美國超級英雄相較,布魯斯缺乏飛天遁地的超能力,只靠不懈地自我鍛鍊,以及一身高科技裝備。這位裝束怪異的億萬富翁(許多版本的小丑都熱衷於嘲笑蝙蝠的穿衣品味,雖然這對冤家在審美上都不太高明),每每在公權力無能插手的地方,一再地跟變態罪犯們周旋。
但是,蝙蝠俠真的熱衷於消滅邪惡嗎?這點實在使人存疑。他似乎只是對秩序與分類偏執,否則為何他明知對手能夠輕易逃出囹圄,仍不厭其煩地把犯罪者帶回根本不可能教化他們的精神病院。
這一徒勞循環,正如蝙蝠俠從未成功驅逐目睹雙親被槍殺的童年噩夢。
是的,對於帶有薛西佛斯式強迫症的英雄與罪犯來說,人性的聖殿便是收納渾沌的「阿卡漢精神病院」——在電影《小丑》中,這裡也是還未蛻變為「小丑」的男主角亞瑟(Arthur Fleck),面對往昔不堪真相的地方。
於是,「瘋人院」這個微妙空間隱喻,能讓我們進一步思考《小丑》這部大膽重寫蝙蝠俠基本設定的外傳電影:高譚市註定是展示理智衰敗的舞台,利維坦終將退化為侏儒。

誰該為了人性淪喪負責?
電影一開始,觀眾就在破敗的街景中明白,公衛與運輸系統已然失靈,社會福利也岌岌可危。
但電影也暗示,高譚市的代議民主準備了「解方」。蝙蝠俠富可敵國的父親,湯瑪士・韋恩(Thomas Wayne)強勢問鼎市長,而且很有機會當選。高譚市中產階級對於成功資本家的熱切寄望,同步於1970年代以後,右傾的全球政治氣氛。人們普遍相信,有效率的管理體制、公部門的私有化與最小化,可以拯救主權國家日益惡化的財政狀況。
這正是《小丑》超越「蝙蝠俠」其他衍生作品的地方。該片側寫新自由主義及其創世紀,還有在無聲處蠶食社會安全與公民權利的樽節體制。儘管這位名為「市場優先」的上帝看似有望「解決社會問題」,但他同時也判決凡人亞瑟的死滅、催產惡棍小丑的新生。
但最能觸動觀眾情感的部分,大概還是男主角Joaquin Phoenix帶有神性的演出。對於電影評論家來說,亞瑟悲傷的眼神可以瞥見十九世紀的《罪與罰》,那位在腐敗帝俄社會下,決定謀殺高利貸老太婆的貧窮青年拉斯柯尼科夫(Raskolnikov)。只是亞瑟不幸得多,除了對於隔壁單親媽媽那毫無根據的性幻想,在高譚市寒酸公寓電梯裡,亞瑟不可能真正邂逅一位願意用愛情救贖仇恨的索尼亞(Sonya)。
儘管如此,《小丑》的劇情安排,卻比控訴不義更為複雜。在阿卡漢精神病院的那段場景,懷疑自己可能是韋恩家族私生子的亞瑟,終於恍然大悟。搶來的病例與社工檔案清楚記載的是,亞瑟的母親好吃懶做、耽於幻想,甚至數度勒索大方慈善的雇主。還不只如此,母親也坐視同居男友對嬰兒的惡意虐待,終於造就了,腦傷無可復原、動輒淒厲狂笑的今日亞瑟。
「無產階級並不無辜」——這就讓「小丑」的真正起源,無法僅僅靠社會學來解答。


憤世者「小丑」與三位超級英雄學長
回到前面的難題:超級英雄(或惡棍),究竟來自何處?
顯然,除了難以修復的階級不平等,人類本質帶有的冷漠、殘酷,一樣居功厥偉。來自社會結構與基因天性的兩種「惡」,攜手把長期徘徊懸崖的精神病患扔進絕望之中。這就讓亞瑟大腦內不斷蠢動的「異物」——不管我們認為那是無政府主義反抗或是吞噬人性的癲狂——指向了通俗文化史上的其他超級英雄文本。
也許最先想起的,是1987年版的《機器戰警》(Robocop)。在這部帶有古典革命理想的老片,底特律市府連年赤字,警察憤而罷工,從而造就了主角墨菲(Murphy)被黑幫歹徒亂槍打死,又被跨國企業改造為生化機械的悲劇。
然而,《機器戰警》在自我認同的議題上剛好與《小丑》兩極對立——兩部電影的主角都在電影結束時「找到自我」。但是警長墨菲找回的是自己仍為肉身時的情感與記憶,亞瑟卻完全相反,過去的懦弱平庸僅是枷鎖,「真正的」亞瑟是穿戴蒼白面具的無情屠夫。
而第二個有趣的對照,則是美漫怪才Alan Moore的名著《V怪客》(V for Vendetta),即便電影改編的版本略有些降格。那位被火焰毀容,終年隱身在面具後的革命家「V」,用肉身迎擊子彈,最終將廣大「順民」喚醒為「公民」,受感召的人們紛紛戴上面具包圍獨裁政權。
不過被《V怪客》所相信的眾志成城,到了蝙蝠俠的宇宙就徹底變調,因為「小丑」的追隨者根本不是服膺倫理道德的羔羊。在這一版《小丑》中,失業勞工群眾成為失控暴徒,他們在亞瑟對三位金融白領的殘殺兇案中得到啟發,跟著在街頭殺燒擄掠,順便槍決雖然討人厭但是「在法律上」並無犯錯的韋恩夫婦,也讓未來的蝙蝠俠註定成為倖存孤兒。
而最有意思的比較,還是關於「瘋狂」的直球對決。如果說,美國超級英雄漫畫的傳統裡,還有哪位怪胎能夠在內在深度上與新一代「小丑」亞瑟相抗衡,那麼,這人毫無疑問會是經典圖像小說《守望者》(Watchmen)裡的「變臉羅夏」(Rorschach)。
無獨有偶,變臉羅夏跟亞瑟一樣,來自悲慘的社經底層與破碎家庭。不過變臉羅夏到最後都沒有放棄信仰,他只是選擇成為,用加倍的暴力來執行私刑正義的地下守夜人。
在這兩個氣味乖僻的故事中,小丑與變臉羅夏都被政府拘捕,在潔白的醫院囚室,接受專業精神醫師「心理治療」。但羅夏願意對醫師自白,如此著迷於暴力是有正當理由的,在早年還未如此偏執時,他目擊了一樁慘絕人寰的兒童殘殺案件。這慘劇徹底改變了羅夏。
但亞瑟不是這樣,他面對醫師時甚麼都不肯說,除了「你不會懂」。小丑懶得為了人類生命這樣的「笑話」提供辯護,無論治療體系用甚麼方法追問,他自顧自放聲大笑。

瘋狂是理性的最極端選項
電影《小丑》與經典文本的斷裂,似乎是在暗示,小丑這個角色「超越」了美漫歷史上的前輩。逐漸蛻變的亞瑟,直覺而非理念先行,也沒有對於原初人性的鄉愁,甚至拒絕為自己的殘酷指派任何藉口。
如果一定要問:亞瑟有沒有瘋?這恐怕要看我們是否接受,瘋狂也可以作為一種非常極端的理性。從這個角度來說,這部異色電影所描繪的,並不是亞瑟的「墮落」。只要觀眾願意沉浸於本片的反英雄敘事,感覺到的恐怕不是遺憾悲傷,而是,亞瑟隨著劇情推展,越來越壯碩強大、孔武有力。
在故事後段,原本還躊躇著要不要在脫口秀上自戕的亞瑟,開始聚精會神為新臉孔上妝。也就在這段情節中,亞瑟狠狠宰殺了誣陷、歧視自己的同事藍道(Randal),並且放過在失業前唯一尊重自己的同事蓋瑞(Gary),還附上真誠的吻。顯然,亞瑟「不是」瘋狂,他比誰都清楚殺戮或感恩的理由。但更重要的也許是,即將被小丑人格吞噬的亞瑟,第一次有能力去掌握環境,而不是被動反應。
這或是尼采鼓吹的「超人」,正從虛無主義陰影中,即將分娩的瞬間。

此外,就更現實的文化地緣背景而言,超級英雄這一通俗形象,還受益於美國歷史獨有的土壤。在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秩序下,理論上只有「國家」,可以合法擁有暴力。但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卻多少得歸功於擁槍自重的「民兵傳統」。
這一傳統使得合眾國到今天仍掙扎於,憲法第二修正案帶來的紛擾,也就是人民是否擁有不可侵犯的武裝權利(並且導致了氾濫的美國槍擊案件)。能夠推測,超級英雄漫畫確實存在著某種地區性根源:自由的美國人,隨時可以為了捍衛美式個人自由而戰,「超人」暗暗吻合於合眾國引以為傲的立國精神。在這樣的倫理圖像下,個體因為強烈的孤獨,從而擁有一種決絕與剽悍,他們打算隻身與整個不懷好意的世界對抗。
有些還未走進戲院,在別的宇宙中靈魂受創的病友,據說有些擔心,《小丑》這部風格強烈的作品,會不會剖開傷心失意者的難以癒合傷疤。
噢,此一憂慮純屬多餘。生命不是悲劇,生命必須是喜劇。故事的主角亞瑟,也曾是一名赤裸而寂寞的凡人,被合法的政治權力驅逐和排除。但真正的藝術家知道感謝這種不被他人理解的痛苦,暴君從此不必蟄伏。
如果真要給這樣有野心的電影一則簡略的解讀,或許會是這樣:從灰燼中誕生的「小丑」,自覺地遠離了老左派冀望共同革命的階級同伴,也不屑地對著社會主義先知擘劃的烏托邦藍圖啐上一口。從而如此輕快地,拋下了你我都還在其中載浮載沉的虛偽文明。
這部電影關心的不是正義,但它嘗試告訴你,理性為何自願瘋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