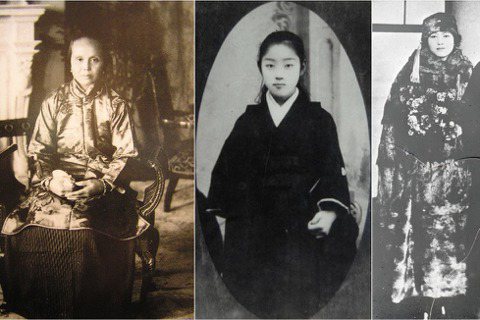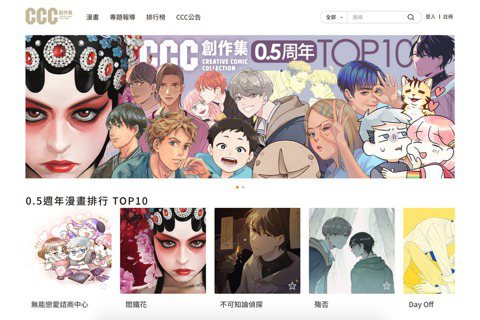金錢未必能夠擺脫窮困:《做工的人》為什麼發不了財?

(※ 本文有雷,斟酌閱讀。)
完結不久的台劇《做工的人》,改編自作家林立青的同名著作。原著是近身觀察工地現場的紀實散文,但影集刻意少了一些現實殘酷,多了一些浪漫幽默。影集主角是幾位在營造業工作的男性工人,同時也描寫了他們所面對的各種人生難題,如何導致難以翻身的階級困境。
在影集中,阿祈(李銘順飾)醉後的一番話,傳達了體力勞動者不甘認命的心情:「你們不覺得喔,這隻鱷魚跟我們很像嗎?不管被困在水池中還是在桶子裡,都一直努力要離開這個環境」。
然而,觀眾卻也清楚看見,無論怎麼努力,出頭天的彼日都沒有到來——為何工人的奮鬥終歸徒勞,賺不到錢、也無法給家人過上好日子?


身體是不懂叫苦的提款機
儘管唸書不多,但這故事裡的勞工角色,比誰都賣命。只是,生命太多無常,詐騙、工地職災、老父重病、貨車遭竊、兒女學費,一次次逼死英雄好漢。
阿祈的弟弟阿欽(柯叔元飾),人近中年不肯結婚,但是他卻沒有因此「負擔」較輕。只要哥哥阿祈又異想天開,無論投資失利或上當受騙,阿欽都二話不說,一肩扛下欠款。為了賺錢,阿欽埋頭苦幹,一天上班16小時,焊工做得又快又好——秘訣正在於上工之前先來一管「巧克力」(某種安毒)。
哥哥阿祈也不懂珍惜自己。由於年輕時接案太多,健康早就亮起紅燈,每次他走上鷹架,都得忍耐視線模糊、腰背痠痛。另外兩位主角一樣拚命,工頭昌仔(游安順飾)每個周末都另外接水泥工,來補貼手下工人待遇;而機具駕駛阿全(薛仕凌飾)則同時在幾個工地開怪手、卡車,直到深夜。
顯然,這幾個男人都沒有在理會什麼法定工時、周休二日,因為工人的鐵則就是拿命換錢。我們也能看到,為了因應高風險與高強度體力勞動,工人必須餐餐肥肉補充熱量、菸酒檳榔隨身紓解壓力。對於體力勞動者而言,意志鞭策肉體,從中榨取更多的勞動,是這一行的生存之道。
儘管如此,這種肉身透支,長遠來說並不划算。在劇情後段,我們看到,由於長年服用「巧克力」提神,阿欽開始幻視幻聽、憂鬱暴躁;哥哥阿祈更慘,在一次修繕鐵皮屋頂的臨時工作中,中風發作從高處摔下,此後半身癱瘓,三口之家頓失經濟支柱。


經濟「不」理性,因為兄弟講義氣
除了拚命做工,主角們也從不放棄可能階級上升的「機會」。年輕時曾經趴哩趴哩的阿祈,千方百計尋找賺錢門路,開廟當廟公、養鱷魚做皮包、拍賣骨董、做營養品直銷、承租夾娃娃機……為了讓妻兒過得寬裕,他什麼都願意嘗試。
工頭昌仔也是錙銖必較。一次,昌仔聽到彩券行老闆跟老客人報價,吃一次「肉包」(去後面包廂叫小姐)要3,500塊錢,他不禁心中竊喜。昌仔可不是打算對老婆不忠,而是掐指一算,既然自己每週敦倫一次——這樣算起來可不就是,一個月淨賺一萬四?
阿祈那心地善良的兒子小傑(曾敬驊飾),每每困擾於父母為了金錢吵架,因此身上也留存「開源節流」的習性。還在念高中的小傑,每次購物都將商品分開結帳,希望多一張發票對獎的機會。不管是節儉或小氣,這似乎成為勞工子弟繼承而來的某種天性。
儘管如此,工人「愛錢」又不完全是表面上那一回事。即便幾位「噗嚨共」一心一意做著發財大夢,但是,故事也明顯點出,阿祈等人不懂查證、輕信掮客、沒有能力估算成本和收益——工人對於「市場經濟」那資訊不透明、資本壟斷的本質,幾乎一無所知。於是,主角們所謂「投資、創業」,註定要以賠錢告終。
我們還能看到,雖然阿祈老是賴酒帳、佔便宜,卻有著高尚無私的個性。當兒子的發票意外中了頭獎,眼看就要脫離窮困,然而此時同事蜆仔卻因工地意外過世,只留下外配遺孀與患有唐氏症兒子面對著黑道逼債。毫不猶豫地,阿祈把獎金悉數送出,甚至讓不知原委的老婆氣到幾乎離婚。
也許應該這樣說:工人們自己都沒有察覺,正因為那種把「義氣」視作第一優先的社群文化,深深牴觸了他們渴望賺大錢的虛幻「夢想」。


沒有「惡人」的劇本
不管原著或戲劇,《做工的人》都有著結構性的關懷,因此故事裡沒有「壞人」。比如鐵工阿猴好幾次蓄意找阿欽麻煩,但最後觀眾也得知,阿猴有其溫柔體貼,他一直在替從事風俗業的女朋友還債。
工地主任亦然。儘管主任要求阿全以個人名義承受砂石車罰單、每個月從傭金中抽走數張鈔票中飽私囊,但仍不是個不講義氣的傢伙。在緊要關頭,主任願意阻擋建設公司董事長解雇在工地睡著的阿祈,同時也帶頭捐錢以幫助蜆仔死後留下的孤兒寡母。
但是,「沒有壞人」作為一種戲劇安排,或許更指向根本問題。在最後一集,阿祈阿欽兩兄弟登上即將完工的工地頂樓。看著由自己親手建築的美麗城市,阿祈不禁發出感嘆:「一棟一棟砌,好有成就感耶,可惜……沒有一棟,我們搬得進去……」假如勞動現場真的沒有「惡人」,那麼到底是誰,讓工人走投無路?
在此意義上,《做工的人》還欠缺最後一塊拼圖。

工人階級遺失的政治拼圖
我們也能注意到,面對勞動風險,工人社群間的互助,常常止於慈善——「義氣」有餘,但「團結」不足。以粗活維生的人真正需要的是,以工會、政黨、集體協商為手段,去謀求薪資、工安、福利、保險等等合理的勞動條件。
然而,這些以男子氣概自豪的工人,儘管不曾畏懼貧困或死亡,卻從來沒想到,只有聯合起來,在各種層面的「政治」進行訴求,才能通向整個階級的安全富裕。
很少透過抗爭、罷工來改善生活的台灣工人處境,當然有歷史因素。
戰後以來,威權政府掃蕩左翼知識份子、扶助資方工會、訂定寬鬆勞動法律,同時也持續鎮壓各種勞工與農民運動。換句話說,社會底層對於艱苦的待遇如此「認命」,其實來自於「制度之惡」。不管在戲劇或現實中,台灣社會的勞動者們,從來得不到組織奧援與教育啟蒙,故此沒辦法去思考,如何透過更廣泛的「階級團結」來爭取自己應有的報酬與尊嚴。
在故事最後,為了不讓一身病痛拖累家人朋友,阿欽與阿祈選擇自殺收場。我們都祈禱兩人在另一個世界能夠真正得到幸福,但是觀眾在為他們不幸命運哀悼之餘,真正的問題也許還是:「做工的人」是否太過溫柔善良,以至於忘記了,義憤應該追求制度變革,我們這個從未公正對待勞工的嚴苛社會,仍待所有勞動者繼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