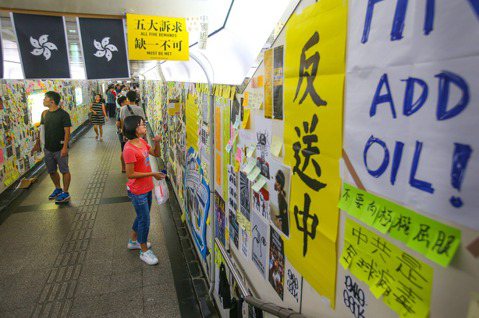葉靜倫/《午夜行者》:煙硝中記錄難民日常,用盡全力抵抗集體失憶

「難民」(Refugee)這個詞,放在現代臺灣人的成長脈絡中實在太遙遠了,如今7旬以下的年輕人,既不曾經歷當年隨國民政府遷臺的歷史,又無法想像逃亡無家的感覺,短短數十載成長於海島臺灣的生命經歷,也讓我們難以理解邊境的概念。若再放入相異的文化、宗教與暴力的複雜性,如阿富汗與塔利班,更如平行時空般無從意會。
不過,這也怪不得誰,因為「難民」這個詞確實離現實既遙遠又冰冷。嚴格來說,它是一個法律名詞1,用以定義一個人在取得難民認定後所應享有的庇護與權利,包括就醫、就業、就學與安全的居所等。而為了進行權利義務的討論,首先必須排除所有不相干的面向。例如,我們不會在聯合國的《難民地位公約》裡討論每個難民的性格、職業、信仰甚至夢想,因為無論他們喜歡什麼、相信什麼、從事什麼,都不影響他們本該享有的人權。
冰冷的法律名詞從庇護、救難、身分審核、資源配置、權利執行等龐大紛雜的全球行政體系中被各家媒體延用,許多媒體隨後開始以「難民」、「難民潮」泛指所有因戰爭或受迫害而遷徒逃亡的人,其中包括許多其實尚未取得法定難民身分的「流民」,受困於庇護申請程序而滯留異地。
手機記錄戰亂流亡的「日常」
在《午夜行者》(Midnight Traveller)中,導演哈桑・法茲里(Hassan Fazili)一家不斷在申請文件中奮鬥,流浪於各庇護所中虛耗生命,即是為了等待合法庇護獲得批准。
然而,即使一個身分名詞從法律到媒體中被更廣義的討論,即使媒體試圖以報導或故事建立世界對難民的認識,但全球落入這個名詞狀態的人如今已超過 7,000 萬人。
顯而易見,這是一個異質性過高的群體,根本不可能單從字面上來想像他們究竟是「誰」,以及經歷了「什麼」——逃亡是什麼?恐懼是什麼?不知道明天在哪裡是什麼感覺?人蛇集團有多危險?路線的選擇如何決定命運?今天睡走廊、明天睡工寮、後天睡森林是怎麼回事?讓孩子深陷威脅有多痛苦?為什麼明明沒做錯事卻無故被毆打?
《午夜行者》將所謂的「難民」立體化,同時還從難民主體與「家庭」視角出發,跳脫錯綜複雜的背景脈絡與議題爭論,讓人用心,而非用腦,來重新領會何謂「逃難」。
這部片不會告訴你塔利班是誰,以及阿富汗戰爭的始末,甚至未加多言自己為何被追殺,也沒有煽動情緒的節奏、超齡的童言童語、發人深省的教條。相反地,導演法茲里用3支手機捕捉下來的,是一家人被迫流亡的「日常」,既不血腥也不造作,有夫妻的鬥嘴、朋友的善意、孩子的嬉笑,甚至經常能看到2個女兒可愛的笑容。
被迫逃躲的大人總是煩躁、焦慮、恐懼且痛苦,但孩子,孩子不管在哪裡都可以玩,可以笑,無論是戰亂的廢墟還是封閉的庇護所,無論手上拿的是洋娃娃還是碎彈殼。只要還在家人的羽翼之下,孩子對世界都還不懂得質疑,反倒能因此將大人從情緒中拉回現實。
為了孩子,成年人必須想盡辦法籌措餐食、鋪就薄床、壓抑情緒,日夜苦撐出一種搖搖欲墜的「生活感」,這種生活感顯現出家庭中的各種強韌,但其中的脆弱也在片中表露無遺。
戰爭終究不只在煙硝戰場上,還藏在無數的生活細節裡。孩子們在庇護所玩的角色扮演是警察與監視,設定的場域是森林,最刺激的遊戲是因為沒飯吃而攀牆偷別人的果子,最煩惱的是在骯髒的庇護所裡染上滿面紅疹,而認識每一個新國家的方法,取決於當地人釋出的善意、敵意甚至暴力。
成年人最常面對的挑戰則是尋覓基本的生存所需、維持體力、保護人身安全,最難的是在無所依循的生存遊戲中做出信任判斷。誰是朋友、誰是敵人、誰為了利益、誰又出於善意?人口販子能不能信?警察能不能信?信了會付出什麼代價,不信又該懷疑到什麼程度?錢能解決的是什麼,錢不能解決的又圖什麼?每日如履薄冰,究竟是浮木還是惡意無從分辨,行差踏錯便會墜入地獄。更糟的是,就算連孩子的命都賠上了,也可能被世界遺忘,此生來去如螻蟻般無聲無息。

直面痛苦的電影工作者
法茲里夫婦正巧是千萬逃難者中的2名電影工作者,用盡全力抵抗人類的無知覺與集體失憶。法茲里因電影而逃亡,又因電影而存在,更因電影而質疑,在孩子失蹤時自我厭惡,不敢相信自己還想著拍攝,那種內心渴望捕捉畫面的激動、羞愧、價值與倫理衝突,是所有親臨重大現場的媒體工作者都得反覆咀嚼承受的。
然而,他們不只是「親臨」,相反地,記錄者既身在影像之中,又寧可不再成為影像;拍攝者既為抵抗被世界遺忘,卻更但願此生不再想起。而那每一格的生活即便已萬般寫實,綠草如茵的結尾終究只能以想像中的畫面補上2。
是這樣執意走向如此境地的捨身,是決心直面甚至刻印痛苦的勇氣,所謂「難民」這個缺乏現實感的法律名詞,在驚濤駭浪、無人知曉去向的歷史洪流中,才得以一點一滴地,長出那稀薄的骨血、肉身與形貌。
(本文授權轉載自「Right Plus 多多益善」,原標題:〈午夜行者:用盡全力抵抗無知覺與集體失憶〉。「臺灣國際人權影展」將於9月6日至8日於台北光點華山電影館;9月17日至25日於高雄電影館免費放映,更多詳情請瀏覽官方網站及Facebook粉絲專頁。)
- 文:葉靜倫,Right Plus 創站主編。曾任出版社資深編輯、NGO 雜工、NPOst 主編,對書寫斤斤計較但錯字很多。除了文字沒有其他技能。想當特務卻當了 10 年編輯,想養獅子卻養了一隻貓。相信智慧比外貌還重要,但離不開放大片。最喜歡善良的朋友,聰明的情人,以及各種溫柔的對待。」
- 更多Right Plus 多多益善:Web|FB
|延伸閱讀|
- 聯合國為因應二戰後的難民潮,於1951年催生了《難民地位公約》,1954 年正式生效。其中明訂難民的定義、資格與權利義務,以及簽署公約的國家所應承擔的庇護責任等。即使未簽署公約,也有「不遣返原則」這樣的國際習慣法加以約束,要求任何國家不得將受迫害的難民強行遣返母國或驅逐出境。
在國際公約的語言中,相對應的責任承擔者是「國家」,也就是各國政府,其中會涉及難民的母國狀況與庇護國責任等。因此如果只是在自己國內逃亡,在相關的權利討論中只能被視為「境內流民」(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IDP),而非難民(Refugee),難以得到正式的庇護與相關權利。雖然事實上,戰爭中的境內流民不計其數,所面臨的生存困境並不亞於難民。 - 法茲里一家在流離失所594天後,好不容易得以欣喜從相對舒適的塞爾維亞難民營獲准到匈牙利處理申請案,進入匈牙利後卻隨即被分隔關進拘留中心。匈牙利對人權嚴重漠視,長期以警力、軍隊、高牆、刺網驅逐難民,早已在歐盟中惡名昭彰。匈牙利政府去年甚至修法針對庇護難民的律師與社運人士提起刑事訴訟,同時打壓媒體工作者。
片中法茲里最後被拘留數月的「中介區」(transit zone),便是匈牙利設在國境邊界的強制拘留中心,自歐洲 2015 年前後爆發難民潮以來,匈牙利便沿著邊境設置許多這種寬度僅 60 公尺左右的中介區,用以隔離並控制難民行動。
此外,本片雖聚焦於法茲里一家逃亡的過程,對他們最後進入歐盟的去向沒有交待,然而難民即使在受到他國合法庇護後,從在異國就學、就業、就醫到語言、信仰、文化、價值觀的適應等,皆是另一個重大挑戰的開始,是難民議題中同樣必須關切的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