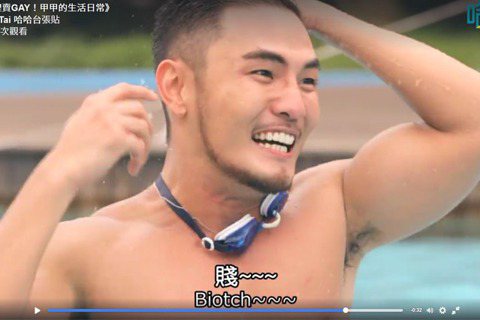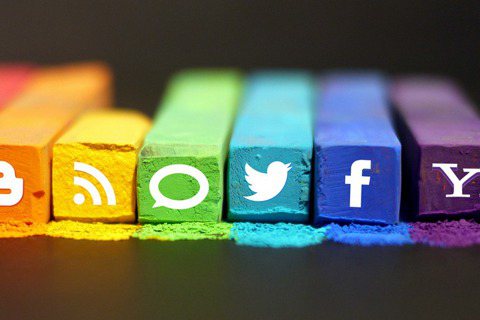世界杯的大棒棒,你爽到了嗎?

一個月了,世足賽幾乎踢翻了整座地球。隔著十幾個小時的時空差距,電視機前的人,沙發上的人,拿著啤酒的人,島上的許多人,都在螢幕前為四年一次的盛事心痛與歡呼。
然而當世界杯的美麗過去,又有什麼會留下?天價建設的足球場選手村,排除了過往社會福利的公共開支,十二座城市的十二座足球場,在檯面上覆蓋一百一十五億,在召喚出一場風光的國際賽事之前,倒已經先召喚出數百萬反世界杯(anti-World Cup)的抗爭者走上街頭。(延伸閱讀:連結1、連結2)
但是這難道不是我們想要的嗎?一座國際化、充滿競爭力、帶來高度消費金流的城市?巴西人難道不應該覺得榮耀?當各國首都仍為了世大運、設計之都爭先恐後地排隊跌倒的同時,我們是不是在心底希望辦一場屌爆了的世界杯?一場好棒棒的世界博覽會?
英國社會學家Maurice Roche認為,舉凡世界杯、世博、奧運此等吸引超龐大人流與金流的國際活動,是一種此生必看(must-see)的「超級賽事(Mega Event)」,正是國家追求現代化的老戲碼,在近二三十年成為競爭資源的新賭局。
一般來說超級賽事的發展背景,是因於都市與國家發展在戰後停滯停滯不前,公部門於是聯合私人企業,共同舉辦以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為名的國際會事,以提高公共建設支出、連帶地捲動各個層面的經濟。
時間是七〇、八〇年代,當新自由主義以英美為起點,開始席捲全球的同時,原先應為地方政府權責所在的公共服務,逐步地市場化與民營化。政府的角色自原先介入公共事務的都市經理主義(urban managerialism)中撤手,逐步轉為強調市場力量的都市企業主義(urban entrepreneurialism),以公私合營的方式,讓私人資金得以假手左右土地開發、社會福利、照護安養、文化營造等公共財,並肯認透過自由市場機制,能夠淘汰過往不具市場競爭力的商品與服務,使得社會福祉最大化。
這種對經營都市的模式轉變,值逢八O年代後歐美國家的工業衰弱,在戰後各級產業的需求已然消褪,畢竟和平的世界不是那麼賺錢,好在資本主義最大的優點正在於「需求永遠可以被創造出來」,產業的停滯逼使企業開始尋找出路,順著新自由主義大浪,經濟上與政治上的權貴階級聯袂合作,巧借「超級賽事」的名目,得以文化、發展、進步之名,增加公共建設、大興土木,超級賽事便成為拯救都市發展的萬靈丹——世界杯將會榮耀我們,而我們也將因世界杯榮耀於歷史。
超級賽事已然是都市更新的最好用的保險套,不但可以向市民保證一切在安全、正當的情況下發生,更可以達到政商同盟的集體高潮。
也於是在全球化之中,都市成為最值得被榮耀、用以賺錢的地方,但世界杯的大棒棒,到底苦到了誰?又爽到了誰?這或許才是我們該時時檢驗的。
為了打造承接超級賽事的現代之都,地方政府、國家勢力、地方財團、專家學者、傳播媒體之間,自原先處於不同階級、身處不同利益的各種人群,為了共同的城市發展目標,相組成為成長聯盟(growth coalition),協力推動都市更新與建設的各種項目。相較於傳統都市建設的鋪路造橋,超級賽事已然成為都市更新與開發的新工具,更使得受害/受益者的圖像更為模糊。
以超級賽事作為火車頭的都市成長列車太快,趕不上的人大有人在。就算不計入巴西世界杯虛報的2.75億美元,即使貪污也被處理的乾乾淨淨,改善城市形象的夢想工程仍無法解決種種的不公義/不公益:被迫遷的貧民窟、青年就業、薪資結構失衡、需要醫療的人仍然無法得到治療。
如果一個光彩明媚的未來,如果一場風光全球的世界杯,是先把邊緣少數的弱勢權利置於祭壇,那我們還需要嗎?我們仍然想要這種超級賽事嗎?
世界杯如果還是太遠,我們有更近一點的:二〇一七年的世界大學運動會將在台北舉辦,預算兩百億之中,到底又是誰受益的多了?作為一個二十一年的台北市民,我很想請問台北市政府當局,我們真的「需要」一場世大運?而這真的會帶給我們什麼嗎?一個殺死老樹的林口選手村?一個破壞永續的松菸巨蛋?還是一群承辦不動產建商,在不透明的政商結構中賺得的滿滿口袋?
無論在世足或世大運,對一個需要存錢15年才能在台北買房的八年級生來說,國際級的賽事結束後,隨著外資進場、房市炒作,我仍陷於世代不正義之中,我將更加ㄧ無所有。
有人得分,有人失分,有人一直贏得比賽,有人終將玩不起遊戲。
二〇一六里約熱內盧的奧運就在兩年後了,世界級的超級賽事不會暫停,都市開發的名目不會止息,假如真的可以向現正世界杯的巴西人問候一聲,我想問起你們:你們真的因為世界杯,更加幸福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