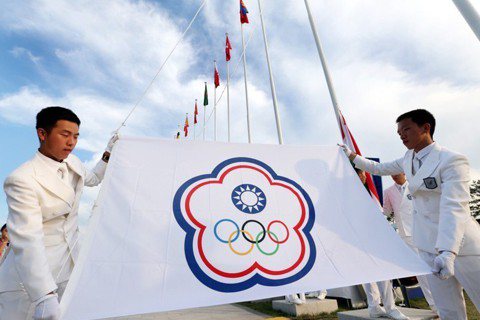為什麼不能吃朋友?

專欄作家朱家安最近引起一波對於食用狗肉的議論,許多評論者對這個主題進行了多面向的延伸探討,因為方向太過分歧,我無法做全面的探究,於此只從我個人認為最核心議題切入。
在生物倫理學中,甚至是一般的哲學普及書裡,「食用寵物」是很常見的討論議題。像是我教學用的《自願被吃的豬》一書中,即有一章是在探討吃寵物貓的狀況。
其故事內容是這樣的:
有個英國家庭主婦的愛貓跑到街上,被車撞死了。她在悲痛之餘,也發現愛貓成為一塊可食用的獸肉,就將之燉煮給全家食用。家人雖然心有不滿,但也找不出什麼理由來批判這位歐巴桑。
為什麼呢?因為這個歐巴桑不但在倫理學上沒有什麼錯,反而還踐行了「節約」之德。有肉不吃,更是浪費。
但為什麼我們會對食用寵物感到不滿?多數人主張我們把寵物當「家人」或「朋友」,而「親友」是不能吃的。但「不能吃親友」的規約,又是從何而來?
不少倫理學家認為這類規約是「禁忌」。「禁忌」的常見定義是「許多人認為不能做這事,但大家也不清楚被禁止的理由」。除了「理由不明」以外,「禁忌」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局部性」,只有某些文化接受。
所以「禁忌」是和特定文化相關的「禮俗規約」,不是具有普遍性且理由明確的「道德規約」。
要注意的是,「不能吃親友」和「不能殺親友」是兩個不同的規約。雖然大多食人族是殺人來吃(別以為食人族離我們很遠,台灣在清領末期,漢人還是會獵殺原住民來食用),但還是有一些食人部族並非殺人來吃,而是只吃其他死因的親友。有些部族甚至認為把親友吃掉是友誼與愛的最高表現。
只要有某種人類文化認為「吃親友」沒有道德上的對錯,甚至是道德上正確的行為(友誼的最高表現方式),就足以證明「吃親友」不會是道德上的必然錯誤。如果吃親友不一定有錯,那吃寵物或吃貓狗也不一定有錯了。
但以上的論述只是部份倫理學家的主張,還是有一些倫理學家主張「吃親友」可能有道德問題,也不只是個禮俗禁忌。
某些「演化倫理學」學者主張,我們的道德系統會受環境影響而產生變化,其情狀類似生物的演化,總是不斷在適應人文與社會環境。我們現在之所以不吃親友與不吃寵物,是因為我們的生存環境已發展到豐足的程度,有其他的肉類可以食用,所以不需要去吃親友與寵物。
這些親友或寵物可能對我們產生更多的美學價值,而不單純只是產生熱能而已。但如果環境改變(戰亂或災難),我們還是有可能回頭吃人肉或寵物。這種觀點也可說明為何有食用親友行為的社群通常生產能力較為薄弱,生活也較不豐足。
第二種說法來自德行論者。德行論者主張幸福是透過與他人的「合作活動」而產生,而在多數當代社會中,死者葬禮與紀念活動是重要的「合作活動」,這類紀念活動所帶來的「內在價值」(不可量化價值)遠高於單純食用人肉的樂趣,也超過「透過吃亡者的肉來紀念他」這類活動。如果「不吃寵物」也有同樣的效果,那也該這樣做。
正反兩方的意見都看過了,那親友或寵物到底可不可以吃呢?以下來談我個人的看法。
多數台灣人選擇不吃親人遺體,並將之立法管理,這是受到文化的影響,其理由是種「美學判斷」(親友屍體不是理想的食物),與道德沒有什麼關係。而「禁止吃寵物」的理由也是種美學判斷。
有些人想從經濟學角度去論述食用寵物的合理性(朱家安的原始論證有這意味),但經濟學基本上不討論個人美學偏好,而不吃親友與寵物,是我們當代社會中絕大多數人的美學偏好,從經濟學的角度去切,會漏掉不可量化的美學內在價值。
如果開放合法的貓狗肉,的確可能減低貓狗被偷竊的問題,但也可能造成更強烈的社會矛盾。許多穆斯林國家可以合法販售豬肉,但該國基督徒(在當地為少數)食用合法豬肉時,仍會引發衝突。這種外部成本,又該如何計算?
之所以有這種衝突,是因為「食物美學」的組成要素非常複雜。
學者在討論議題時習慣控制住一些變項,讓問題簡單化。但「食物」是人類文化的核心,有太多複雜的要素參雜在內,從演化出來的喜好、歷來文化的遺留,一直到個人成長過程中的經驗,都會影響我們對於食物的價值判斷。因此如果在討論食物價值(包括美學與道德)時控制太多變項,會讓思想實驗嚴重失真。
就像我個人不吃貓狗,其原因很複雜,絕對不只是「愛貓狗」或「貓狗是朋友不是食物」這樣簡單的說法可以解釋。我相信大多數台灣人不吃貓狗的原因也很複雜。
印度教徒不吃牛,穆斯林不吃豬,某些人會認為這是宗教規約的影響,但他們之所以不吃某物,還有更多成份是來自當事者的個人生命體驗,正如許多農家子弟好幾代後不吃牛,和耕田無關,而是覺得吃牛肉「怪怪的」。
如果只廢除相關規約(「禁吃牛」),但個人心中的價值觀點並未改變,這種禁令就仍然對其個人有效,而不同價值觀之間的衝突就會持續下去。所以就算在法律上開放殺貓狗或食用貓狗,也無法減緩雙方的衝突。
那要怎麼解決這種衝突呢?不妨由更高的角度來看。
我們習慣由食物來界定社會地位或角色,你吃某東西,就代表你屬於某個社會階層。現在台灣產生吃貓狗爭議的,主要是「移工」與「底層勞動階級」,因此「反對移工吃貓狗」議題可能融入階級歧視而更加複雜。在討論這議題前,就應該小心的把歧視部份先挑出、去除。
就像「移工」吃「狗貓」,被人罵翻天。那如果是「白人外商經理」吃了「逃跑的寵物袋鼠」呢?可能就有人主張要「尊重澳洲文化」「體諒他的思鄉之情」了。
在全球化的時代,我們的社會有多種文化群體共存,建立更全面的溝通模式來釐清彼此價值觀的差異,會比處理「什麼可以吃」這種單一議題要更有意義。
此外,我也要指出一個似乎被多數討論者忽略的倫理學要點。移工「殺貓狗來吃」這個議題,如果要說有倫理學的成份,那不會是「殺」,也不在於「吃」,而是應該放在「偷」之上。
這種偷是道德上的偷,比法律的範圍來得要大。就算是流浪狗,我們也認為不是所有人都有「資格」去「取」,因此當殺狗貓者任意取之,或是去偷家戶的有主犬貓時,就會產生道德爭議。
最後,如果你覺得這篇太長,或你看不太懂,我就給你個「方便法門」吧。
我們現在禁殺貓狗,理由很簡單,就是這種行為會讓社會上一大票人「非常的不爽」,所以才會立法通過。也許有些人透過殺貓狗或吃貓狗而「覺得爽」,但他們就要承擔相對的機會成本,也就是社會大眾的敵視。
有必要為了殺或吃貓狗而承擔這種風險嗎?你只能透過殺貓狗或吃貓狗來達成人生的幸福嗎?
請思考這個問題,並找到能說服你自己的答案,否則你將難以說服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