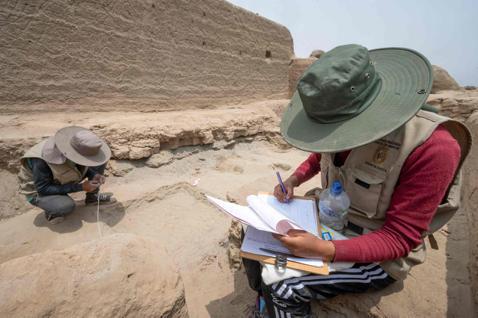劉祐誠/逝者已矣,來者如何追?再見胡台麗,再見《矮人祭之歌》

再見,是一句溫柔的道別;再見之後,除了追憶外,還有什麼可再繼續?
兩個多月前,也就是2022年5月7日,對台灣原住民文化投入相當熱情的胡台麗教授辭世消息傳出,我的社交媒體平台的諸多位好友,紛紛寫下對於這位個性熱情洋溢的人類學者追思。除了學者的身份外,胡台麗還擁有導演、作家、策展人等其他社會身份。我與教授的相遇,除了作者與讀者的單方面認識外,就僅有在賽夏族北群矮靈祭祭場,看著她時而安靜的參與,時而與諸多位賽夏族人話家常。
在胡台麗老師逝世消息公開後,我為了向這位敬佩的前輩學者致敬,於是選擇一個閑靜的夜晚,再次觀賞這個距今33年前,由胡台麗及其製作團隊,透過片段記錄賽夏族矮靈祭祭歌,讓觀眾見識到賽夏族面對現實世界、祖靈信仰的族群內外問題之境遇。
不復存在的賽夏族祭典畫面
因著自己的學識判讀經驗增加,這部紀錄片有別於自己年輕時觀賞的囫圇吞棗,影片中許多顆鏡頭從現在來看,都是些不再存有的畫面。例如:影片中諸多的賽夏族長輩;賽夏族北群祭場的位置、北群祭場組成空間的更動,這些都應該會是關心賽夏族的熱情文化人士,眼睛為之一亮的影像材料。
對我來說,一部紀錄片的生成,都會有諸多個重要關鍵因素,其中我自己認為最為重要的,應該是採訪者與受訪對象的互動。在那個甫結束戒嚴時代的台灣,許多觀念不斷地在國內相互激盪的時刻,胡台麗能於1989年完成賽夏族矮靈祭的拍攝,除了需要歸因於她個人強烈興趣使其促成外,當然也要歸功於他能讓賽夏族的領導者們願意相信她及其團隊,並由部落的耆老說服賽夏族眾人,才能讓攝影器材直接對準正在準備祭典的賽夏族人,接著才有這些一幕幕的珍貴影像。
每個祭典舉行都有各自的調性,諸如,舉行廟宇修繕完工的慶成醮典,主辦單位都會歡迎大家共同參與;攘除災厄的送肉粽,則盡量希望無相關人士避免前往觀賞。只是不常接觸原住民事務的一般民眾,每當欲與原住民文化進行互動,很容易都會用參加熱鬧「廟會」心態,來面對每個原住民的祭典。賽夏族矮靈祭的舉行目的,除了向baki' ta'ay、koko' ta'ay的矮靈道歉外,它在備辦祭典的過程,同時也要求族人們需要化解曾經有過的紛爭。
矮靈祭之於賽夏族人,那是個關乎維繫族群連結的祭儀;祭歌之於賽夏族,則是個邀請矮人們降臨祭場的溝通渠道,因此在矮靈祭祭典的最後,當無法被看見的矮人們從祭屋被眾人迎岀後,祭歌的聲音在這個晚上便不能停止,直至隔日的太陽再次升起。眾人往復不斷地唱誦祭歌誠心的向矮人們尋求和解,同時也需要像長輩們尋求告解一樣,盡量在祭場向矮人們回憶過往兩年間,是否曾經與人有過矛盾,並思考如何進行解決辦法。透過人際間、族群間的和解、道歉,每次的祭典舉行後,才能讓人數不多的賽夏族人,再次找到自己族群的歸屬感。
反思對待紀錄作品與被攝者的方式
藉由《矮人祭之歌》得知,1989年的賽夏族矮靈祭祭歌已經面臨人員傳唱恐將消失、祭場外服務於觀光客的喧囂市集,也出現可能影響祭場舉行的討論聲音。33年已經過去,當五指山上的芒草開花、矮靈祭的祭典又按照賽夏族人的行事習慣再次開始運行,祭歌如何被教導至下一代年輕人身上,以及祭場上的祭歌如何更有效的執行,這些問題都不斷的需要考驗這個時代的耆老。
幸喜的是,由五峰鄉賽夏族文化藝術協會與UTUX泛靈樂舞劇會所共同合作,他們即將出版2020年北群賽夏族矮靈祭的主祭朱志敏先生示範,總時長近六小時的矮靈祭祭歌的紀實錄音出版品,為賽夏族的祭歌傳承展開新篇章並且也為台灣的聲音,多留下另一個獨特的生成方式。
2022年6月14日,於台北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由師友們替胡台麗教授舉行追思會,當日一眾文化界重要人士出席自然是意料中之事,但是治喪委員會名單及該追思會的行程表則都出現賽夏族耆老朱志敏名字,則是令我訝異。我訝異的是,這位平常把車水馬龍的台北視為洪水猛獸的耆老朱志敏,他特地遠從新竹五峰鄉下山,來到華山文創園區向他的朋友致意,顯見朋友情誼之深,對他來說遠重於他認為那原本他無意想理解的城市。
1989年《矮人祭之歌》作品完成後,胡台麗沒有把它視為藝術作品的媒材來源地便消失不見,而是不斷得常年與賽夏諸位友人積極地保持聯繫,於是在她人生的最後一次集會中,大家才會不遠千里來跟朋友道別。我以為在探索自己感興趣的知識領域外,同時仍把焦點歸諸於人,或許這才是人文研究者,從承擔可能無法生活於現實世界的實際壓力下,卻勇敢持續邁向人文研究這條崎嶇道路上,需要保持的信念以及可能獲得的魅力所在。

我在運思這篇文章期間,網路社群上也正在繼續傳遞專擅於唸歌的楊秀卿、精通於布袋戲木偶雕刻的徐炳垣相繼離世消息,似乎在我上個時代綻放的風華都正在黯然離場。另一方面,晚近十餘年的台灣創作風氣,我大膽地、甚至有點不負責任地說,創作者們似乎從高舉跨文化改編的大旗,重心逐漸偏往在地題材進行改編、轉化。這樣的創作意識轉向,可能含有從現實政治情況過渡而來的創作焦慮,或是對台灣自身主體性展現自信,都可能是讓這股風潮持續風行的原因。
從日常生活中,我不斷見聞各自擁有自身看家本領的藝師、學者漸次凋零,或許大家都容易說,要趕緊與時間進行賽跑,才能讓這些人的技藝盡量的留在這個時代中。的確,相比於過去的各項紀錄聲音、影像技術,或是呈現這些內容的載體,確實都容易超越台灣以前尚在摸索的階段。
在疫情前的閒暇時光,我喜歡隨意地中途觀賞路巷里弄的各項祭祀活動,偶爾能看見高舉搶救該地民俗文化大旗的「熱心」人士肆意地抓取錄像,或是被主辦單位聘請的攝影團隊,攝影師們為了讓自己的畫面更加完整,直接破壞正在進行的儀典活動軌跡。這些如此「積極」的案例,儘管可能讓不在現場的其他人得以見到當地民眾與空間的互動,甚至從乾淨的畫面裡也不會讓觀眾知道,拍攝者自己正在影響活動的發生。最終某地的民俗活動被人記錄,但是被冒犯的,卻也是這些需要被搶救的事物。
透過胡台麗《矮人祭之歌》之於賽夏族長老朱志敏的互動,當創作者投入田野地進行創作、或是就原本展演體裁進行轉化創作,甚至是帶著搶救的心態,進行記錄的相關工作。無論自己進入一個族群的動機為何,這些技藝主體背後都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物。倘若沒有對待受訪者的真誠關懷,就急切的進行採集、記錄,那一句簡單的再見就不再相見,或許是對雙方最好的相處之道。

- 文:劉祐誠,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博士生。來自不住在台中高鐵附近的烏日。希望用自己所學到的各項有趣想法,努力分享給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