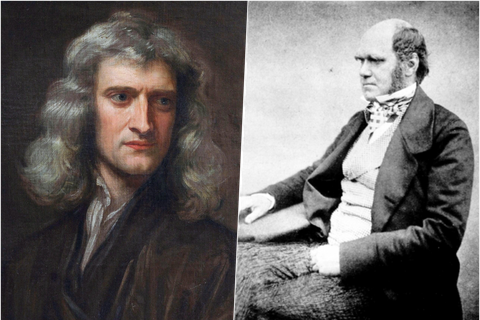內亂是另一種死刑原理?——奧姆真理教主的絞刑處決

「除了針對殺人的死刑」這個問題之外,還有完全不同領域的死刑問題。那就是從以前持續至今,也在某種意義上始終被視為理所當然,對政治犯、革命者執行的死刑。
我們向來認為,有志從事政治革命等大事的人,都願意為了自己所深信的革命信念賭上性命,也很自然接受「革命或者赴死」等標語。當為了革命而賭命的戰士揭竿卻失敗時,很少人會認為不該判處死刑,應該判處終身刑或無期徒刑。假如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被捕、槍殺之前說「我不該接受死刑,終身刑就已經足夠」,相信大家都會有種受騙的感覺。
內亂與死刑
歷史上看來,內亂或外患罪,即與外國勢力共謀企圖顛覆國家之罪,判處死刑是常見的情況,現在許多死刑存置國也多是如此。
日本也規定有內亂、外患罪。死刑廢止論的代表學者貝加利亞(Cesare Beccaria)明確肯定對外患罪應判處死刑:
市民之死可能有用的情形有:首先,當罪人與威脅國家安全之各項權力有關,且罪人之存在對於現已確立之政體可能誘發危險革命時。——《犯罪與刑罰》
但是,要在法律的框架中說明此時死刑的正當性並不容易。因為這些犯罪——內亂罪、外患罪、叛逆罪——並不以殺傷人作為法律要件。實際上,在幸德秋水受到連坐判處死刑的大逆事件和櫻田門事件當中,明明沒有出現任何死傷者,卻還是判處死刑。
這些案例從法學上來看,只能用國家的自我防衛權來說明死刑的正當性,但實際上這已經跨越了法律框架,不顧一切只為了維持既存國家秩序,因此這樣的說明也只是一種欺瞞。在內亂和革命的情況下,於法律無秩序狀態中出現原始性的力量與力量的衝突,所以與其說是法律問題,這更屬於實力、暴力的領域。
霍布斯(Thomas Hobbes)認為,自然狀態是「萬人對萬人的戰鬥」,為了讓人類社會得以維持秩序與和平,需要創造出絕對的權力,而所謂法律秩序便是藉由權力(利維坦)約束暴力(「萬人對萬人的戰鬥」)來實現的。不過,在這裡成為問題的是,無法納入霍布斯所謂「法律理路」的領域。
這與一個井然有序的和平世界中的死刑問題,很明顯有不同本質。我們必須看清楚暴力與權力論之間的界線。
死刑中有腐敗的存在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認為,國家權力有兩種:
法律維持:維持、確認法律,為了強化其規範性效力而發動
法律創制:重新訂定法律,為了賦予國民新的強制而發動。
前者是基於法律的權力行使;後者則是偏離法律的權力行使,因此根本上來說其實並無根據。所謂「法律創制」,並非意指訂定法律的正當權力,它包含甚至可以左右法律權力的意涵。
也就是說,後者的「法律創制」不管表面上採取何種形式(以往用的是武力征服,現代則採取議會制民主主義的形式),其內涵都是一種暴力的行使。
而在國家權力中,死刑權力和警察權力這兩種權力也往往不僅止於「法律維持」,同時常態性、日常性地進行「法律創制」。因此,具備其他國家權力行使所沒有的特徵,也就是班雅明所謂的「腐敗」:
事實上死刑的意義並非處罰違法,而是確立新的法律。因為只要行使能左右生死的暴力,遠比執行其他任何法律,都更能強化法律本身。不過在此同時,也正是這一點,透過纖細的感性更可感受到法律當中有某種腐敗的存在。——《暴力的批判》
班雅明所謂「死刑中有腐敗的存在」,是因為死刑表現上是「法律維持」(法律的執行),卻對政治犯等進行「法律創制」(無根據的暴力行使)。
另一方面,班雅明認為社會權力、人權的行使也與國家權力一樣,具有原始的暴力性質。比方說勞工權利之一的總罷工,總罷工中當然感受不到「腐敗」,可是具備「法律創制」的要素,這一點與死刑還有警察權力的專斷行使是一樣的。在班雅明的《暴力的批判》中也論及總罷工是一種實現革命的特殊手段。
死刑的權力關係
根據這種權力論,總罷工騷亂、動亂、內亂、革命,都是「法律創制」之權力作用的場景。同時,當該嘗試失敗,首謀者被既存權力判處死刑,也一樣可以看到「法律創制」式權力作用的場景。
對政治犯判處的死刑,不僅從現象來看,從權力論來看,也與政治犯企圖顛覆國家的嘗試等值。對政治犯判處的死刑,儘管可以強烈感受到班雅明所謂的「腐敗」,卻依然與內亂、革命暴力等值。
實際上在內亂中,革命勢力在革命成功、達成目標的過程中,為了留下「革命成就」的證據,往往會對既存統治者進行「處刑」。不管這是以立即審判判處的死刑,或是在混亂中不經審判實行實質死刑,無論形式為何,都無疑是班雅明揭櫫的「法律創制」之權力行使。
其背景並非出於只允許革命勢力有流血特權,或者在非常時期民眾停止思考的結果,而是在兩者之上,渴求犧牲的權力(逐漸樹立的新權力)之本質。這種歷史現象必須從這個角度來理解。
班雅明說革命是一種「神的暴力」或者「純粹暴力」。既然如此,當革命失敗,對政治犯進行的死刑也可以冠上同樣稱呼。此時甚至無須探究死刑的根據,只要拿出非常時期「法律創制」的權力,死刑的權力關係便已成立。
康德一方面表示,只支持由自由、平等、法律支配所形成的共和制這種國家體制;另一方面也認為,當統治者背離共和體制轉為暴政時,反抗暴政統治的人民即使是為了自由,也只能根據大逆罪被判處死刑,這就呈現了類似的概念。
奧姆審判為一場司法戰爭
內亂罪適用問題的例子在歷史上並不多見。
內亂本身在日本從明治時期起,陸續有佐賀之亂(1874年)、萩之亂(1876年)、西南戰爭(1877年),此後從未根絕。
而就算不適用如同字面的內亂罪,也有些事件帶有同樣權力行使的色彩。例如大逆事件,還有奧姆真理教事件也明顯有此傾向。
從昭和末年(1989年)到1995年,奧姆真理教引發的一連串殺人、監禁致死等事件中,遭受被害致死者27人、負傷者約6000人,另一方面遭起訴的教團相關人員超過180人,包含教祖在內有13人獲判死刑。
儘管這一連串事件中心是1989年的坂本律師全家命案、1994年的松本沙林毒氣事件,以及1995年的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但整體來說,這一連串的事件不僅帶有強烈的恐攻色彩,也伴隨著出自宗教狂熱所衍生的國家顛覆計畫。另外,奧姆真理教甚至建設沙林毒氣製造工廠,企圖以化學武器發動武裝革命。
審判中,對教團幹部14人求處死刑,在法院除了一人以外其餘全部做出死刑判決,剩下一人判處無期徒刑(不過為特殊無期徒刑判決),也就是前面所說的「實質終身刑」判決。
檢察官對於所有被告人以一般犯罪進行起訴,但辯方曾經對一位被告人提出應適用內亂罪的主張。
奧姆真理教事件確實帶有內亂的要素,但是就根本上來說,國家權力不可能完全沒有發現到此種包含內亂危險的事態存在。司法權力也一樣。
實際上,最高法院在進入平成之前(即1989年之前),為了預防首都內可能發生內亂導致的大混亂,曾經對東京地方法院本廳的刑事部(刑事法院)進行組織體制與人事體制上的措施,以期充分保留處理事件的餘力。
因此影響到都內其他支部(東京地方法院八王子支部,現立川支部)的刑事部,需承擔較大的負擔。此舉雖然並未具體明言是以奧姆為目標採取備戰體制,但確實考量到國家陷入危機的狀況,以備萬一。
後來,奧姆真理教也確實發動前所未有的化學武器恐攻事件,東京地方法院彷彿已經做好準備般,從一般三位法官審理的體制(合議體)臨機應變改為四人制和五人制,迅速因應。
警察、檢察官等日本國家暴力裝置這一連串的措施,都是國家對奧姆真理教的掃蕩、毀滅戰,而法院本身也進入備戰狀態,準備投入這場戰爭。
司法戰爭的敗者
奧姆裁判確實是一場司法戰爭。
所以如同前述,儘管求處死刑,最後卻出現一個實質終身刑判決的人,這個事實震驚了法曹界。就算已經科處實質終身刑這種重刑,法院駁回檢察官的死刑求刑,就表示已經退出這場司法戰爭。
這是一種極為不上不下的權力行使。同時也可以說,法院依然在司法原本的權能「法律維持」這個領域中踏步。
無論如何,整體看來,奧姆真理教事件的死刑並非單純「法律維持」的權力行使,而是「法律創制」的權力行使,也就是赤裸裸的主權權力作用。此外,奧姆真理教所引發的一連串事件和對這些事件的審判,彼此之間可說是一種「構成的權力」的衝撞。反過來說,也因此成立了穩固的死刑權力關係,市民對於死刑這個結論也從未有疑。
更具體地說,在現代社會中使用生物武器或化學武器,不僅具有單純殺人的意義,相對之下,如果對這類犯罪的死刑是以不殘虐的方法進行,那麼就沒什麼否定生命刑的理由吧。
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等如同前述,以無差別隨機殺人這一點看來,基於「安全社會」的理念可以讓死刑正當化;同時,就使用化學武器的毒物恐攻這點來看,也找不出死刑之外的選項。
※ 本文摘選自《死刑肯定論》,原文標題〈第十一章:內亂與死刑〉,更多內容請參本書。
《死刑肯定論》作者:森炎譯者:詹慕如出版社:光現出版出版日期:2018/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