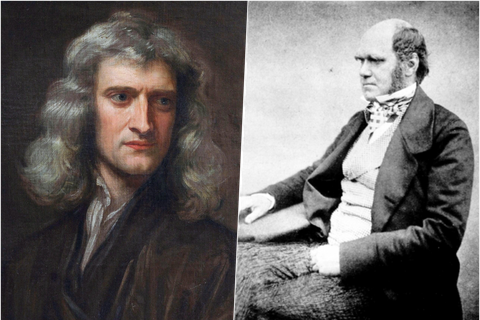「世越號文學」的開始——導讀《那些美好的人啊》

※ 文:金明仁,文學評論家。
1
那天以後,人們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有的人哭了好多天,甚至以淚洗面數月,他們就像很容易被小石頭絆倒、體弱多病的人,就算看到習以為常的景色或聽到風吹草動,都會哭出來。不光是那些碰一下就會哭的人發生了改變,那些沒有流淚的人也發生了改變。他們心裡都掛著一個沉重的鐵塊生活,所以走在路上更顯沉重,看待世界的視線也不知怎的,像被罩上一層陰影,變得黯淡無光;也有人總是無緣無故的神經質、發脾氣;還有些人明知那件事不是自己的責任,卻不停責怪自己,把自己逼往絕境。就這樣,這些悲傷的、哭泣的、努力不去忘記的人,在那天之後都像得了重病。
但絕大多數人只是到此為止,他們忍受著自己能夠承受的痛苦,時而選擇去淡忘此事,時而面對突然想起時止不住的眼淚,就這樣慢慢的中和那些痛苦,為了討生活而忙碌,為了各自不得已的理由。
但在這群人當中,也有些人是不同的,他們把難過與憤怒轉變成團結與抗爭。那天後,他們直接跑去彭木港與罹難者家屬並肩作戰。有人陪伴家屬去抗爭,有人悶不吭聲的做起各種粗活,有人做記錄,有人安慰、治療罹難者家屬,還有人陪同家屬踏上那漫長的釐清真相之路⋯⋯那天之後,不僅是心的型態、亮度和色澤都發生了改變,有些人的人生型態和生活色澤也都徹底轉變,他們放棄了那天以前的生活,徹底改變了人生的方向,將時間和空間的存在轉移到「那天之後」。即便這些人有與其他人不同的條件與理由,但這樣做絕非易事,我只能以驚訝、帶著敬畏之心的眼光關注那種「自我獻身」所帶來的轉換瞬間,因為像我這種平庸之人是無法接近那種境地的。
在我看來,金琸桓也經歷了那種轉變瞬間,更準確的說,他應該是自己突破、衝過去的人。根據我的淺見,可以將金琸桓看作「世越號之前的他」與「世越號之後的他」。
金琸桓與我雖是同門同系,卻是晚我10年的後輩,我與他沒有什麼特別的交集,更確切的說是我們很難有交流的機會。雖然我是評論家,他是小說家兼評論家,但我是在80年代中期踏入文壇,活躍於90年代初,金琸桓則是90年代中開始寫評論和小說。正如大眾所熟知,80年代與90年代的文學之間存在巨大的斷層,即便不提我脫離文壇、近似封筆的那段時期,我仍不會把這些90年代新秀列為評論對象。
況且,金琸桓並不是以被稱為「正統小說」的短篇小說展開作家生涯,他主要以《不滅的李舜臣》、《許筠,最後的十九天》、《黃真伊》等長篇歷史小說活躍於文壇,雖然他有許多作品受到廣大讀者喜愛,但這類作品多半被歸類於「大眾文學」或「通俗文學」的範圍,而這類內容與我關注的種類有著一定的距離。
說實話,金琸桓所寫的長篇歷史小說,我只聽過書名,從未讀過任何一本,所以自然不知道他企圖透過那些歷史故事傳達什麼核心價值。也許正因如此,世越號之後,他的行動似乎用「變化」、「飛越」或「突破」來形容更為恰當。哪怕是現在才仔細閱讀他的作品,想必也可以從書中看到關於這個時代的激烈譬喻。再者,金琸桓選擇了與當代其他作家不同的路,應該可以成為他在世越號之後做出耀眼「獻身」的線索。但我不打算用「自我獻身的飛躍轉換」來形容世越號之後的他,重點不是他在這段期間的想法,我關注的是現在他在做什麼。那天之後,很多作家感到苦惱和悲痛,卻沒有一個人能像他這樣去行動、去寫作。
若用一句話來形容世越號之後才認識的金琸桓,他就是「世越號的人」。
我知道他策畫並主持了播客「416的聲音」,不僅見了罹難者家屬,還有很多潛水員,他深入世越號的問題,與形形色色的「同伴」保持緊密聯繫,從各方面深入且持續幫助罹難者家屬釐清真相。不僅如此,他還將從這些接觸中獲得的素材與自己的本業結合,進行小說創作。他在2015年就以朝鮮時代漕運沉船事件為題材,寫出讓讀者聯想到世越號的長篇小說《目擊者們》;2017年,在《黃海文化》夏季號刊登了短篇小說〈尋找〉;隨後八月出版了長篇小說《謊言》,並憑藉這部小說榮獲第33屆樂山文學獎。《謊言》出版後不到8個月,他再度出版收錄了〈尋找〉等8篇小說、描寫世越號故事的短篇小說集《那些美好的人啊》。
金琸桓擁有可怕的集中力,他出道20年來共計出版了25部長篇小說,也不停歇的出版短篇小說、童話、散文和評論集等,僅憑專注力並無法完整說明他有別於其他作家的驚人產量。某次見面時,他曾坦露,自己也不知道會一直執著在世越號這個主題上到什麼時候。從他的言語中似乎可以預想到他對世越號的專注力,並非只能用「小說家遇到素材」來理解,如果他不把「世越號的衝擊」看作是自己人生裡迫切的問題,便很難有這種專注力。
正如前所述,許多人都把這些衝擊看成影響人生的問題,因而付諸行動、改變了人生。我相信他們的轉變,會對這個慘不忍睹的韓國社會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金琸桓的《謊言》和《那些美好的人啊》,正是作者的寫作能力與世越號船難的衝擊在劇烈碰撞下產生的結果。因此,我們能藉此明白文學或小說作品在這轉變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也可看成在了解文學、小說在此過程中是以什麼型態存在時,十分重要的試金石。

2
《那些美好的人啊》收錄8篇以世越號為題材的作品,作者提到書中蘊含著「人與人相遇時瞬間的美好」,因此書名取作《那些美好的人啊》。但直至此刻,讀者對船難仍記憶鮮明,因而在閱讀這本小說時還是會揪著一顆心,那種「美好」依然飽含血淚。這種悲劇題材存在的現實性,從「習慣上」來看會妨礙虛構的小說。悲劇需要更長的時間去除美化,才能傳達事實本身,而這個悲劇可能被虛構得過早了。但如果這是在傳達悲劇的真相,卻有人阻礙我們分擔悲劇中主角的難過與痛苦,進而強迫我們保持沉默呢?無論如何,我們都應該將悲劇的記憶持續下去,讓他們的聲音傳到更遠的地方被更多的人聽到。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需要討論寫作種類的習慣嗎?我在讀過《謊言》後,寫下這麼一段文字:
戰爭或災難等巨大衝擊性事件很難馬上寫成形式虛構的小說,必須等事件的衝擊波消失、達到某種沉澱時,才能傳達出事件本身的衝擊。敘事手法可以採用直接的新聞、紀錄片或報導文學,靠理性的力量架構出整體意義,故事才能像慵懶的貓頭鷹,假裝沒有在觀察,實則卻睜著眼睛開始了敘事。從這點來看,也許《謊言》這部小說誕生得過早了,虛構性帶來的距離美,不僅凸顯出赤裸的現實,在與衝擊相撞時,也產生精神上的混亂與激情。
那是這部作品的缺點嗎?當然不是!正好相反,我只是從原則性來說明小說形式上的界限,形式不過是根據需求設定出來的。面對所有人的無動於衷,甚至在憎惡的情緒裡漸漸被遺忘、被強迫遺忘的「世越號船難」,可以透過一部小說把這歷史性的悲劇重新召喚回人們面前,去討論它的寫作類型又有何意義呢?
那些英雄不顧減壓症和心理陰影的危險,超負荷的潛入沉船,抱著一個個孩子出來,送回家人的懷抱。他們不但沒有獲得補償,還殘忍的被人們遺忘。《謊言》代替了那些「沒有嘴巴的存在」,道出民間潛水員的世界,從那以後,這炙熱的故事喚醒了世越號船難的「現存性」,我想說的是,不必把《謊言》框架在任何寫作形式裡。——2016.8.24,Facebook。
像這樣有必要表達出事件客觀性,同時作者內心也存在迫切想說出來的慾望,即便超越了寫作類型的習慣,本書收錄的八篇作品也並未草率的以船難當事人——即受害者本人和難以與他們分離的罹難者家屬——為視角發聲(以罹難者家屬為主角的〈贏了的人們〉除外)。作者也明白這些人的心聲仍被關閉在「不立文字」的世界裡,取而代之的是,他將與當事人有緊密關係的人設定成觀察者和敘事者,正因如此,這部作品的虛構寫作手法和美的距離才得以成立,能與直接傳達的報導文學區分。
〈眼神〉中的生還者,也是救下多條人命的救助者;〈不回來就是最棒的旅行?〉中的機場出入境海關,經歷了喪妻之痛;〈할〉中找到多名失蹤者的潛水員;〈濟州島來信〉中追憶罹難老師的生還學生;〈尋找〉中與罹難學生有密切緣分的攝影師;〈心留在這裡〉中,特調委員會解散後,仍堅持為生還學生進行心理諮商的調查官;〈小小的喜悅〉中,認為自己在靠寫罹難者的死出書而不斷自責的小說家,這些人正是觀察者和敘述者的素材。

接著,像這樣站在距離一步或半步的地方,將觀察者/敘述者與罹難者或家屬連結在一起,故事雖帶有原本的悲劇性,但作者期望「即便那個瞬間過於殘忍,充斥無法挽回的悲傷。但越過了生死的邊界,希望彼此能夠成為守護對方的防風林,帶來希望與美好。因為美好,才能擁有希望。」
在緊急狀態下擦肩而過的救助者與被救助者,透過眼神的記憶認出彼此(〈眼神〉);違背出入境安檢規章,為失去兒子的父親在孩子的護照蓋下出境章(〈不回來就是最棒的旅行?〉);潛水員不堪身心病痛決定自殺,卻再次挺身救人(〈할〉);生還學生一路追隨為救學生而犧牲自己的老師(〈濟州島來信〉);罹難者家屬為尋找事故真相,忍住自己的難過與痛苦,幫助律師參選國會議員(〈贏了的人們〉);被解散的特調委員會調查官,傾聽生還學生的心聲,幫助他與罹難學生的母親擁抱(〈心留在這裡〉)。這些故事在虛構與現實中穿梭,傳達故事中人們彼此相擁、相互珍惜的美好。正因如此,不僅展現了悲劇的一面,事實上也成功傳達出隱藏在此事件中,人類相互連結的里程碑。
當然,這些美好之中仍隱藏著血淚。
〈眼神〉的主角是生還者也是救助者,那天之後,他一直被惡夢、腹瀉和肌肉痛困擾。透過眼神記住對方的特別能力,或許也是那天的衝擊所致;〈不回來就是最棒的旅行?〉,海關人員因妻子獨自出國旅行遭遇不幸而陷入悲傷;〈할〉的潛水員因無法忍受骨壞死、腎功能衰竭和睡眠障礙而決定自殺;〈濟州島來信〉中,生還學生因事故陰影曾暈倒過14次,從此不敢再乘船;〈贏了的人們〉中,燦民爸爸期待玩偶裝能把自己送回那天以前;〈小小的喜悅〉的卓作家認為自己在利用他人的不幸創作而感到痛苦。我們很難區分虛幻與現實,因為所有人都痛苦不已。仔細想想,金琸桓在這似短非短的時間裡持續寫下船難的故事,也可以看成是他在表達自己的心理陰影。雖然這些小說中不斷展現出美好的人們的故事,但也可以看作是自那天之後,所有人再也抵擋不住外界的痛苦,各自尋找療癒之路的故事。
因此,在閱讀本書時,我幾度體會撕心裂肺的痛楚。加害者把真相丟進深海,不但遮住臉孔躲起來,還要責罵受害者,意圖把他們囚禁在黑暗中。為什麼要讓最痛苦的人找不到能尋求原諒的地方?為什麼要讓無辜之人互相尋求原諒、深陷痛苦呢?想到這裡,漸漸平復的憤怒再次湧上心頭。

3
一直以來,所有的故事都是記憶的工具,無論是傳說或民間故事這些小的敘事,或神話、史紀等大敘事,都是保存並傳播集體記憶的方法。小說是以個人記憶的保存、傳播登場的,但小說所保存或傳播的個人記憶並不代表那完全是孤立的、個人的,而是以個人的形式存在於集體中。
將近20年來,韓國的小說作品故意隱瞞了這樣的事實。身為人類的我們並非與生俱來就是為了傳承集體的命運而存在,最初我們都是對彼此漠不關心的個體。長期以來,這樣的人物形象一直存在於韓國的小說,也許這是因為過去20年歲月裡充滿了豐富的記憶和自由的幻象,以及人們對「集體」有著難以改變的厭惡。正因如此,這段時期的小說在集體或大多數主題中,都有意的將主角隔離出來,好讓彼此的關係變成像小島一樣孤立的存在。
這現象不僅體現於小說裡,整個世界都在把每個事件視為個人的榮辱,成功與失敗自然也看作個人的責任。但這種被我們視為「被孤立的個人世界」神話,不用多久便會原形畢露,當所有人只關注自己眼前的事,某種只能靠集體力量支撐或牽制的東西正一步步以敵對、危險的規模滋長,而如今它們正反過來讓我們這些被孤立的個人陷在困境中,束手無策。
如2009年的龍山慘案(용산참사,起因於首爾市針對龍山區的都更計畫,造成與不願搬離的被拆遷戶爆發警民衝突。2009年1月20日,不到50名的拆遷戶占據一棟大樓,與千餘名警察爆發激烈衝突,期間引發大火,造成6人死亡。),當時除了部分敏感的人,大多數人都沒意識到那次悲劇有可能也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他們只覺得事件慘不忍睹,卻依舊採取事不關己的態度。
5年後,世越號船難發生,在那個平凡的星期三早上,悲劇徹底演變成推翻被孤立的個人世界的大事件。這件在日常中發生、讓我們束手無策的悲劇,成為那些不曾思考集體問題的人們難以抹滅的痛楚。

文學是時代裡相較於其他意識中最為敏感的,龍山慘案後,作家開始思考「文學與政治」。自那之後的小說作品,慢慢出現個人背後龐大集體的影子。最初想要體現的目的應該是「記憶」,但這並非單純喚醒過去的回憶,而是積極解讀、反思的私人形式。如2014年韓江出版的《少年來了》,正是對光州民主化運動的記憶與哀悼,其中也蘊含反省與自責。這種寫實記憶的行為若沒有政治層面的覺醒,很難喚醒個人與集體、個人與組織的命運。這一連串以小說/文字體現的記憶行為,也可以視為是在深刻的反省過去20多年來如幻影般的個人主義時代。
世越號船難的傷亡規模和特性所帶來的衝擊是龍山慘案的百倍、千倍,它在這個時代人們的靈魂裡留下難以抹滅的痛苦。因此,很多人不是被動的記住這次事件,它就像紅字般烙印在人們腦中。文學更是如此,也許從這時起,韓國文學已經從世越號開始有了區分。金琸桓的「世越號故事小說化」可以看作「世越號之後」文學新世紀的開始,他特有的積極採訪能力和極具氣魄的筆鋒,寫下與那天有關的記憶與哀悼、反省與自責,更連結起受傷的人們,誕生了《謊言》和《那些美好的人啊》。
這珍貴的成果,或許會成為改變未來韓國文學品質的契機。
※ 本文為《那些美好的人啊:永誌不忘,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導讀,更多內容請參本書。
《那些美好的人啊:永誌不忘,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作者:金琸桓譯者:胡椒筒出版社:時報出版出版日期:2018/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