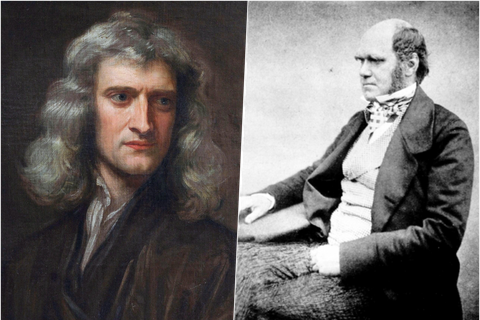被壓榨的一代:讀到博士,收入只夠填飽肚子

波林(Brianne Bolin)或如她要學生這樣稱呼自己的伯芮安教授,就像是隱形人。在我抵達位於芝加哥的哥倫比亞學院(Columbia College)、即她教授寫作課的地方後,我詢問前台的助理該去哪裡找她。「波林?」女助理一臉茫然地反問,並快速瀏覽了一遍教職員名單。「非常抱歉,我找不到這個名字。」上頭沒有波林.伯芮安這個名字,儘管這幾年下來,她每年都在學校開四門課,但她連個聯絡電話也沒有,更別提研究室。
原本想要帶我參觀校園的波林,匆匆趕到大廳。她將滿頭紅髮扎成馬尾,黑框學院風眼鏡左側靠太陽穴的地方,纏了一圈紅色電線絕緣膠帶;幾個月前這副眼鏡摔壞了,但她買不起新眼鏡。波林為了今天的會面,著實細心地打扮了一番:黑色背心(她後來告訴我這件衣服來自舊貨店)、牛仔褲(也是來自舊貨店),和一個解剖學風格的心型黃銅墜飾,用一條細細的黑繩串起,掛在她的脖子上。
對波林來說,這是一個難得且夢寐以求的夜晚——她有一個8歲但行動不便的兒子,名叫芬恩(Finn)。芬恩父親的未婚妻答應為她照顧孩子,但此刻的她情緒有些激動,無法好好享受這個難得的夜晚。她剛剛得知那名女子和芬恩的父親即將結婚,因此在婚禮期間他們將無法照顧男孩。又一次地,她只能靠自己。
在她向我展示了電腦實驗室和學生們的抽象攝影及錄像裝置後,我們為了談話而在學生休息室坐下來。那是一個擺放著現代時髦家具且能欣賞格蘭特公園(Grank Park)和密西根湖(Lake Michigan)絕美景致的地方。此刻,比起焦慮,波林更像是憤怒。作為兼任教授,每一堂課她可以賺4350美元,年收入則低於2萬4千美元。
在我跟她見面的時候,她的銀行帳戶裡只有55美元,待支付的信用卡帳單則為3000美元。她以975美元的代價,在芝加哥郊區一個沿著鐵路、每20分鐘就會有一輛火車呼嘯而過的地方,租了一間兩房的房子,而她已經欠了一個月的房租。她的書架上放滿了研究所時讀到、至今依舊能琅琅上口的詩集與哲學書籍,還有她搜集的1960年代法國黑膠唱片,而她卻只能依賴食物券來養活自己與兒子。
此外,由於她的工作不提供醫療保險,因此她們加入了由各州及聯邦政府針對貧困者所推出的醫療照顧計畫。而伊利諾州給予如芬恩這樣年紀孩子的保險補助,其家庭收入需受限於聯邦貧窮標線的142%:在2014年,此金額為2萬2336美元,在2017年則為2萬3060美元。這意味著波林的收入不能超過此金額。「事情不該如此的。」主修英文的波林,知道這句話就像是陳腔濫調,但她就是無法不去想這件事。
事情不該如此的。

大學時代,波林就讀位在遙遠南邊的東伊利諾大學(Ea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成日與書籍相伴,「和朋友住在拖車公園裡,讀著吳爾芙(Virginia Woolf)和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的小說,並為凱魯亞克(Jack Kerouac)及金斯堡(Allen Ginsberg)關於『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叛逆而癡迷,」她如此回憶。她獲得大學及碩士學位,修讀前衛詩詞。
她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為學術界的明日之星,畢竟東伊利諾大學不是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但她確實想過自己可以獲得一份薪水還過得去的穩定工作。「我喜歡美好的事物——我是小小中產階級分子,」她說。「我以為到了35歲的時候,我就可以穿著沒有破洞的衣服,銀行裡還有一點積蓄,但現在的我只能在慈善舊衣回收中心Goodwill購物。我穿著只要5塊美元的Banana Republic西裝夾克,而這些衣服總是很快就壞掉,畢竟之前早就經歷過其他人的磨損。是我的夢想讓我淪落至此。這不是什麼可恥的事情,但我確實無法不去想,我是不是哪裡做錯了。」
如今許多政治辭令談論著該如何拓寬人民觸及大學教育的機會(因為有充份的證據顯示,教育程度能提升經濟收入),但在歷經金融危機的世界裡,良好的教育並不能讓你免於在貧窮線附近徘徊。
在接受糧食援助或其他形式的聯邦救援人口中,擁有大學學位的人數自2007年到2010年間,成長了3倍;接受援助的博士學位持有者人數則從9776人上升到3萬3655人。具體而言,2013年領取食物救濟的家庭之中,至少有28%的家庭其成員中的最高學歷為大學以上。根據肯塔基大學(University of Kentucky)經濟學者的分析,此比例在1980年僅為8%。

高知識分子向下流動
如同波林之於她所任教的學校,高等知識分子貧窮者普遍藏在美國這個國家內。「沒有人知道或在乎那個住在拖車停車場裡的我,擁有博士學位,」住在俄勒岡尤金(Eugene)、撫養一名孩子、曾經在大學裡教語言學,如今卻依靠福利與食物救濟維生的兼任教授佩特拉(Petra),如此說道。明尼蘇達的圖資管理員和網站開發者米雪兒.貝爾蒙特承認,很少朋友知道她的經濟狀況如此窘迫。她說:「每一個美國人都認為自己是暫時經濟拮据的百萬富翁,我也不例外。」
這些教授與其他受過教育與培訓的工作者,面對的是中產階級流眾最典型的困境:債務、工作過量、孤立無援、以自己的貧困為恥。他們甚至沒有什麼休息時間,像是和伴侶喝著愛爾淡啤酒的約會,或和朋友談論自己的困境並交換八卦的聚會。他們幾乎不放假。
在這些人之中,許多人都表示儘管父母的學歷或許不如自己,卻擁有更好的經濟條件。當我在和這些中產階級流眾交談時,總會聽到他們不斷責備或嘲笑自己。追求崇高的職業與想要美好事物的欲望,難道錯了嗎?他們覺得自己錯了。他們的人生自然也不像那些年紀較長且生活更有保障的同事們,更遑論與自己原本預期的軌道,有多大的差距。
受過高等教育卻向下流動的大學教授們,並非偶然的現象。其他受人尊敬的職業,也正在失去昔日的光環。根據全美法律就業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Law Placement)的調查,法律系畢業生的就業率從2007年的92%下降到2012年的84.7%,並來到2016年的87.5%。而2012年法律學系生的平均負債金額為14萬美元,與2004年相比,上升了59%。
在經濟衰退期間失去工作至今依舊沒能重拾工作機會的行業,還包括了建築業、市場調查、資料分析、書籍出版、人力資源和金融——儘管這些工作的就業條件或吸引到的人口,往往是具有碩士學歷者。

對我而言,讓此種壓迫更為嚴重的元兇之一,是那句經常浮現在我們耳邊的呼告:「做你所愛」(do what you love)。這句話總是勸誘著中產階級,要他們勇於追求自己的夢想。出於好意的精神導師和企業們,頻繁使用這句格言。我自己也經常聽到這句話。那些總愛勸別人「做你所愛」的人,成功地讓自己看上去令人稱羨,並從底下的員工身上榨出更多勞力。
這則忠告的目的原本是想推翻過去總認為工作是一種職責、一種屈從而非激情的想法。工作對於一個人的人格,以及其內心對於重要性、價值觀的形塑,有著愈來愈顯著的影響。然而,有些歷史學家並不認為這是一種常態。反觀上一個世紀,人們之所以工作,往往是出於經濟壓力,而他們心目中的天堂,是一個不用工作、流著奶與蜜的土地。(貴族們自然是希望什麼事都不用做,憑著自己的家產而活。)
讓我們將「做你所愛」這句咒語代入眼前這一切;此刻,我就坐在龐大的共享辦公室WeWork桌子前,打著這段文字,而這句咒語醒目地印在這間公司的員工T恤上。我凝視著這句標語,期待那名此刻身穿著這件T恤、正在補充咖啡的年輕女子,能真的在某處實現這場美夢。我腦中想起許多自己認識的年輕與中年父母們,是如何遵循這句格言,卻導致自己不得不吞下那一言難盡的苦果。
如果我們所有人都做自己所愛,該如何生存下去?世界上的其他人又會變成什麼樣子?對於許多記者、新創工作者等那些雖不穩定但「具有創意」的產業員工來說,這句格言有時甚至具有某種強制性。這些工作的光環與聲望,就是這些以長工時換取低薪者的收穫。或許有一天,他們能即時發現以追求所愛之名,被迫做著那些根本不能帶給他們任何回報的工作。
當我在基於人生的種種壓力下、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創造力」以換取工作機會時,我這才明白:在堅持「做你所愛」的本質之中,隱藏著令人不舒服的階級歧視。假使深信「做你所愛」的信念其實來自一個擁有特權的社會身分、一個風險較低且失敗也不意味著賠上一切或人生終結的環境,那麼對於那些不擁有特權的人而言,為了實踐這句話會讓他們落得何種下場?

找一份「真正的」工作!
在波林非常年輕的時候,她就期望自己能和工作有緊密的連結。她生長在伊利諾州中部一個小鎮上,覺得自己和學校裡的孩子們非常不同。第一點,她是養女,也是家中的獨生女。最初,她通過測試並進入資優班,她的母親也驕傲地稱她擁有「令人畏懼」的智商(儘管在她進入青少年時期後,母親的詞彙變成了「難搞」)。進入高中後,她不太能適應學校,變得非常情緒化,總是穿黑色的衣服,並時常沉浸在閱讀中。
上了大學後,她很快就覺得自己找到了容身之地。「文學賦予生命另一番回響,」她說。接著在她升到大二時,她的男友令人震驚地被室友殺害了。這場悲劇讓她更常將自己埋藏在文學中,尤其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和喬治.奧本(George Oppen)的詩集。靈魂是什麼?她想著。男友的靈魂存在於某處嗎?「我以特有的方式,建立起我和這些作家的友情,」她說。「那時的我很孤單——現在也是如此,而書本能讓這個世界更美麗。」
然而,她說,學校裡的人從來沒有告訴她,踏入學術圈或許不是最明智的就業選擇。相反地,教授美國浪漫主義、也是她最喜歡的教授麥克.勞登(Michael Loudon),總是鼓勵她到辦公室裡聊天。(他現在退休了。)「他對我有信心:他知道我一定會繼續研究當時正在研究的題目,並寫出一篇論文。當然,他沒有想過我會擁有一份了不起的工作,但他認為我可以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這算是某種天賦。」
1975年,在勞登念大學的時候,獲得全職終身職(tenure-stream)的教授,占全美教授的45.1%。然而到了2011年,僅有24.1%的教授獲得終身職:也就是六名教授之中,僅有一個人能實際拿到終身職。像波林這樣的兼任教授或兼職教授只是附屬的,意味著他們屬於非終身聘用教師,因此這些受過良好訓練及教育的人,有許多面臨經濟困窘。

波林上大學時,這個現象開始發生,但她和父母並沒有察覺到這個趨勢。她的父親沒有上過大學,一輩子替泛世通(Firestone)製造輪胎;她的母親則是家庭主婦,擁有家政學學士學位。「早上九點打卡,晚餐時間回到家,」她如此形容父親。他的工作只是為了謀生,沒有其他意義,而他或許也不明白女兒為什麼要追求做自己所愛之事。
即便如此,當邁入20歲中期的波林於畢業後,立刻找到一份位於芝加哥韋斯特伍德學院(Westwood College)教寫作的教職時,用存款替她支付大學學費的雙親,對她刮目相看。一個學期後,她轉到哥倫比亞藝術學院任教。她希望能教文學,但她說自己也很喜歡基礎寫作,且樂於幫助學生精進寫作能力。
此外,芝加哥讓她感到興奮。她從未見過這麼多不同種族、不同國籍的人。她能日日夜夜聽到各式各樣的音樂,並尤其喜愛猶太傳統音樂克萊茲梅爾(klezmer)和巴爾幹的民族音樂。她甚至組了一個兩人樂隊,演奏樂器包括了手風琴、用海上旅行箱做成的低音樂器、一桶鐵鍊和一台打字機。「我在經濟上不算寬裕,但我就跟城市中那些26歲的人沒兩樣,和幾個室友合租房子,舉辦那些有現場演奏的派對,享受人生,」她說。「我沒有認真的伴侶,對未來也沒有計畫。我盡情揮霍年輕。」
接著,28歲的時候,她懷孕了,對方是一個20歲、來自她喜歡的樂團的隨性男孩。她知道養育孩子的責任將落在她一個人身上,但她說自己從未想過墮胎。然而,不幸的意外發生了:芬恩生來就因為腦性麻痺而不良於行。為了全心全意地照顧孩子,她辭掉工作長達數年,並搬回父母家中。她的母親以她為榮,但這次不是因為她是學者,而是因為她一肩擔起照料這個有著藍色大眼、一頭薑黃色頭髮、沒有人幫助便無法吃喝行走、一天之中需要數次將他那孱弱的身體從輪椅上移動到別處的男孩。
2008年,在芬恩兩歲時,波林回到哥倫比亞藝術學院,並盡可能地多開課。但她的老闆警告她,她或許永遠都拿不到終身職。「學術圈再也不是理想的職業選擇,」波林說道。那些批評她「被擊倒」、指責她因為「未婚生子」而落得這般下場的人們,並沒有給予她任何幫助。這些令人反感的反對者,和波林沒有任何關係,然而這些令人痛苦的言論,無法改變她的人生軌道。她的處境已然定型。她隸屬於一群除了能獲得父母或網路社群些許幫助,社會根本無法給予他們半分援助、而他們對未來早已茫然若失的族群。對於這種困境的其中一個反應是:
忘了你自己!找一份能繳清帳單的工作!
「為了照顧孩子,擔任兼任教授可能會累積大量債務,」她指出,而這個過程「讓他們必須奔走於五個校園間,摧毀了他們的健康,並陷入惡性工作迴圈。如果你已經盡力嘗試了,那麼是時候該邁出新的一步了。」她幫助那些無法走上終身職這條路、或最終沒能獲得終身職只好從頭開始的研究所畢業者,找出市場可能需要的分析、資料蒐集、寫作、公開演說等技能。

當收入只夠填飽肚子
波林的困境不僅僅肇因於時間不夠用。如同社會心理學家針對已發現的「決策疲勞」(decision fatigue)所做的研究,作為貧困者需耗費極大的心力。即便金額再低,他們仍舊需要持續針對所有開銷進行衡量,像是:沒錯,或許我應該多買幾塊正在大減價的肥皂(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家曾在貧窮的印度農村進行此一實驗),但如此一來就無法負擔這個星期的藥品或食物了。
與波林一起走在那個對她而言只會讓她自慚形穢且超過她消費能力的喬氏超市裡,我見識到了要想讓開銷維持在食物券所補貼的349美元範圍內,是一件多麼令人筋疲力竭的事。只有在夏季不上課的時候,波林才有資格申請食物券補助。此外,當她的月收入低於2000美元時,她還可以申請600美元的社會安全生活補助(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由於患有乳糖不耐症的芬恩只能喝昂貴的杏仁奶或米漿,因此波林只能買每磅59美分的量販雞腿包、一袋49美分的紅蘿蔔,以及單位價格最便宜的牛絞肉。「我曾讀過一篇部落格文章,指出人們是如何浪費20美元在快照服務或高級的起司上,」她說。「我絕對不會那麼做。」
當最基礎的生存都需要耗費如此多的心力時,已經沒有多少餘力可讓他們進行長期規劃或鼓起勇氣——如波林知道自己該做的那樣。「我必須靠抽菸來紓解壓力,」她說,一邊熱切地捲著自己的菸。訪談的那個晚上,我約她在酒吧碰面,而她發現除了香菸外,大量的瑪格麗特也能緩解壓力。她說總是自己吃藥;平時,她會使用鎮定劑Xanax來對抗焦慮。她還會每天服用抗憂鬱藥。如同2015年因為在部落格中赤裸寫下自己的最低工資生活而引起全美轟動的琳達.提拉多(Linda Tirado),在自己那本《當收入只夠填飽肚子》(Hand to Mouth)所寫的:
拚命工作卻很窮真是他媽的讓人崩潰。
過去,教育曾經是進入中產階級生活的管道,如今卻再也無法扮演這樣的功能。學術圈和其他領域的工作要不是陷入危機,就是瀕臨滅絕。波林就跟許多人一樣,緊緊攀附在那已經岌岌可危的階級邊緣。
※ 本文摘編自《被壓榨的一代:中產階級消失真相,是什麼讓我們陷入財務焦慮與生活困境?》,第二章〈高學歷無用?〉,更多內容請參本書。
《被壓榨的一代:中產階級消失真相,是什麼讓我們陷入財務焦慮與生活困境?》作者:艾莉莎.奎特(Alissa Quart)譯者:李祐寧出版社:八旗文化出版日期:2019/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