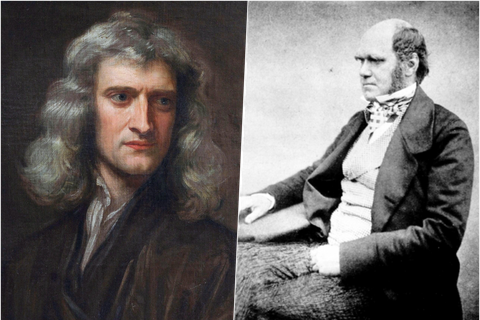《動盪》: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必然取決於國家領導人?

在談論國家危機時,人們常提出的另一個問題,長久以來一直都是辯論的主題——國家領導人是否會對歷史產生重大影響?抑或在特定的一段時間之內,不論國家的領導者是誰,歷史還是會以相同的方式發展?
國家領導人,是否會對歷史產生重大影響?
這種討論的一個極端,是英國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所謂的「偉人史觀」,他主張歷史是由偉大人物的行為所主宰,如奧利佛.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和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當今的軍事史學家仍有類似的觀點,他們經常強調將領和戰時政治領袖的決定。
與此相反的極端是作家托爾斯泰,他認為領袖和將領對歷史過程的影響微乎其微。為了表達他的觀點,托爾斯泰在小說《戰爭與和平》中描寫了虛構的戰爭情節,將軍雖下了命令,但這些命令與戰場上實際發生的情況並無關聯。
歷史的過程取決於許多細節,而非靠偉人的政策或決定,很多當今的歷史學家都持這種觀點。他們主張,領袖只是因為他所採取的政策與其同胞的觀點有了共鳴,才具有影響力。原本平凡的政壇人物可能因為他們當時掌握的機會,而非因為他們的個人特質,才顯得偉大。常舉的例子是美國總統詹姆斯.波爾克(James Polk)和哈利.杜魯門(Harry Truman)。領袖只能由其他歷史因素決定的有限選項中做出選擇。
介於偉人史觀和領導人毫無影響力中間的一種觀點,則可以舉德國社會學者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的看法為例,他主張在某些情況下,某些類型的領導者,即所謂的魅力型領導者,有時會影響歷史。
這個辯論還沒有結果。每一位歷史學者都抱持某種根據原則、而非有效方法的概念,對經驗證據進行評估,並把這種觀點應用於個案研究。例如所有關於希特勒的傳記都必然會重述他一生中同樣的幾件大事。
但主張「偉人史觀」的人在敘述這些事件時,斷言希特勒是異常有影響力的邪惡領導人,他使得德國的發展與由其他人領導的結果不同。反對「偉人史觀」者也會敘述相同的事件,但卻把希特勒描繪成反映當時德國社會普遍特色的聲音。這樣的辯論無法藉由敘述和個案研究來解決。

獨裁領袖死亡的影響,比民主領袖死亡的影響大?
另一方面,最近有一種分析方法有解決這個問題的可能,它結合了三個特徵:許多歷史事件的大型樣本,或者某種特定類型的所有歷史事件;使用「歷史的自然實驗」,即比較在其他方面都相似的歷史軌跡,其中發生或未發生某種擾動(下面將舉出兩例);並測量其數量方面的結果。
西北大學的班哲明.瓊斯(Benjamin Jones)和麻省理工學院的班哲明.奧肯(Benjamin Olken)已經就這方面發表了兩篇傑出的論文。瓊斯和奧肯在他們的第一篇論文中問道:領袖在位時因自然因素而死亡,國家經濟成長率會發生的變化,和在隨機選擇的時間,在位領袖並未因自然因素死亡時所發生的變化,有什麼不同?
這種比較提供了自然實驗,測試領袖改變時的影響。如果偉人論的觀點正確,那麼比起領袖未死亡的任何時候,領袖死亡時的經濟成長率應該較可能隨之改變——無論下降或升高,分別取決於領導人的政策好壞而有不同。
瓊斯和奧肯的資料,取自1945年至2000年間舉世國家領袖因自然因素而死亡的例子,總共提出了57個這樣的案例:主要是因心臟病或癌症而死亡,另外還有幾例墜機、一例溺死、一例落馬而死、一例被火燒死,和一例斷腿而死。
這些事件確實構成了隨機擾動:領袖的經濟政策不會影響那位領導人意外淹死的可能。結果證明,比起隨機選擇領袖未死亡的時刻,經濟成長率更有可能隨領袖自然死亡而改變。這表示由許多案例平均來看,領導階層確實會影響經濟成長。
瓊斯和奧肯在他們的第二篇論文中問道:如果領袖是遭人暗殺,死於非命,會有什麼結果?當然,暗殺事件絕非隨機事件:它們更有可能發生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如果人民對經濟成長低感到不滿意),而非其他情況下。因此瓊斯和奧肯把成功的暗殺與不成功的暗殺嘗試做了比較。
這確實是隨機的差異:國家的政治情況可能會影響暗殺企圖的頻率,但不會影響刺客的準頭。他們收集的資料,包括由1875年至2005年對國家領袖所做的298次暗殺企圖:其中59次成功,239次未遂。結果證明,比起暗殺未遂,暗殺成功後,國家政治體制更可能會有所改變。
在這兩項研究中,獨裁領袖死亡的影響都比民主領袖死亡的影響大,而且權力無限的獨裁者死亡的影響,比有立法機關或政黨限制的獨裁者死亡的影響更大。正如我們所預期的:擁有無限權力的強大領袖產生的(無論好壞)影響,比權力有限的領袖更大。因此,這兩個研究達成了一致的結論:領導者有時會造成不同。但這取決於領導者的類型以及所檢視的效果類型。

七個國家的領導人角色
現在,讓我們把這些自然實驗與書中七個國家的領導人角色連結起來。我的目標是要了解本書的領導人是否符合瓊斯和奧肯所確認的模式,以及他們進一步提出的測試問題。許多歷史學者對我們書中七個國家的領導人做出以下的評價:
在明治日本,沒有單一主導的領袖;而是由幾位領導人共有類似的政策。
在芬蘭,政治領導人和公民幾乎一致同意,芬蘭應該盡最大努力抵抗蘇聯的攻擊。(但有時候史學家認為,曼納海姆元帥擔任軍事指揮官的技巧,以及巴錫基維和凱科寧兩位總統在戰後贏得蘇聯領導人信任的能力,對芬蘭的命運有正面的影響。)
至於智利,歷史學者認為皮諾契特的殘酷、掌握權力不放的堅決,和他選擇的經濟政策都果斷而不尋常(甚至連他的將領也作如是想)。
在印尼,蘇卡諾和蘇哈托都被認為是關鍵的領袖,但接下來的總統卻不然。
在戰後德國,學者通常認為布蘭特發揮了獨特作用,扭轉先前西德政府的外交政策,承認東歐共產主義政權和德國國界,因而使德國隨後的統一成為可能。在較早期的德國歷史上,俾斯麥、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經常被當成獨特領導人的例子,無論在好或壞的方面,都影響深遠。
在澳洲,並沒有明顯占主導地位的領導者。最接近的例子是惠特蘭總理和他的旋風變革計畫,但惠特蘭本人卻承認,他的改革是「承認已經發生的事」。
在美國,小羅斯福總統因不顧美國孤立主義者(最初可能包括大多數美國人)的反對,逐步為美國參與二次大戰做準備,以及帶領美國擺脫經濟大蕭條的努力而受稱頌。在十九世紀的美國史上,林肯總統也被認為在內戰過程中扮演了獨特的角色。
簡而言之,我們的七個國家提供了九個領袖(六個專制,三個民主)的例子,人們常認為他們發揮了影響力,造成了改變。此外,在本書討論的七個國家之外,最常被認為在現代史上造成影響的領導人包括英國的邱吉爾、蘇聯的列寧和史達林、中國的毛澤東、法國的戴高樂、推動義大利統一的加富爾,和印度的甘地。
因此,我們列出了16位通常被認為締造改變的領導人名單。在這16人中,11人屬於專制政權,5人則屬民主政體。乍看之下,這個結果似乎符合瓊斯和奧肯的結論,認為獨裁政體的領導人影響更大。
但我並未把這段時間內全球所有獨裁和民主領導人的相關數字列表,因此我不能斷言(如果有),哪一種領導人的數量有比例懸殊的影響。

步步為營推行自己觀點的領導人,發揮的影響最大
我們的小型資料組確實提出了兩個假設,值得透過類似瓊斯和奧肯的方法來測試,集合包含自然實驗的大型資料組,並用數量來測量結果。一個假設來自於這樣的觀察:在四位最常被認為具有獨特影響力的民主領袖(羅斯福、林肯、邱吉爾和戴高樂)中,至少有三位是在戰爭期間產生了影響或最大的影響。
林肯的總統任期幾乎都是處於美國內戰期間。邱吉爾、羅斯福和戴高樂在職時既有戰爭,也有和平時期,但公認其中兩位或全部三位都是在戰時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邱吉爾是1940至1945年二戰時的英國首相,但並非1951至1955年和平時期的首相;戴高樂在二戰時擔任將領,隨後在1959至1962年阿爾及利亞暴動期間擔任法國總統;羅斯福則是在1939年二次大戰在歐洲爆發後,以及大蕭條時期擔任美國總統。
這些結果都符合瓊斯和奧肯的觀察:影響力較大的領導人,其權力的限制愈少;民主制度的領導人在戰時行使更集中的權力。
另一個結果要進行測試的假設是,在面對擁護不同政策者強烈反對的情況下,步步為營,最後推行了他們自己觀點的領導人(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獨裁國家),發揮的影響最大。
例如:薩丁尼亞王國總理加富爾和普魯士總理俾斯麥分別克服外國勢力、其他義大利人或德國人,甚至他們自己國王的強烈反對,逐漸實現義大利和德國的統一;邱吉爾說服了最初意見分歧的英國戰時內閣,拒絕哈利法克斯勳爵提出和希特勒和談的建議,接著又說服美國,把他們的首要任務放在對抗德國而非對抗日本的戰爭(在日本襲擊珍珠港之後,原是美國的當務之急)。
羅斯福不顧美國孤立派的反對,逐步為美國參加二戰做準備;戴高樂慢慢說服他的同胞和阿爾及利亞人,透過談判解決阿爾及利亞爭取獨立的抗爭;蘇哈托慢慢地排除印尼人民摯愛的首任總統蘇卡諾;和布蘭特說服西德人民不顧已連續執政達二十年基民黨的激烈反對,吞下放棄前德國領土的苦果。

從國家危機歷史中,我們學到什麼?
如果我現在已經說服讀者,不要忽視我們可以由歷史中學到實用教訓的可能,那麼我們可以由本書中討論的國家危機歷史中學到什麼?許多一般性的主題已經出現,其中一組主題是由協助書中七個國家面對危機的行為組成。
這些行為包括:承認自己的國家置身危機;承擔改變的責任,而非只是指責其他國家,自認為是受害者;建立圍籬,識別需要改變的國家特性,以避免不知所措,以為國內的一切都無法適當運作;確定可以向哪些國家尋求幫助;確定已經解決類似問題的其他國家所採用的模型;耐心等待,並明白第一個解決方案可能無法奏效,可能需要連續進行幾次嘗試;反省哪些核心價值仍然合適,哪些則不再恰當;以及誠實地自我評估。
另一個主題則和國家認同相關。年輕國家需要建立國家認同,比如印尼、波札那和盧安達。歷史較久的國家,國家認同則和核心價值一樣,可能都需要修改;近代的澳洲就是一例。
還有一個主題則是會影響危機結果的不可控制因素。一個國家難以擺脫其先前解決危機的實際經驗,以及其地緣政治的限制,無法突如其來創造更多的經驗,也不能幻想地緣政治的限制會消失。但是,國家仍然能夠實際地考量它們,就像在俾斯麥和布蘭特領導之下的德國一樣。
悲觀的人可能會反對這些建議:「這太顯而易見,簡直荒唐!用不著賈德.戴蒙的書來告訴我們要誠實地自我評估,向其他國家借鏡,避免受害者心態等等!」
錯了,我們確實需要一本書,因為不可否認的是,這些「顯而易見」的作法經常遭到忽視,而且迄今依舊經常受到忽視。過去因忽視「顯而易見」的作法而犧牲性命的,包括所有米洛斯男子、數十萬巴拉圭人和數百萬日本人。如今因為忽視這些「顯而易見」的作法,而威脅到自己福祉的人,也包括我的數億美國同胞。
悲觀主義者也可能會回應說:「是的,遺憾的是我們確實經常忽視顯而易見的事,但光憑一本書無法改變那種盲目。修昔底德的『米洛斯對話』已經存在了兩千多年,但世界各國仍然犯同樣的錯誤,就算再多一本書,又能有些什麼好處?」
我們作者為什麼繼續努力寫作,有令人鼓舞的原因。比起世界史上任何時候,如今識字的讀者多更多,我們對世界史的了解比以往多得多,提出有證據的論證也可以比修昔底德好得多。如今有更多的國家是民主政體,這意味與過去任何時候相比,當今都有更多的公民可以表達政治意見。雖然愚昧的領導人比比皆是,但有些國家領袖閱讀廣泛,他們在現在比以往更容易由歷史中學習。
我曾多次見到國家元首和政治人物,驚喜地聽到他們告訴我,他們受到我先前著作的影響。整個世界現在都面臨全球問題——但在過去這一個世紀裡,尤其是在最近幾十年內,世界已在發展解決全球問題的機構。
基於這些理由,我不聽悲觀者之言,放棄希望,而是繼續執筆不輟,為的是只要我們願意,就可以由歷史中學習。尤其是,在過去國家經常要面對危機的挑戰,今天雖然依舊如此,但現代國家和現代世界在嘗試回應時,不必如以往在黑暗中摸索。了解過去曾經發揮作用與否的改變,可以為我們提供引導。
※ 本文摘自《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結語,更多內容請參本書。
《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作者: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譯者:莊安祺出版社:時報出版出版日期:2019/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