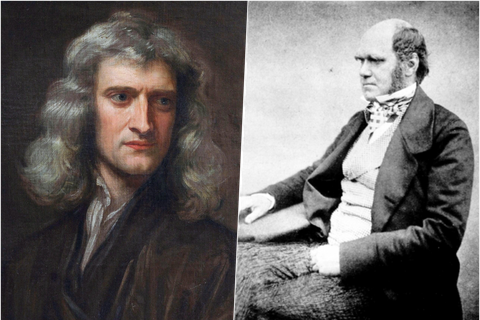憎惡與恐懼,難道能輕易遺忘?——韓國生死邊界的急診故事

『我有些感冒所以來看醫生,有一點咳嗽跟痰,大概過了一個禮拜了,已經。我因為有些疾病,所以還滿常跑醫院的。』一個30歲左右的女性患者,戴著口罩遮住大部分的臉,僅僅用一雙惡狠狠的眼睛看著我說道,那句「已經」,是多麼具威脅感啊。
「剛剛幫你量過體溫,沒有發燒喔,聽說昨天另一家醫院也說沒有發燒,對吧。」『可是,我身邊的人都說我好像看起來有發燒啊,所以我自己也覺得應該有吧,這個自己應該可以感覺得到吧。』「你應該沒有吃退燒藥吧。」『沒有。』「讓我來看一下吧。」
不管怎麼測,兩耳測出來的體溫都沒有超過37度,肺部的呼吸聲音聽起來也挺正常,X光片也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問題,持續一週左右的話,我覺得應該只是單純的支氣管炎。
患者的恐懼
「好的,這位患者……」『啊,請等一下,我現在要把醫生你講的話錄下來,如果我之後發生什麼事,總要有人負責才行啊,還有你講的我可能會忘記,錄音也可以再重新聽一次,如果我變成重病,之後總要留下一些證據才行啊,這樣應該沒關係吧?』「嗯……那你請便吧。」
雖然感覺不是很好,但也沒有理由拒絕,在等她弄好錄音準備時,我摸著無辜的診療室電腦螢幕,內心覺得不太舒服,電腦螢幕上的滑鼠游標些微顫抖著。
在這段時間,她東弄西弄按著手機準備錄音,『可惡,這錄音按鍵……』自言自語的,她花了好長一段時間在弄手機。診療室彌漫著一陣尷尬的沉默。『好了,可以了,請說吧。』她把手機放在診療室的書桌說道。
好的,患者你現在的咳嗽、痰等症狀,看起來應該是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狀而已,而且也沒有發燒,X光片上或是聽診時聽到的聲音也都相當乾淨,沒有異常。我想你的症狀是持續比較久的支氣管炎,我會根據一般支氣管炎開適合的藥給你吃,好好休息的話,應該會沒事的。
『嗯,不是MERS嗎?醫生你應該要確實地說這不是MERS才行啊。』我都不知道我是在跟患者說話,還是跟錄音機說話,內心感覺十分混亂,完全沒辦法不去在意那個手機,而且手機上錄音功能顯示著正在錄音,目前已經錄了幾分幾秒,當我的嘴一張開發出聲音,錄音機的紅色音量波峰又升了上去。
患者你曾去過的醫院,直到三小時前我們都未收到疾病管制局傳來發現有MERS患者,或是出現在曾治療過MERS患者的醫院名單上面。而量你體溫時也沒有發燒的症狀,目前為止根據國家公開情報與方針,因為所處地區並非感染區,感染機率幾乎微乎其微,你也沒去接收MERS患者的醫院,因此院內感染的機率也相當低,依據國家標準來看,這樣的狀況很難判定您為MERS患者。根據國家規範的基準來看,我認為予以一般感冒來治療即可。
老實說,我是很想說「我個人意見」來看是沒關係的,其實,這不也是個人的判斷,不是嗎?但是比起她的疾病,我現在要站出來對抗的,是我的聲音正被錄音、遲遲沒有進展的責任問題,以及患者的恐懼。如果說出自己的意見「嗯,我認為既然如此,就再看看吧」這樣的話也很正常啊,不,一開始在診療時不就這樣說了嗎?
反正這樣的作戰方式應該有效,說任何話之前都將「國家」兩字掛在嘴邊,原本不信任又銳利的眼神看似已經漸漸鬆懈,大概以「國家」規範的基準為起頭,聽起來更具有說服力,雖然希望透過眼前這位醫生診療得到沒有感染MERS的豁免權,但眼前的醫生不斷反覆著大義基準,似乎獲得更大的豁免權般。

拿「國家」當擋箭牌
就在我才以為自己正從被攻擊的身分脫離的瞬間,『好,那也請回答這個問題,』即使不這樣也已經放得很近的錄音機,朝我推得更近,她這樣說:『明天我要去濟州島,一整個週末都會在那邊。聽說濟州島也有MERS患者,我如果去濟州島,也不會得到MERS嗎?或者,去的話,會對我健康造成絕對性的威脅嗎?請醫生也確實地回答這個問題。』
她說話的語氣與眼神顯得趾高氣昂,似乎是在說「想要通過我這關,試試看啊」,這是最後一個關卡,如此理直氣壯的提問!
我知道有一位患者曾去過濟州島,投宿在新羅飯店約三天,雖然新羅飯店不是醫院,但擔心暴發感染,所以目前為封鎖狀態,其他地區依「國家」規範指針來看,感染率幾乎為零,因此依據「國家」指導方針原則,只要不要接近新羅飯店附近,到濟州島旅行相當安全。
『啊,原來如此,這樣就可以了。謝謝,那我先回去了。』呼,終於!她拿著手機離開診療室。我拿著「國家」當擋箭牌,而且幸好空閒時有仔細詳讀MERS的新聞,真是太有幫助了。
呼,現在只要想起那雙惡狠狠的眼神,雙腿還會有些發抖,全身汗毛直豎呢。看看時鐘,竟已經過了30分鐘,因為要確認各個MERS患者曾去過的醫院,和進行各種傳染性預防程序,必須花比平常更多倍的時間解釋說明,還要被錄音。
可是,仔細想想,這不過是個感冒的患者不是嗎?為什麼我得遭受這種審問呢?我有做錯什麼嗎?難道在這時局、坐在這個位置,照顧病患是一個錯誤,必得成為標靶嗎?我感受到的是對我的不信任與厭惡,被第一次見面的患者突然拿槍瞄準,用那銳利的視線惡狠狠地看著不清楚狀況的我,而且還是對著在非常時期站在第一線、仔細且小心戴著悶得要命的口罩、將不安感隱藏起來老實看診的我。
這是我應該受到的待遇嗎?難道這是一定要克服的試煉嗎?我停止思考,決定不要再想下去了,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憎惡與恐懼,難道能輕易遺忘?
MERS造成全國喧騰,共有186位患者確診,共38名患者死亡,與病毒有關情況,在騷動後日趨平靜,最後正式宣告終結,在大眾心中也逐漸被遺忘,但是對於被確診的患者、倖存下來的5千萬名的人們心中,一定留下些什麼。
對於摸不著無形死亡的恐懼、憎惡,需要有人出來負起責任,對於陌生人近似輕蔑的不信任,這可惡的病毒,找到人類的弱點與惡的位置鑽了進去,如同病毒一樣滲透到我們的內心,攪亂我們、挑撥著我們好一段時間。
之後好好活下來的那5千萬名人們必須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那一年初夏,在我們的內心,難道只留下了混亂不安嗎?那一年,戴著悶熱口罩的我們,所感受到的那份憎惡與恐懼害怕,難道能輕易遺忘?
※ 本文摘自《雖然想死,但卻成為醫生的我:徘徊在生死邊界的急診故事》〈我們無法感受的孤獨〉,更多內容請參本書。
《雖然想死,但卻成為醫生的我:徘徊在生死邊界的急診故事》作者:南宮仁(남궁인)譯者:梁如幸出版社:時報出版出版日期:2020/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