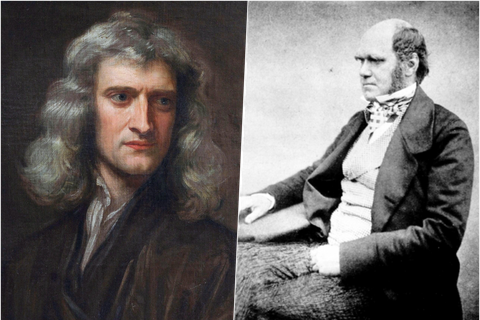記憶中的家,還能重來嗎?——日本311大地震之後

2014年2月,低氣壓籠罩日本列島,大雨和暴雪輪番侵襲,癱瘓了這片土地。雪災結束才沒兩天,我飛抵東京,只見日頭將首都打得晶亮,路邊則無一抹殘雪,遑論雪災的痕跡。這城市復原的速度,讓人吃驚,我因而有理由相信,東北那塊海嘯刷過之域,肯定也回復原樣。這刺眼的陽光,就是寒冬即將過去的清朗證明。
畢竟,距離那場災難,已過了三年。但老天爺像要反駁我的樂觀一樣,新幹線一抵達福島,大雪就急急落下,稍早的日照如夢一場。我們吃力走過雪堆,再回到車站隨便找個拉麵店坐下時,天已暗黑,專注讀著菜單的伙伴突然抬頭:「沒有問題吧?」
這個問句聽起來語意不清、沒頭沒尾,但因為這個時間這個地點,不需多餘解譯,就能讓人心領神會。我忍不住偷偷看了吧台後方的店員一眼:不知道福島人該如何承受這無法結束的懷疑?
「當然沒問題。」楊明珠低頭剝開筷子,用一種吃飯時間就是要吃飯的肯定語氣回答:「這裡離核電廠這麼遠。」


羽生,金色的勇氣
這些年,媒體乃至台灣社會對這場災難的關注,只剩核災。或許因為天災的傷害終究會被時間沖淡,輻射的影響卻可能永遠被留下來。福島就像車諾比,成為一個永遠洗不清的汙名,一輩子都會讓世人擔心。
楊明珠理解這些「擔心」,卻不見得能接受。即使菅直人政府失足釀禍,她仍對這國家的控管與素質抱持信心,「有誰比日本人更在意這場災難?但是,他們還是願意吃這裡的食物,還是在這裡。」拉麵的熱騰霧氣蒸暖了我們的眼睛,楊明珠提起東電曾開放讓媒體參觀,她獲得珍貴的機會卻不能去,感到非常遺憾。作為記者,她寧可眼見為憑。
我對「看不見」的東西也沒有多餘的感覺。三年前,首次進東北災區,大巴士行經福島時加速前進,慈濟志工們每到一個點就拿出儀器探測輻射濃度,宣告沒事。看著大家鬆口氣的表情,我有些事不關己;此行,若非伙伴遲疑一下,我也沒注意到此地的特殊性,或許我潛意識裡從未認真看待這個危機。況且,受災也不是這裡的人願意的。
比起我們這些「過客」,久居日本的楊明珠很自然地與這塊土地上的人事物同聲共息,傷心他們所傷心的,相信他們會相信的,支持他們所支持的。例如這幾天是索契(Sochi)冬季奧運,她也得關注日本選手的表現,而這些選手確實優異,讓她一邊採訪三一一重建進度,還要每天熬夜發冬奧新聞。
「羽生結弦表現得真好。」她將正在看的報紙湊到我眼前,解釋年輕的花式溜冰選手在這場災難即將滿三周年之際,奪下金牌,讓整個日本振奮。
因為,他的成功,對整個重建區具有象徵性的意義。羽生結弦是仙台人,海嘯發生時,他才高一,是個十六歲的孩子,不免感到恐懼和無助。「當生存遇到問題,運動就成了奢侈的夢想」,在收容所裡他與家人擠在兩個榻榻米的空間,只擁有一床毛毯,感受周遭人們的苦楚。他時常盯著天花板想:現在已經不是滑冰的時候了……。
十天後,當他寄居在教練家裡重新練習時,面對的是沒有腿部肌肉、做不了跳躍的身體。災後一個月,仙台出現規模六的餘震,遠在橫濱的他在冰場上感覺到震動時,內心幾乎崩潰,對教練說:「我好累,這種狀態下,真的可以繼續嗎?」失去自信的他,兩天後在經歷過阪神地震重創的神戶演出時,被現場觀眾的喝采鼓舞,心想:「如果神戶都能重建,仙台也可以。」
災難的經驗,讓他產生與其他選手不同的企求,除了獲勝之外,他更希望冰場上的表現能給予災民勇氣。因此,在索契冬奧這個國際賽場上,他刻意挑戰高難度動作,心想如果能夠在這個舞台完成這件事,代表三一一地震重建有望。
羽生結弦確實成功了。奪金後,他對媒體表示:「一直到今天,我都有一種無力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重建中發揮作用。得到奧運金牌,就像一切才剛剛開始那樣。我感覺一定能為災區做點什麼。」
因此,媒體在頭版打上斗大的標題:「羽生,金色的勇氣」。這位年輕選手的意念,不只傳給災民與同胞而已,災難發生以來,始終理性以對的楊明珠,同樣因此眼眶泛紅。「看到這些新聞,我就忍不住,完全克制不了內心的激動。」
我本以為這只是單純的粉絲反應,卻聽她輕聲解釋:「三年前跑這些新聞的時候,我一直很投入,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心裡被劃了道傷口,也沒有什麼情緒,但現在只要看到地震相關新聞,我才發現內心的創傷,一直很想哭。我以為只有我這樣,前幾天,跟新華社記者聊起,才知道,我們都一樣。」
等待重建、需要勇氣的,恐怕不只有災民,還有每一個被災難劃出傷口的人。


海嘯,摧毀了這一切
對經歷過災難的人和土地而言,時間沒有意義,傷痕還很深,盡頭依然遙遠。就像現在,這個土撥鼠準備探出頭的時節,三陸沿岸仍是黃土裹著的風景,像寸草不生的荒地。跟三年前相比,僅僅少了堆疊起來的廢棄車輛、垃圾、土石,與四散的生活用品;但又比過去多了待整的土堆、工地的圍籬,還有不斷咆哮著的工地機械。
站在福島縣新地町公所頂樓往外望,除了一大塊土黃色格子拼成的土地外,再無其他。如果對這裡的一切毫不知情,很容易會將它錯認為收穫過後,等待播種的土地,以為春天來臨,色彩就會不同。但現實是,這直直往海邊延展,平坦且毫無長物的黃,已經維持整整三個春夏秋冬,就連新地町居民都會忍不住想,過去那樓房成列的熱鬧市鎮,莫非是幻影?
海嘯,摧毀了這一切。
海嘯來的那天,新地町健康福祉保健課課長大崛勝文就在這樓頂協助四、五十位民眾避難,危急之時,無意識地將視線投向窗外,只見海水從遠處夾帶垃圾、房子和大量黑色粉塵襲捲而來,就像災難電影那樣。滾滾大水順著役場旁的砂子田川長驅直入,於他腳下翻滾。而這裡離海,有將近三公里距離。
「直到今天,我都說服自己那只是一場夢。」大崛勝文聲音輕輕的,如夢話呢喃,我必須要非常靠近,才能聽清楚。面對我疑惑的表情,他也不多說什麼,只是將視線繼續投向遠方,兀自沉默。
三一一即將屆滿三周年之際,我隨紅十字會再赴這塊海嘯吞噬的大地,一一拜會三陸沿岸的地方政府,瞭解重建進度和成果。但無需這些公務員開口,光靠自己的眼睛就能明白困難非常。如果這場災難是一場夢,災後一千個日子過去,早該是重建開展、生活定序的夢醒時分,但整個重建區顯然還沒從這惡夢裡脫離——就連我這外人都懷疑自己困在時間的結界裡——地方政府的無奈和居民的焦慮不斷發酵。
以距福島第一核電廠約58公里遠、一小時車程之久的新地町為例,這個人口超過八千、計622戶人家受災的小鎮,幾乎毫無重建進度可言,大部分居民還住在組合屋裡。
「民眾當然希望盡快回復正常的生活。」都市計畫課住宅科科長千葉秀一與大崛勝文坐在會議室中,跟我們聊到重建進度時,嘆了一口氣。他們身上的白色襯衫絲毫無助於氣色,面容始終黯淡,眼球血絲更是明顯。我對這種疲累表情並不陌生,三年前就已經見過。重建的擔子,沉沉地壓在這些基層公務員肩上。


記憶中的城鎮無法全然重來
如同「重建」字面上的意思,「重新建造整座城鎮」本就是個難題,因為這不只是把房子蓋起來而已,從車站到整個交通系統的建立,整個城鎮的生命線都得重新鋪起。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看不見的城市》裡寫道:不管怎麼樣描述一個城市都是徒勞無功的,因為組成一座城市的,不是台階、拱廊等等物件而已,「而是空間的量度與過去事件之間的關係」。
人們對家鄉的愛戀,建立在記憶上,但災後重建的現實則是,記憶中的城鎮無法全然重來,只能盼著恢復「居所」。而日文所說的「居所」,並不只是住屋而已,還包含「歸屬感」。換句話說,是一種底定的生活感,一種家的感覺。
「大家都想要盡快回復原本的生活。」公務員們搖頭,這並不容易,因為重新造鎮要找土地,得解決私人用地問題,而民眾也不敢住在低窪地區,必須在高處找地重建,同樣面臨選地、整山及私人用地問題。他們試著對我們解釋重建的每一步,步步都是難關,「如果都能解決,進度就可以快一些,但是……。」
這時候,我並不知道,接下來所有拜會採訪,將會充滿各種「但是……」。

※ 本文摘自《日常的中斷:人類學家眼中的災後報告書》第1部「海的子民」:〈這片海是心靈的故鄉〉。
《日常的中斷:人類學家眼中的災後報告書》作者:阿潑出版社:八旗文化出版日期:2018/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