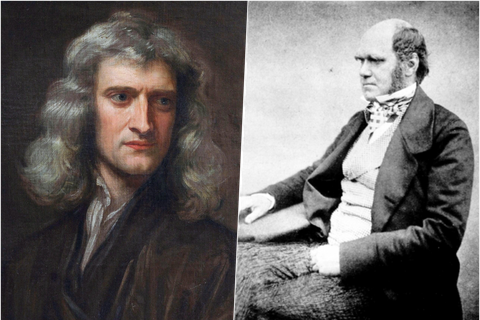疫情過後,世界能恢復以往的生活嗎?我們須為「下一波疫情」做準備

每年,都會發現二到五種新的人畜共通病毒從動物傳染給人類。隨著世界變得更加城市化,森林砍伐進一步使動物遠離它們的自然棲息地,而且肉類在全球供應鏈中成為重要的一環,另一場疫病大流行的可能性只會有增無減。未來幾年,氣候地帶的轉變也將迫使動物離開棲息地,與人類有更多的接觸(進而增加人畜共通傳染病的風險),並且擴大蚊子和其他媒介傳播傳染病的範圍。
同時,無論SARS-CoV-2和隨後發生的COVID-19大流行的真正起源是什麼(我們的觀點是,在撰寫本書時根本沒有足夠的證據來得出結論),未來實驗室事故的風險是真正會存在的,也必須得到解決。隨著所有這些風險的累積,我們可以要求——但我們不能指望——中國和其他國家要完全透明和合作。即使有足夠的政治意願,許多較貧窮的國家也將缺乏及早識別和控制病毒的資源和能力,需要較富裕國家的大量援助。
隨時做好下一波疫情大流行的準備
COVID-19大流行已經造成極大的禍害,但是下一種病毒很可能會更惡毒。世界在破紀錄的短時間內生產了許多可行的冠狀病毒疫苗。但是,即使科學不斷進步,如果下一次疫苗需要花好幾年時間開發——或者完全遙不可及——又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佛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Francis Crick Institute)的盧佩特.貝爾(Rupert Beale)在《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雜誌中寫道:
能夠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研發出好幾種針對這種可怕病毒的高效疫苗是一項相當驚人的成就,這是我們—我指的是整個人類,尤其是分子生物學家——所取得的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我們技能熟練,但我們也很幸運。事實證明,SARS-CoV-2疫苗相對容易開發。但引發下一次大流行的病毒可能不會那麼容易對付。
在COVID-19危機期間,具有SARS、中東呼吸症候群、H1N1和其他傳染病經驗的國家,往往表現得更好。作為一個地球村,現在必須面對的問題是:我們從這場共同的災難中集體學到了什麼?
答案並不簡單或顯而易見。畢竟,世界已經在2020年之前針對如何應付潛在的流行病擬訂計畫。政府投資於全球公共衛生,多年來,針對這一類威脅也發出了數十次警告。在COVID-19之前,美國被評為世界上準備最充分的國家,英國位居第二。中國在SARS之後展開重要改革,似乎與其他國家合作。當真正受到考驗時,這些都沒有出現。我們如何保證在未來十年所做的努力不會導致和今天類似的災難性結果?

首先,世界必須進行痛苦、嚴峻的事後檢討,每個線索都不能放過。我們很容易就揪出罪魁禍首,包括習近平和川普,但還有很多人難辭其咎。譬如,川普並不是唯一一個無視最初警告或自始至終淡化病毒的人。巴西的波索納洛和匈牙利的奧爾班等,其他民粹主義領導人也是如此。
同時,即使病毒在義大利蔓延,歐洲領袖幾乎沒有做任何準備。在疫情爆發之前,西方政府認為大多數傳染病會從開發中世界向外傳播,因此可以遏制在開發中世界。但COVID-19首先在世界上相互聯繫最緊密的先進經濟體中傳播,早在它登陸南半球之前就襲擊了阿爾卑斯山的滑雪勝地。當傳染病首次在中國出現時,世衛和許多國安專家錯誤地忽視了快速實施旅行禁令的重要性,屈從於北京的意志。
在許多低度收入國家根本無法確保個人遵守社交距離、建立足夠的醫療照護能力或為閒散工人提供足夠的安全網時,就鼓勵它們在全國實施大規模封城也是短視的決策。嚴峻的自我批評過程,對於確定必要的改革和為未來的流行病做好準備,至關重要。美國人還必須在事實和科學上達成共識。
防堵疫情的重重障礙:假資訊與保守勢力的破壞
2020年11月,自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就一直警告全球將會爆發疫病大流行的美國資深全球公共衛生專家羅莉.賈瑞特(Laurie Garrett)觀察到,在她的整個職業生涯中,她犯了一個災難性的分析錯誤。在她設計和參與的所有情境規畫演練中,她從來沒有考慮過白宮會成為阻礙和錯假訊息的主要來源的可能性。她明白他們可能準備不足,反應遲緩,就像雷根處於愛滋病流行時期一樣,但沒料到總統會是一個積極的破壞者。
川普的矢口否認和充滿錯假訊息的公開聲明,使數以千萬計的美國人相信,即使感染率和死亡人數飆升至歷史新高,COVID-19不是一種嚴重的疾病。他甚至排擠並壓制了共和黨中理解威脅,並主張做出強有力回應的聲音。由於川普仍然是共和黨中最強大的政治力量,問題是這個國家的半數人民是否會繼續將冠狀病毒描述為「騙局」,將戴口罩等公共衛生預防措施描繪為對個人自由的黨派攻擊,並將政府專家貶斥為「深層政府」的叛徒。
如果是這樣,大量美國人口將抗拒認真思考未來的生物威脅。國會中的共和黨議員或未來的共和黨總統會將它作為優先事項嗎?我們已經提到,川普政府中有一些高級官員很早就意識到了這場危機的重要性。某些共和黨參議員和眾議員也是如此。問題是他們在和川普以及其他自鳴得意的人辯論時輸了。建立以科學、信任和細心準備為中心的全國統一應對措施,對美國政治領袖來說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但這是絕對必要的。

上任之後不到幾天,拜登政府發布了一份200頁的《應對COVID-19大流行的策略及預防的國家戰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COVID-19 Response and Pandemic Preparedness)。這項戰略尋求重建美國民眾的信任。它的目標是擴大檢測規模、加快疫苗發送、鼓勵戴口罩、增加個人防護設備的生產,並確保供應鏈安全。它尋求加強急難救濟,採取安全地重新開放學校和企業的措施、促進安全旅行,也要採取其他措施來遏制疫情,並解決它對經濟的影響,包括對受到不成比例影響的少數民族社區要實施救濟。它還呼籲美國透過留在世衛並推動改革,加入COVAX倡議,並尋求加強其他多邊倡議,包括「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抗擊愛滋病肺結核瘧疾全球基金」,以及「全球疫苗免疫聯盟」的合作,來恢復在抗擊COVID-19方面的全球領導地位。
它提升了對歐巴馬時代的「全球衛生安全綱領」,和其他旨在建設衛生基礎設施和防疫準備的多邊努力的支持,並承諾向遭受病毒嚴重打擊,以及貧困和糧食不安全加劇後果的國家提供人道援助。與此同時,拜登政府迅速採取行動,重新組建白宮國安會「全球健康安全與生物防禦小組」(它在伊波拉疫情爆發後成立,但被川普政府解散)和其他跨部會的基礎設施,以便監測和應對生物威脅。政府也尋求經費來建立一個新的「全國流行病預測和爆發分析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pidemic Forecasting and Outbreak Analytics),使全球早期預警和對新成生物風險的應對能夠更加現代化。
所有這些承諾都是至關重要的糾正措施,而且早就應該做了。但是,美國還應採取其他許多緊急政策,以加強全球防疫準備和對跨國威脅的抵禦能力。
首先,美國必須在國內就流行病構成的威脅、如何應對,以及相應投資的必要性建立兩黨共識。面對疫病,美國最大的弱點是它在基本問題上存在分歧。極端兩極分化、媒體的迴聲室效應,和錯假訊息全都導致對公共衛生問題的高度不信任。客觀上具有破壞性的流行病遭到否定與駁斥;合理的安全措施變成了黨派政治的桎梏。如果美國在這些基本問題,以及疫病大流行構成生存威脅的觀點上仍然存在分歧,就不可能做好充分的準備來應對疫情。如果川普繼續在美國政治上扮演領導角色,並堅持他的政府做對了一切、疫苗足夠了,那麼任務將變得更加困難。

對政府和專業知識的信心不能在一夜之間就恢復過來。但是拜登政府在COVID-19危機的末期做出強有力的國家級應對—包括白宮和其他政府官員的誠實和一致的訊息流通、政府各部門內部及跨部門之間合作,以及在美國和海外有效地處理COVID-19疫苗的分配—可能會開始重建人們對公共衛生措施的信心,若是要更有效地遏制下一次全球傳染病,這是絕對不可缺少的。
其次,拜登政府推動世衛改革時,它應該尋求解決COVID-19危機暴露的核心缺陷。我們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提到,在疫情肆虐期間,世衛對中國太過於恭順。它關於封城和旅行限制的建議,還是有相當不足之處。話雖如此,同樣明顯的是,世衛感到被困在兩個對立的超級大國中間,它仍然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拚命努力。
世衛是唯一一個幾乎把全世界所有國家和地區都含納在內的組織,擁有無限的衛生職責,並被視為具有國際正當性。世衛以前也進行過改革,最近一次是為了應對2014年西非伊波拉疫情。當時暴露出世衛最初的應對措施存在缺陷後,採取了一些手段,包括設立「公共衛生緊急計畫」(Emergency Program)和「緊急應急基金」(Contingency Fund for Emergencies),其目的是提高世衛在面對危機時快速反應和部署的能力。這些改革似乎有所成績,有助於世衛更有效地應對2018至2020年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伊波拉疫情。
拜登政府強調美國在世衛內部開展工作是正確的,以推動更多改革的重要性,而不是像川普那樣試圖撤出資金、解散組織。退出、威脅退出或降低支持能量,並不會導致世衛垮台、創造更可行的替代組織;它只會使得其他國家——包括像中國這樣對透明度不感興趣的國家——更有力量在世衛推動自己的議程。

WHO內部政治角力與公衛合作的權衡
那麼美國應該尋求哪些改革來確保世衛組織更加獨立和有效呢?世衛在未來突發的緊急衛生事件中不受政治干預至關重要,並且根據COVID-19的經驗,它必須要求所有會員國,致力於提高透明度和合作的層級。這需要有更多的措施—包括施加制裁的威脅—以確保世衛官員在「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中,能夠立即和不受牽制地接觸到疾病的來源和樣本。為了進一步減少世衛依賴會員國自願捐款才能執行其職能,世衛還需要有效和持續地增加它的資金。
此外,世衛應更新有關進出受感染國家的旅行建議,因為旅行限制確實在減緩病毒傳播方面達到了正向的作用。台灣應該被接納為觀察員國家。從2009年到2015年,它是出席世界衛生大會的觀察員,但北京在2016年改變了立場,因為它對台灣總統大選的結果不滿意。台灣在遏制COVID-19和更廣泛的全球公共衛生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不應出於政治原因將它排除在世界衛生體系之外。
在推動這一類改革時,我們還必須認識到,地緣政治的局限將使得在近期甚至中期內,全面落實變得十分困難。譬如,對世衛組織在以往突發衛生事件中的表現進行的幾項調查,建議在會員國不遵守規定的情況下應進行制裁—包括2011年的「國際衛生條例審查委員會」(IHR Review Committee)和2015年的「伊波拉臨時評估小組」(Ebola Interim Assessment Panel)提出的建議—但它們從未發生過。世衛前任總幹事陳馮富珍研究了該組織可能懲處不遵守《國際衛生條例》的國家的方式。問題在於,幾乎不可能想像所有政府都同意一個普遍適用的制裁或執行《國際衛生條例》的機制。
即使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ssociation, IAEA)負責監督《核不擴散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規定的義務及報告違反行為,制裁也需要經由聯合國安理會投票表決——這代表需要中國、法國、俄羅斯、英國和美國的支持,缺一不可。習近平非常有可能不會對提高透明度做出有可信度的承諾,而川普在共和黨內留下的「美國優先」議程的陰影,可能會導致人們對美國向世衛的長期承諾的疑慮揮之不去。縱使如此,重要的是公開說明世衛改革的理由,期盼在未來某個時候政治限制會放鬆。

拜登總統還應該定期、堅定地向習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公共衛生合作,重新評量COVID-19之前存在的合作,並在必要時恢復和改革這些合作措施。在可能的情況下,必須在領導階層加強協調,以使改革有任何成功和持久的希望。但我們不應期望這樣的改革是容易的。嚴酷的現實是,世衛很可能在未來許多年後繼續成為美國、其他民主國家以及中國相互之間角力的戰場。
在COVID-19疫病之後,民主國家不太可能取得他們認為必要的所有改革。即使在不太可能的情況下,這些改革似乎是應當的,也可能沒有可預測的實施方式。當下一次危機來襲時,無法保證大國會遵守它們的義務。因此,如果美國認為有必要,即使它仍然充分參與世衛組織,美國可以、而且應該創建和參與平行的全球公共衛生的組織。
這就帶出了我們的第三項建議:有必要建立新的國際工作籌畫,和志同道合的國家聯盟,以增強填補世衛的工作。美國可以領導這一工作。小布希政府通過2003年啟動的「總統辦公室愛滋病緊急救援計畫」,加強了全球抗擊愛滋病毒/愛滋病的鬥爭。為應對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和2014年伊波拉疫情,歐巴馬政府尋求改善國際合作,和通過「全球衛生安全綱領」進行新生物防範。川普政府對COVID-19的民族主義態度嚴重破壞了這一傳統—但拜登政府有機會重振它。
有些國家提出了一項新的國際流行病條約。這一想法受到美國、中國和世衛的歡迎。它值得一試,但談判將是漫長而艱難的,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地緣政治競爭重新抬頭的壓力。將國際社會的所有精力都用於開發一項新協定,可能會將外交資源從改善全球防疫準備所需的即時方法中轉移出去。嚴峻的現實是:在未來幾年,由於有些國家能力不足,以及有些國家在疫情爆發時拒絕合作,現有的國際公共衛生安排可能會被證明是不夠的。
※ 本文摘自《疫後震盪效應:防疫政治學與世界秩序的崩潰》第13章,標題為鳴人堂編輯所加,燎原出版授權刊登。

《疫後震盪效應:防疫政治學與世界秩序的崩潰》作者:科林.凱爾、湯姆斯.萊特(Colin Kahl, Thomas Wright)譯者:林添貴出版社:燎原出版出版日期:2022/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