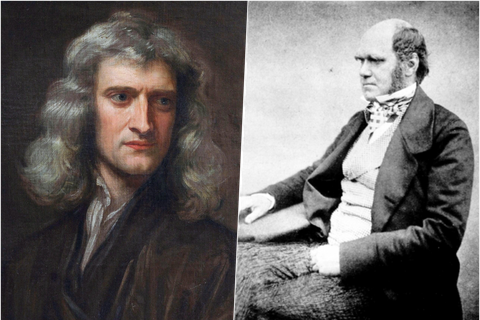阿潑/回到2020年1月23日那天:我們步入未知恐懼的疫情時期

害怕成為「被生病」的人們
這個世界可粗略分成兩種人:生病的人、沒有生病的人;或者,應該再增加兩種分類:不知道自己生病的人,以及「被生病的人」。
如果「生病」是一種罪刑,我早已在牢獄,沒有什麼自由可言。長年進出醫院的我,在遠行前夕,經朋友提醒口罩之必須,於是道別之後,轉身走向車站裡的藥妝店,蹲在架前,揀選口罩。
說「揀選」也太過。架上口罩之稀,如同這即將打烊的藥妝店內人客一樣,一眼即知數量,我僅能在兩種共四包口罩中選買。正因為存貨太少,即便只買一包,都會感覺自己如在饑荒中搶糧一樣,心有罪咎。只隱隱感覺似乎有要事發生,卻又不明所以。
這包口罩和我準備帶出國的旅行清潔用品一起上了計程車,並在我鼻喉略略痠癢時,被我打開戴上。不知是否因為如此,駕駛座上有了聲音:「我之前載了一對情侶,女孩子就坐在我後方,從上車就開始咳嗽,咳得很兇。」他摸了摸後頸,說現在都還能感覺到飛沫的存在。
「我們做服務業的,不能夠戴口罩,因為客人會以為你有問題,是不是生病,是不是不想給人看臉,客人會不舒服,不想搭,或是投訴。」 司機壓低嗓音,彷彿傾吐祕密:「可是,我也很害怕啊,我擔心客人傳染給我,而且,如果車子沾上病菌,也會傳染給別人。」
他說:「我要在這個密閉的車內跑一整天的車。我生病怎麼辦?我的家還需要我養……」他害怕生病,但也擔心他人(乘客)的眼光。
我無法確知他的滔滔不絕究竟因何而起,但他顯然對於染病很是焦慮。一路上,我任由他的煩惱如天竺鼠在滾輪上跑動那般,無止境迴圈,無法答話。後來我才知,這夜是「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報請成立滿兩天,儘管偶有訊息如落葉花瓣在社群網站漂浮,但不至於在我的世界產生漣漪,因此,一直到隔日醒來,我都把這司機的擔憂,看成是對無禮乘客的抱怨。

戴上口罩的記憶:從SARS到COVID-19
下了計程車的十小時後,武漢封城的消息,震動了全世界,我前一晚的疑惑霧盲,此刻變得清晰可明。2020年1月23日下午,一邊關注新聞,一邊拉著行李箱往機場路上前進的我,立刻發現在這座城市生活的人們,瞬間失去了自己的半張臉──從捷運到車站,從車站到機場,交通運輸從業人員、車上的乘客、路上的行人,已自行戴上口罩。這個畫面,我有記憶,那是17年前你我的曾經。
那一年,同樣疫病來襲,島國輿情鼓譟,恐懼滲進人心。人在花蓮上學的我,因群山之隔,路途之遙,課業之重,遠離新聞核心,不知風暴到底有多大,但因在醫學院讀書,每日必得出入消毒過的大樓,用校方發送的簡易體溫計,天天度量體溫回報。我的生活被課表切分為上課下課,進教室出醫院,身體也被數值化:36度、不到37度。有段時間我被譏笑為「冷血動物」,因為體溫總是很低,不知為何這竟讓我有些得意:至少我很安全。
然而,這個社會並不那麼安全,也無法以簡單的數值來分界,即便沒有發燒,但只要與染疫員工有關,就被排擠,即便表面安好,也因是職業醫護,就有疑慮。從媒體可知,這塊土地陷入了被體溫數據衡量、依職業、健康排序階級的情狀,恍若失去理性。
像是這樣的標題:〈隔離者受歧視:我們不是瘟神〉〈你和恐怖肺炎患者同機!〉〈中鼎員工哭訴 小孩無校可念 SARS恐慌情緒剝奪小孩就學權〉
人們害怕「那些生病的人」,也擔心那些「不知道自己生病的人」;他們不願自己成為生病的人,也拒絕那些可能會生病的人。凡人都是可懼的,但有些人更可懼。

如果染疫成了十惡不赦的罪刑
恐懼綁架了所有人,包含遠在山那一頭的我自己。我在某個回家的週末狠狠地將疫情新聞看過一遍,當時和平醫院被感染的新聞仍未出現,卻有幾起疫情發生,染疫員工的無奈,以及光是隔離者受到歧視的憤怒在媒體奔騰,即已鼓譟人心,我這時才感受到現實世界像被稜鏡映照那般變形。盡是污名。
返回東部途中,站在空曠月台上、沒戴口罩的我,無法控制地,將周遭乘客的盯視,想成是譴責;一上車,尚未坐穩,聽到後方傳來的猛烈咳嗽聲,只覺整個車廂都震動了,人人將背豎直,神色緊張,甚至有人還站了起來,像是要立刻跳車那樣的慌張。這樣的氣氛催得我翻出口罩戴上,從彰化到花蓮七個小時都無法放鬆,只覺自己不太舒服,全身發熱,一路想著:「可千萬不要感冒,這太冤了。」
平時很少感冒、也不把感冒當一回事的我,這時卻非常害怕自己生病。如何不怕?
同樣是發燒咳嗽,以前無人理你,現在被當瘟神對待,可能被隔離,搞不好還要被責怪:「幹嘛搭火車,幹嘛來看病?幹嘛趴趴走?」
當時我並不知道後來引發和平醫院院內感染的「曹女士」是在火車上被傳染的,就已經在腦中演了一齣驚悚劇,劇情是被「隔離」的我,被全世界「隔離」,我的親友受到社會歧視,又或者像前幾天新聞裡那個倒楣鬼一樣,只是感冒發燒就被公司炒魷魚,甚至像媒體報導的那位感染者一樣,聲聲向大眾認錯:「我對不起社會,生了這種病。」

「得病是否為一種失德的因果關係?」
「得病是否為一種失德的因果關係?」 蘇珊.桑塔格曾這樣反問,彼時的我禁不住憤世嫉俗也想質疑:誰想要生病?又是誰要為這種病負責?為什麼生病的人該將一切暴露在大眾眼前,為什麼他們該說「對不起」?
對疫病的恐懼綁架了整個社會,比起病毒,染疫者更像是人類的敵人,只要隔離、排拒、犧牲他們,就能保全自己。我們還是健康無病的群體。我想像自己是個口罩怪獸,沒有嘴巴,無法控訴,無能抵抗這一切。2020年1月23日這一天,口罩怪獸再次占據了城市,歷史再現。
是日,恐懼襲來,讓我在每個轉換的交通工具上都不敢大口呼吸,怕是不慎嗆到,咳嗽,會引人注意。一週後,返國時,疫情已升級,隔絕、歧視的話語較之過去依然存在,甚至透過社群媒體更是擴散,慶幸整個社會已懂得節制,且因信任疫情指揮中心的指令,很快就冷靜下來——戴口罩、勤洗手,保持1.5公尺的距離,成為日常生活法則。
歷史雖重來,但那年的教訓,讓我們明白,這不再只是某個醫院的悲劇,不是只有台商有危機,而是整個國家、整座島乃至整個世界的命運,國界被封閉,日子被強制更換成另一種規律。島國人民習慣下午兩點「聽判」,判決是數字,數字之外還有案例編號,每個編號是某個年紀的男性或女性,他是誰,因何染疫。人們從這微薄的資訊猜測他的故事與心情,甚至,知道他的足跡─再度量自己的生活痕跡。
每個人還是只露半張臉,健保卡決定我們在醫療院所的進出,額溫槍宣判我們自由刑度。
卡繆的《瘟疫》再次成了這個時代的經典,甚至註腳:
……說黑死病已經吞沒了一切事物和一切人,倒比較接近事實。這時已經不再有所謂個人的命運,只有集體的命運,也就是大家所共同遭遇的黑死病和共同產生的情感。這些情感之中,最為強烈的便是放逐感與被剝奪感,跟這些感覺交雜的,便是那種叛逆和恐懼的感覺。
我依然頻繁上醫院,每家醫院都在管制,每次都有不同的進出規定,或是刷健保卡,或是確定旅遊史,甚至必須填單說明各種狀況。一次,老實地在單子上填寫流鼻水乾咳——擤掉我一小包面紙——眼見工作人員緊張問原因,還往後靠了一下。
我有些抱歉:「應該是過敏吧?」
「如果你是感冒的話,不要來這裡,去急診。」
工作人員的反應相當合理,於我卻有些衝擊,也有點受傷。但確實,過往常犯的過敏,有時發生的感冒,此時此刻總讓我擔心——會不會其實沒有這麼簡單?與其說擔心自己染疫,其實更是害怕成為「兇手」,破壞別人的健康與生活。以及隨之而來的質疑與汙名。並想起武漢封城前一晚計程車司機的喃喃自語:「我不能生病。我不能害別人生病。」
於是,讓人又想到蘇珊.桑塔格,想隨之扣問:得病是否為一種失德的因果關係?
※ 本文摘自《孤絕之島:後疫情時代的我們》,原標題為〈那一天,那一年〉,木馬文化授權刊登。

- 文:阿潑,受過新聞與人類學訓練,擔任過記者、NGO工作者與研究員。曾獲開卷好書獎、國際書展大獎、台灣文學金典獎等。著有《憂鬱的邊界》、《介入的旁觀者》、《日常的中斷》等。Facebook:「島嶼無風帶」。
《孤絕之島:後疫情時代的我們》編者:黃宗潔出版社:木馬文化出版日期:2021/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