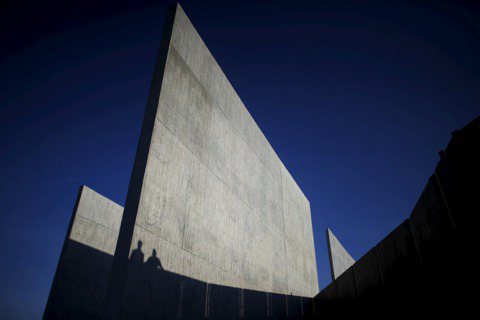顏值、態度,還是社會經驗?——淺談審判者的偏見

屏東地院剛剛結束的國民法官模擬審判,審的是一樁強盜案。在現實事件裡,這個案件是以8年有期徒刑確定,而模擬國民法官審判的結果,最終做出了無罪判決。經過這麼多次的模擬審判,參審員或陪審員通常判得比法官輕,也更容易判無罪,這樣的結果應該已經沒什麼好訝異的了;尤其,在現實世界裡,這個案子也曾經一度獲判無罪。令人訝異的,是無罪判決背後的理由。
據報導,參與該模擬審判的一名國民法官坦言,自己有婦人之仁,當被告頻頻高喊無罪的同時,感受到對方的態度誠懇,加上稍有顏值,所以整個人都被影響,最後投下無罪票。這說法嚇倒了不少人,也在法官之間傳為笑柄。
然而,就在法官們掩嘴竊笑之際,也有人不甘示弱地反駁:
法官難道不會受到當事人的態度跟顏值影響?素人法官願意承認這一點,職業法官敢承認嗎?
法官的偏見
一切在法庭上所發生的事情,都可能會影響法官的裁判,包括當事人的「態度」。事實上,法官必須把呈現在法庭上的一切事項都看在眼裡,就連律師也會事先與當事人「溝通」,法庭上該怎麼應對進退。儘管如此,對法律實務工作者來說,事情從來就不是「態度好+顏值高=無罪」這麼簡單。
態度好的當事人容易獲得有利的裁判,不完全是因為法官偏心,更常見的原因是,合作的態度,本來就比較能夠協助法院查明真相。
套用一本法普著作的說法:「否認犯罪也必須『誠懇以對』」(參見姜長志,《說真的,你很好騙:27個詐欺暗黑真相大揭露》,第370頁)。法官能分配給每個案子的時間都是有限的,如果當事人把這些時間拿來講幹話、戰態度,卻沒有針對事實或證據表示意見,要贏這場官司,就只能寄望於對造犯錯了。
然而,態度的影響卻沒有止步於此。法官必須提醒自己,裁判必須以法律與證據為基礎,而態度跟顏值不是法律也不是證據,但再怎麼提醒,都難以完全排除偏見的影響。正如《不平等的審判》一書所指出的:
故意作成的偏見其實並不是法官主要的問題……所有法官都會受到許多不被認可的偏見左右,這會影響到他們對於看似中立之法律及事實的認知,和他們最後的判決。(第194頁)
性別、種族、階級和其他許多因素也都有類似的軌跡。法官們都很清楚不應該讓這些因素影響判決的作成;其實,他們還常指示陪審員在評價證人、被告和辯護人時,不可以受到這些差異的影響。不過,法官也只是這個社會的一分子,在這個社會中,這些因素就是會帶來許多聯想……(第199頁)
這本書主要的研究對象是美國的司法,但同樣的說法,在臺灣也是成立的;正如美國的法官是美國社會的一分子,臺灣的法官也是臺灣社會的一分子。
比方說,學者指出,在離婚的父母爭取子女監護權的案件裡,臺灣的家事法官幾乎一面倒地偏向於把孩子判給母親,這是因為,法官往往先入為主地認為「女性比較會照顧小孩」,這樣的想法,往往還跟所謂的「幼兒從母原則」或「襁褓原則」結合。
這樣的見解,固然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不過,個案之間都有差異。「幼兒從母」儘管是判斷過程中的一種指引,但爸爸比較會照顧小孩的案例,也是存在的。筆者身為家事法官,最感困窘的是,知道這些問題,不一定能幫助我做出更好的判斷,因為我們常常找不到適當的證據方法,來呈現父母子女平日的相處互動。
另一個例子,是關於「案重初供」的迷思。初供,就是被告剛被抓到的時候講出來的供詞,「案重初供」的意思,就是這種供詞最為可信,因為被告往往在此時最沒有防備、最不會說謊。我們的最高法院很久之前就指出,法官不能用這個標準,機械性地判斷供述是否可信。從此以後,幾乎沒有刑事判決敢寫出這四個字;只是,法官心裡到底是怎麼想的,就是另一回事了。
同樣地,「案重初供」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這種說法要能夠成立,有賴一定的前提要件配合。被告在毫無防備的時候講出來的話,或許最不經修飾、最不會加油添醋,但同樣地,在那種毫無防備的情況下,他卻也最容易受到誘導、誤導,而即使訊問者沒有刻意誘導或誤導,還搞不清楚狀況的被告講出來的話,也可能是最不精確、最不完整的。更重要的是,即使法官深覺初供可信,在被告的自白之外,有沒有合乎刑事訴訟法的補強證據,仍是問題所在。
人民的偏見
非常政治不正確的是,《不平等的審判》一書也指出,人民對法官也常有偏見:
我們很容易覺得法官有偏見——就算他們並沒有。因為相信自己的觀點絕對正確,所以如果我們很反對某位法官的立場,我們會懷疑他不值得相信。如果我們認為某一位法官屬於行動者,而另一位則是裁判員,兩者的不同可能並不是因為他們真的有什麼偏見,而是在於他們是否與我們的觀點一致。(第194頁)
同樣地,這個說法在臺灣也是成立的。比方說,認為法院總是用似是而非的理由輕判、縱放被告,認為法院太過保護被告人權的想法,在我國人民之間似乎十分流行。然而,有位外界譽為司法最後良心、唯一良心的前輩法官,卻成天批評自己的同事缺乏人權意識、缺乏憲法意識,甚至痛斥最高法院是「沒有靈魂」的法院。他的批評不但經常得到人權團體的共鳴,在法官、檢察官之間也能取得一定的迴響。
確實,筆者準備律師、司法官考試時也發現,刑事法的爭議問題,學者之間眾說紛紜時,最高法院十之八九會選擇對被告最不利、保障最低的那一說,通常也是法學者們最反對、批判得最兇的那一說——保守的人罵你太前衛,進步的人罵你太反動——夾在中間的法官,大概也只能深感手足無措,不知道哪一邊才是真正的社會期待。
再比方說,有一種常見的批評認為,法官、檢察官多半出身上流社會,無法同理社會底層民眾的苦處。從筆者的個人經驗來看,這種批評只說對了一半,甚至只說對了四分之一。
法官、檢察官多半出身於什麼樣的社會背景,目前沒有完整的實證研究,因此,「法官、檢察官多半出身上流社會」的說法,只能是一流的嘲諷,三流的臆測。
依據筆者私下觀察自己同事的經驗,確實有些法官出身優渥,並因此對社會底層缺乏同理心,但也有些出身優渥的法官,知道自己跟當事人來自不一樣的社會背景,反而更願意試著理解當事人的處境。
同樣地,有些法官出身低微,因此能夠輕易理解社會底層的境況,但也有些出身低微的法官,對來自社會底層的當事人特別缺乏同理心,他們的出身反而造成一種心態:「我出身低微,但我憑著自己的努力出人頭地,你怎麼可以說,你出身低微,所以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
經驗經驗,多少罪惡假汝之名?
我相信,不少讀者已經摩拳擦掌地準備反駁我。理性勿戰。這是我的個人經驗,如果你相信,很好,我們已經達成某種同情的理解;如果你不信,也很好,這終究不是你的經驗。
人是萬物的尺度,每個人的經驗,對他自己來說,都是最真切、最實在的,但每個人的經驗都是有限的,更受到時空背景的限制。誰要是不願意承認「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偏見」,那麼,更多的社會經驗,就無法洗刷他的偏見,也不見得會淬鍊出什麼人生智慧,反而提供了更多的素材,讓他能將自己的偏見包裝成「洞見」。
對於裁判者而言,社會經驗不會只有助力,還是偏見的來源,而助力與偏見其實是一體兩面,因為人是萬物的尺度——無論這個人是法官、檢察官,還是參審員或陪審員。回到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模擬國民法官,他對於被告顏值與態度的偏重,難道不也展現了他的社會經驗?
到頭來,缺乏社會經驗並不可怕,不知道自己的經驗有其侷限,甚至自以為很有社會經驗,才是最可怕的。把社會經驗當成司法改革的通行證,將司法裁判的「不合乎社會期待」,歸咎於法官欠缺社會經驗,或者將人民參與審判的理論基礎,建立在「參審員或陪審員比較有社會經驗」之上,或許,都是太過想當然耳的「偏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