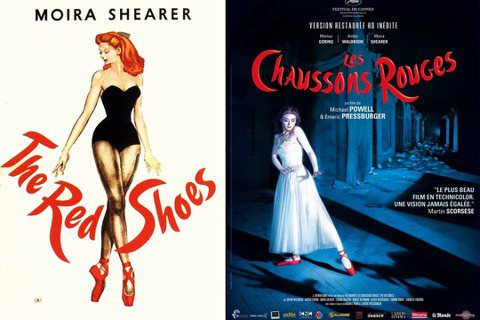李行與瓊瑤電影(十二):畸戀言情之外,健康寫實的《婉君表妹》

《婉君表妹》雖然改編自中篇小說,電影劇本的骨架和戲肉並沒有因此落入無戲可演、只能依靠大篇幅獨白或心聲推展劇情的窘境。原著〈追尋〉雖只是「中篇」,角色、情節的飽和度其實不亞於長篇小說,應是當時瓊瑤為求自立、為謀生計而辛勤筆耕的產物(中短篇的「生產」時間較短,因此可能會有較大的「產量」)。
改編劇本幾處特色
細品電影《婉君表妹》,以周旭江掛名主筆的劇本讓人擊節處至少有三。
首先,是將小說裡的過場文字敘述立體化,使之成為具體的場景。比如西席先生讚美周家老大、老二和婉君一折,原著裡是輕輕一筆帶過的描寫,在電影中,則是完整的一場戲,將幼年仲康、叔豪、婉君三人與老師之間的互動,具體呈現在觀眾面前。
其次,電影劇本在塑造角色時,下了極大的工夫,人物的台詞,平實而生活化,簡單、俐落,而且直指每個角色的性格核心。一場三兄弟爭搶婉君,因而爆發全面衝突的高潮好戲,電影是這樣演的:周老爺氣急敗壞地數落:「你們書都讀到什麼地方去了?連弟兄相讓的古訓都忘了嗎?不知廉恥!」廳堂上,周夫人焦急又無奈,只見三兄弟一字排開,被父親斥罵後,各有各的委屈。
伯健:我是爹媽作主把婉君說給我的。
叔豪:我——我們是跟婉君一起長大的。
仲康:我愛婉君!婉君也愛我!
一人一句台詞,道盡角色內心世界與成長歷程。這樣精煉而耀眼的人物塑造,給觀眾帶來極強烈的感情衝擊,同時映照了婉君被苦苦逼問「究竟愛誰」之際,所回應的那一連串「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真的,她不知道「應該」愛誰。選了其中任何一個,都註定會是整個家庭的悲劇。不選其中的任何一個,說不定這個悲劇還有解脫的可能。


非同小可的製片格局
走筆至此,我們暫時跳開這難解的四角習題,看看當年港台華語影壇的情勢與景況。對當年其他的獨立製片業者而言,幾乎不可能有那麼多時間、精力、經費和社會責任心,能像龔弘所主導的中影公司一樣,仔細琢磨瓊瑤筆下的故事與人情,使之穩重,使之雍容,使之雋永、使之悠遠而耐人尋味。
透過《婉君表妹》,我們看到的是一群形象鮮明的人物,在創作團隊精心打造的白粉牆、黑窗格的生活空間裡,穿梭其間,盈盈散發著繡色畫意。華語片觀眾在此之前從來沒有機會見到這樣的東方詩情世界,無論是邵氏、國泰的出品,抑或年代更早的新華、永華電影。而這樣的光影世界,卻如此理所當然地在「後梁祝」年代的台灣影壇,應運而生,一似水到而渠成。
《婉君表妹》第三個「獨門特色」(其實筆者更願意贊之為「優點」),是它淡化了多角畸戀的情愛糾葛,把經營纏綿情思的精神,挪去加強三個男主角的個性與所呈現出的姿態。至此,《婉君表妹》引人入勝的已經不是「婉君要嫁誰」的懸念,而是伯健、仲康、叔豪三人與婉君之間的關係,會發生什麼變化。
從表哥表妹成長的私戀,擴大成為青年男女成長的抒寫,再接上中影希望故事結尾必須要有的「健康的尾巴」,整部《婉君表妹》,結結實實開闊了〈追尋〉原著的格局。在保有原作閨閣情致的前提之下、在忠於原作雅秀之創作精神的前提之下,《婉君》的最後高潮,竟是三個男孩子離家啟程去面對不同的人生責任。

年輕世代的成長縮影
三種取樣,切片出中華文化在巨變之中,一整個年輕世代的成長縮影。飽涵舊文化底蘊的伯健離家到上海讀大學;仲康在婉君自盡獲救後,得知兄長不願苦守父母之命,自願放下婉君,於是他瀟灑離家,將兒女私情昇華成對國家社會的投入,遠赴廣州投考軍校。
年紀最輕、比婉君還晚三天出生,得要叫她一聲「婉表姐」的叔豪,在故事的最後擔起「繼承人」的身份,肩負全家幸福的維繫關鍵。一向以稚氣形象貫穿全片的叔豪,選擇以「出走」來成全整個家庭,在年輕的一代突破舊社會、舊秩序的種種藩籬之後,所可能得到的團團。
正是這一份成全的心,把《婉君表妹》在添入「符合國策」的離家求學、從軍報國情節之際,推上更雋永,也更體貼的層次。簡單一個「愛」字,至此跳脫白紙黑字,躍然銀幕,迭宕多姿,綻放出更豐富、更艷麗的色澤。
回扣到劇終之前鴻雁來賓,家書到府,婉君在姑父、姑母的殷寄之下,展信而讀。信是仲康寫給婉君的:
婉君表妹:
南來逾年,雖思念之情無時或已,但當此大時代,青年報國未遑,不容有私人之感情存乎胸際。余已考入軍校,參加革命陣營,吾國民革命大軍,不日即將揮師北伐。明年鶯飛草長之日,當為我等重聚揚子江畔之時,請多珍重。
起首一句「婉君表妹」,結尾一句「請多珍重」,總共八個字,收住了〈追尋〉,也收住了《婉君表妹》。畸戀之外、言情之外、國策之外、口號之外,就衝著這八個字,電影《婉君表妹》真的值得我們為她灑下的幾滴至情之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