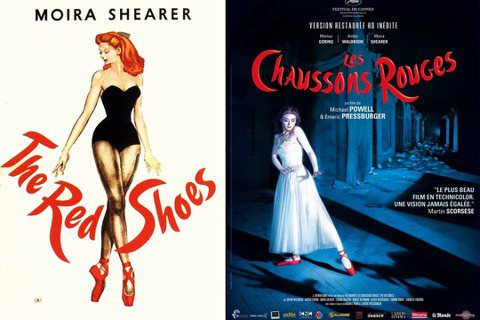李行與瓊瑤電影(八):春來春自去,花開花自落——談《浪花》

《浪花》的三生三旦加上一位母親,每個角色的性格都極其立體清楚,拍成電影,如果選角選得對,必定事半功倍。然而,當年在瓊瑤和李行之間的不愉快,竟然是因選角而起的。
在瓊瑤簽下小說授權時,便有附帶條文,說是原作者對主要演員有同意權(多年後白先勇的《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也有這一條)。1970年代,瓊瑤電影進入第二波高潮,李行、白景瑞,以及張美君導演連番交出優秀成績,瓊瑤夢幻世界裡的人物,男的若非秦祥林、鄧光榮,就是谷名倫;女的若非甄珍,大概就是林青霞或恬妞。一直到《碧雲天》,李行導演在沒有得到瓊瑤同意前,就先宣布了林鳳嬌、秦漢、張艾嘉的組合。
根據資深文友提供的訊息,當年,瓊瑤曾在香港《銀色世界》雜誌上寫到,她原本對張艾嘉飾演俞碧菡有些遲疑,認為張艾嘉在電視螢光幕上穿著牛仔褲唱西洋歌曲的模樣,扮演現代感較強的蕭依雲或許更為合適。但因沒有和李行導演直接溝通的機會,直到看到電影成品,她才認可了張艾嘉的演技。
這次的《浪花》又一樣,因為事前缺乏溝通,為了全片靈魂人物——藝術家秦雨秋的選角——兩造之間心結更深,雖然事後已經敞開心胸好好談過,然而就我們外人的眼光看來,可能裂痕已生,在不久之後也就分道揚鑣,一段美好的合作就此畫下句點。雖然遺憾,但也只有祝福。
瓊瑤心目中的秦雨秋,飄逸出塵且兼具「古典」和「現代」的特色,外表可能符合大家對於傳統女性的柔美印象,骨子裡卻又有強烈的叛逆因子。她在文章中點名,或許「唐寶雲」是合適的人選。至於李行導演挑中的李湘,當初出道時,除了參演李行在中影拍攝的《路》,亦曾演過瓊瑤小說改編的《月滿西樓》和《尋夢園》,後來在《庭院深深》電影版裡,表現更是可圈可點。
瓊瑤在文章中指出(當時《浪花》才剛準備開拍),她第一時間的反應,認為李湘「現代味夠了,古典味不足」,但跟李行導演提了「唐寶雲」,又惹出更多「溝通不良」的問題。


《浪花》的選角
這些矛盾和不悅,轉眼也都是40多年前的事了。
當年的風風雨雨,並沒有削弱《浪花》的威力。影片中的李湘倒沒有一定呈現出什麼古典與現代、傳統與叛逆,她用飽滿圓厚的成熟姿態,將秦雨秋完整活在電影銀幕之上。與她搭檔的柯俊雄,也把俗中有雅的中年畫商,刻劃得入木三分。
若真要說在選角上有什麼缺點或遺憾,恐怕林鳳嬌是最大的問題。阿嬌演的戴曉妍一角,據故事裡的描寫,是保守家庭裡的叛逆少女。年紀輕輕跟野朋友玩band,亂搞男女關係,16歲的時候大了肚子,被鎖在家裡,打罵規勸,終致精神崩潰,孩子流掉之後離家跟姨母秦雨秋長住。她的狀況與創傷後壓力症相仿,一不小心病情發作,就會完全失控。
林鳳嬌演起這個角色,不但放得太過太猛,整個創作團隊對戴曉妍的了解、描寫和體貼也都不夠,以致呈現起來非常扁平。一開始表現她嬌俏活潑,讓她吊兒啷噹地逛畫廊,跟秦漢飾演的大學生鬥嘴;後面要表現她發病時的激烈感,運用了極過火的場面調度和鏡頭語言,替林鳳嬌配音的配音員除了尖聲怪叫、扯嗓大哭之外,就剩下其餘場面裡不住發出的「嗯哼」「哎嘿」。嬌喘微微卻言不及義,實在令人掩面難以卒睹,是為全片最大敗筆。
相對於李湘、柯俊雄的浪漫與穩重,黃曼飾演柯俊雄的太太,在傳統黃臉婆和罵街潑婦之外,她還很有分寸地給了我們不少反省的空間,讓我們非但無法討厭這個母親,更甚而會願意去同情這個中年婦人。秦漢一掃《碧雲天》挑不起大樑的窘境,把《浪花》故事裡的活潑大學生,演出白馬王子的漂亮姿態,表現可圈可點。
張艾嘉的柔與勾峰的剛,也為整幅人性塵網多添了軔性和體諒。勾峰的角色基本上就是當年《船》裡頭的紀遠;張艾嘉的角色則為即將來臨的第三波瓊瑤電影與瓊瑤小說創作高峰,也就是瓊瑤自組「巨星影業」時代的諸多女主角,做了一次美好的暖身。她的青春活力、溫暖體貼,在不久的將來,便會透過林青霞的演繹,成為「瓊女郎」最深入人心的藝術形象。


春來春自去,花開花自落
李湘自出道之初,基本上就定了嫵媚、成熟的戲路。可惜瓊瑤自組的火鳥公司創業作《月滿西樓》至今不傳,大家無緣重溫她正值青春的亮麗表演,只能從《尋夢園》的片段(她飾演武家麒原本的戀人海珊)裡去欣賞、放大、想像。
她曾在1971年的亞洲影展,以《母與女》獲頒最佳女配角獎,也留下包括《母親三十歲》、《庭院深深》等精采的傳世之作。在白景瑞導演的《家在台北》裡,大堆頭的明星擠滿三段故事,讓人印象最深的女角色除了歸亞蕾的哀婉棄婦,就是李湘詮釋的那位過盡千帆皆不是,天涯漂泊意興闌珊的「冷露」一角。
這次在《浪花》裡,因為瓊瑤一度對選角的反彈,致使「秦雨秋」這個角色在拍攝期間,包括導演李行還有李湘本人,無不戰戰兢兢,非得要拿出最優秀的成績不可。李湘也把秦雨秋的艷麗、瀟灑、浪漫,以及內斂、穩重,拿捏得恰如其份。一場自畫像的戲,張力不亞於當年《彩雲飛》裡〈千言萬語〉歌聲底下,鄧光榮深情款款地為甄珍塑像的經典段落。

電影演到秦雨秋在她的畫室,窗外是寒風、枯枝,窗內是雨秋執筆在畫架前。紙上已經開好一張臉,那是她的自畫像,細節尚未落定,她穿著深色寬袍,翩然走到牆邊攬鏡自照。鏡子裡映出那幅才畫了一半,尚待畫家續筆的作品,背景襯著動人的歌曲〈雲一朵〉,跟後來瓊瑤寫的〈我是一片雲〉有那麼一絲異曲同工的微妙:
你是一朵雲,我是雲一朵/偶然間相遇,轉眼又飄過
鏡頭從歌聲中拉開,飾演畫商賀俊之的柯俊雄見到已完成的畫作,心醉神馳,回身探望,只見李湘坐在鋼琴前拂鍵而歌:
愛是一朵雲,心是雲一朵/春來春自去,花開花自落
這一場你證我證,兩人心意相通的戲,李行導演的團隊再次使用一首歌曲,包覆所有的元素——人物、道具、心意轉折、劇情推力——唯一讓人覺得遺憾的是,這首〈雲一朵〉和結尾高潮的那首〈浪花吹醒情人夢〉,在電影裡由陳蘭麗為李湘幕後代唱(崔苔菁灌錄唱片版本),陳蘭麗唱得極賣力,歌藝又好,聲音辨識度極高,卻不知怎地放得太多太滿,滿到李湘已沒有其他的表演空間。對嘴演起來,既不像她本人唱的,又欠缺餘韻無窮的效果,就只是兩首好好聽的歌,真是可惜!
不過話說回來,《浪花》以及之後的《風鈴風鈴》這幾部李行導演的末代瓊瑤電影,在歌曲的運用上實在比稍早的《碧雲天》要高明甚多。雖然不復《彩雲飛》等作品一鳴驚人的氣勢,李行和作曲家翁清溪之間的合作也終於日漸穩固。《浪花》的〈雲一朵〉和〈浪花吹醒情人夢〉,儘管讓真正的戲劇效果打了折扣,卻無損它們本身是優秀好歌的事實;《風鈴風鈴》更留下傳世經典的〈幸福〉和〈愛神〉,此為後話。

龍思良設計,張大千題字
自1960年代中後期開始,台灣電影圈和美術界的關係愈來愈親密。李翰祥的古裝片就不用說了,《喜怒哀樂》的〈樂〉、《八十七神仙壁》(未完成,爾後改拍為《祇羨鴛鴦不羨仙》)等,都有藝壇人士助陣。
白景瑞的《第六個夢》由席德進幕後代畫,不但替片中柯俊雄飾演的畫家畫了一整場畫展(數十幅作品均由席德進提供),為電影量身訂製了兩幅肖像畫,其中一幅還在鏡頭前被女主角唐寶雲醋意攻心,執筆在畫中美人的臉上打了一個大叉。
龍思良跟李行導演的合作也算早,《彩雲飛》裡鄧光榮那一幅幅的涵妮和小眉畫像,都是龍思良的大作。不過龍李之間最密切的合作,應該是李行導演一系列的電影海報。
《風從那裡來》、《吾土吾民》、《碧雲天》、《浪花》、《小城故事》、《汪洋中的一條船》、《白花飄雪花飄》都由龍思良設計,他運用版畫或者油畫,或者照片拼貼,做為畫面的視覺中心,再配上名家題字,在當時台灣電影界可算是別開生面的創意展現。
說起「名家題字」,李行導演這系列電影作品的片名題字人,也是赫赫有名的超級大師。《浪花》、《原鄉人》都是張大千,《風鈴風鈴》則是葉公超。

《浪花》當時揮軍香港,聲勢很大,香港在1976、1977年幾乎已經沒有台灣「三廳」文藝片的生存空間,或許節奏太慢,也或許片中的都會時尚質感,接不了香港地氣。以瓊瑤電影來說,巨星公司出品的《我是一片雲》尚有機會在香港海運戲院上映,之後的多部作品海外發行最遠似乎只到星馬及東南亞,具有「插旗」意義的香港反而不見蹤影。
李行及白景瑞的幾部瓊瑤電影也一樣,《彩雲飛》、《海鷗飛處》、《心有千千結》、《一簾幽夢》,反應都不錯。然而轉眼到了林青霞、林鳳嬌從甄珍手中正式接過「瓊女郎」的棒子,整個時代氛圍也變得不一樣了。林青霞主演、張美君導演的《在水一方》在港賣座似乎不好;白景瑞導演的《秋歌》則根本連上映的機會都沒有。林青霞後來總算以別種樣貌成功打入香港市場,也以轉型中的香港電影做為自己轉型的跳板。
當年香港嘉禾戲院揭幕,不選流行港產片,反而挑中李行導演的《浪花》做為開幕獻禮。大卡司的三生三旦,又是來自台灣的李行的文藝片,宣傳起來自有一番不凡的氣質。可惜賣座平平,連帶使得嘉禾院線手中握有的《秋歌》也沒有排期。很明顯的,在《浪花》的光影浪花終於拍打上岸時,整個時代、整個環境,已經準備邁入另外一個紀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