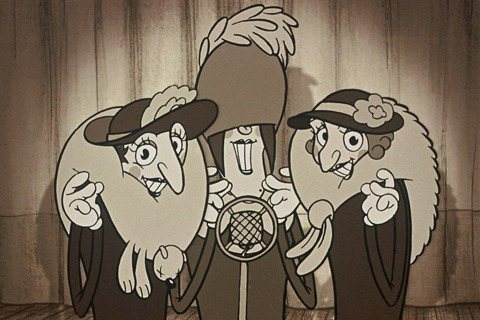他們的1990——《七月與安生》和《八月》

今年因為種種原因無暇追蹤金馬獎,幸好今年有辦得獎片巡迴放映,讓我得以一口氣全部補齊。
所有得獎片中,我自己最喜歡最佳影片和新演員獎得主《八月》,它像是契可夫的田園詩,淡得別有意境,不禁佩服許鞍華率領的評審團做了勇敢的決定。當然其他入圍作品也都在水準之上,有些作品在技術或是其他環節甚至比《八月》更加成熟,但我以為《八月》佔了一個優勢——它可是詩啊,在這樣一首看似平凡輕盈,實則內蘊深刻的詩作之前,其他電影似乎都顯得重了或多了。

無意中發現了《八月》、《再見瓦城》及《樹大招風》和《七月與安生》這四部片的導演年紀相當,這批生力軍的受到肯定,華語電影在世代交替上似乎開啟了一個新的局面。
其中《八月》是內蒙導演拍的中國片,《再見瓦城》是歸化中華民國的緬甸華人導演拍的台緬德法合拍片,這兩部片的故事不約而同取材自導演個人特殊的生命經驗。
至於《樹大招風》和《七月與安生》,前者由三位新人聯合執導,他們出自鮮浪潮,可視為杜琪峰子弟兵;後者導演是曾國祥,他的前兩部作品由彭浩祥監製,今回則是由陳可辛監製。換句話說,上述兩組導演,分別在幾位風格明確的香港資深導演帶領之下,或是透過時代背景(《樹大招風》1997年回歸中國前夕的背景設定)拉出作品的張力與格局,或是找到新的切入角度(《七月與安生》中的後設敘事與自我認同)為打著IP名號卻幾近氾濫的中國式鄉愁和小清新文藝片另闢新局。




此外,《八月》和《七月與安生》兩部中國片也形成另一組對照。
《八月》導演張大磊1982年出生於內蒙古,父親是內蒙國營電影製片廠的剪接師,母親則在警察專校任職,教授馬列主義哲學。張大磊在俄羅斯學拍電影,回國後靠著當婚攝維持生活,首部作品《八月》全由素人擔當演出。
《七月與安生》導演曾國祥1979年出生於香港,父親是曾志偉,在加拿大長大,多倫多大學社會系畢業之後,他回到香港開始演戲,2010年和尹志文合導一部50分鐘的中長片〈指甲刀人魔〉及長片《戀人絮語》(這部片讓他獲得金馬獎新導演提名),以上兩片的監製都是彭浩翔。2012年,他又和尹志文及彭浩翔合作了一部《最後一夜》。直到2016年,曾國祥首度獨立執導長片《七月與安生》,監製是陳可辛。
張大磊和曾國祥年紀只差三歲,《八月》是張大磊自己的年少回憶,《七月與安生》曾國祥拍得則是兩個女生長達十餘年的友誼。1990年代之於《八月》是當下,不識愁滋味的純真少年,不經意在那個曇花開了又謝了的夏日裡,經歷了一個時代的結束;1990年代之於《七月與安生》僅只是回憶中的浮光掠影,儘管篇幅只有七分鐘,曾國祥卻是極有效率地,以準確地節奏讓觀眾在最短時間內,摸清七月與安生這兩個主人翁截然不同的性格與家庭背景,同時設計下一些懸念,為日後種種悲歡離合埋下伏筆。
值得注意的是,《七月與安生》當中關於1990年代的短短七分鐘,和《八月》整部片滿滿的1990年代是互通聲氣的。1990年代的中國,國有企業改革,許多人因此下崗,共產與集體神話不再,《八月》就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之下,有別於《陽光燦爛的日子》的輕狂,透過一個男孩的眼睛,讓我們看見時間如何靜止與流動,而在那樣的時間之河裡頭,有些人因應時勢開始進行改變,還有些人則是堅持不變。


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看《七月與安生》,自是饒富趣味。在片頭那場1990年代的回憶戲中,一群孩子集合在操場上,古靈精怪的安生自己脫隊不打緊,還帶著溫柔乖巧的七月一起放肆。正是這一次的冒險,締結了她們兩人的友誼,註定了她們長達十多年的牽絆。
當安生拿起石頭對準學校警報系統,使鈴聲大作導致全校陷入混亂,兩個女孩攜手趁機逃出校園。這是整部《七月與安生》中我認為最重要的一刻,對比日後她們相繼逃離家園、脫離同溫層、變換交友圈,年少時代這段小小的冒險,彷彿預言般告訴觀眾,日後她們將再次重演這樣的叛逆。唯有走出集體,她們才能定義個體,找到自己。
《八月》是透過個體的微觀,講述了整個時代;《七月與安生》看似強調個體唯有從集體中脫逃,才有辦法真正確立自己的存在。不過耐人尋味的是,《七月與安生》的後設敘事,卻又在歷經真實人生與虛構創作的數度辯證之後,曖昧地告訴我們天底下沒有個體真實這回事。
安生拿起了石頭,片尾卻告訴我們真正砸壞學校警報系統的卻是七月;安生率先離家,沒想到最後真正「離開」的卻是七月,而也正是七月,留給了安生一個「家」。所謂的「七月就是安生,安生就是七月」在剝除感傷主義的外衣之後,說不定是我多想,但我總覺得這個母題彷彿一個寓言,總結了屬於中國新世代的集體性,從瓦解消亡再到重新建立的史詩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