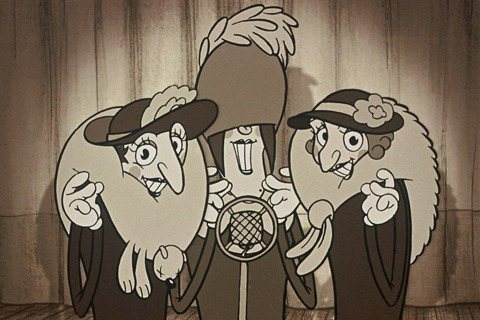浪漫而殘酷的《狂飆一夢》:天然獨世代眼中的黨外運動

很小很小的時候看過曾心儀本人,她來過我家幾次,那時只知道她是爸爸的眾多文友之一,覺得她好漂亮,不是世俗定義的美,但就是覺得她眼神犀利、說話專注的樣子很迷人。
曾心儀是作家,家裡有她幾本著作,我讀過《貓女》,雖然具體內容記不得了,但是對於這個書名印象深刻(那時《蝙蝠俠大顯神威》蜜雪兒菲佛詮釋的經典貓女角色可還沒問世呢),而且我還記得出版社是派色文化(小時候每次見到派色老闆,他都叫我「少年ㄟ」)。
爸爸因為辦文學雜誌,家裡文友來來去去,後來沒機會再見到曾心儀,漸漸忘了這個名字。沒想到再聽到曾心儀,一晃眼竟然將近30年,接連聽聞有人在拍紀錄片,被攝者是她,原來就是《狂飆一夢》。
電影上映首日,我進戲院看《狂飆一夢》,一方面好像是為了趁機回想一下30年前的童年回憶,另方面卻又有種在讀《鏡傳媒》(或早期《壹週刊》)人物專訪的感覺——曾心儀後來怎麼了?她又是基於什麼理由走上社運之路呢?她得到了什麼?因此失去家庭的她後悔嗎?如今她還寫作嗎?我以為自己可以在《狂飆一夢》裡頭找到答案,事實上卻沒有。
1991年5月,調查局逮捕四位青年,引發社會聲援,導致實行長達42年的《懲治叛亂條例》被廢除。雖然還沒有機會看到記錄這段歷史的紀錄片《末代叛亂犯》,但很佩服該片導演廖建華繼續拿著攝影機追蹤台灣民主軌跡,而且還是以獨特的角度切入。

記錄人生的迷惘
《狂飆一夢》分別拍攝兩位參與社會運動將近40年的「民主老兵」曾心儀和康惟壤現在的日常生活,穿插過往片段,偶而佐以身為記錄者的廖建華個人角度旁白。
曾心儀是外省第二代,是作家也當過記者,曾經為陳水扁等人助選,50歲時親身參與立委選舉,以0.51%得票率落選;康惟壤是早年很多社會運動的麥克風手,他笑稱自己沒有一個真正的職業,一生未曾領過兩萬元以上的薪水,沒有傲人學歷,不是知識份子,卻以自己的方式實踐左派之路,他曾參選議員失敗,如今和幾個同齡朋友合租公寓,雖然偶爾為房租發愁,但行動不便的他依舊關心政治。
曾心儀和康惟壤,他們抗爭了一輩子,賠掉家庭,但是並沒有因此榮華富貴,甚至從未真正步入政壇,他們不是聞名遐邇的民主鬥士或指標性人物,走在街頭,衝在前頭,像是不起眼的小草,壓不扁踩不壞,即使屬於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還是沒有放棄。
廖建華在這部紀錄片的延伸出版書《狂飆一夢:台灣民主化與沒有歷史的人》作者序〈明天你是否依然愛我〉中寫到:
更久以後,我感到空虛,那個空虛來自長輩們敘述的時候,我像是上完一堂枯燥乏味的歷史課一般,我也更確定,我好奇的不是他們如何抗爭,而是他們參與民主運動前的生活、抗爭時的生活、失去時代舞台之後的生活。我三十歲不到,而他們已經過完大半人生,多有六七十歲。如果幸福快樂的社會是我們持續不斷的共同目標,我們還在前往的路上,未來一定避免不了更多的運動、抗爭,我們該如何自處,也許從這些長輩們的身上見到一些什麼。
在我看來,廖建華的《狂飆一夢》和傅榆的《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有點相似,被攝者和台灣民主運動只是媒介,對於自己的人生、信仰和追求倍感迷惘的記錄者,所謂的「天然獨」世代,原來是想以拍片的方式尋找自己。

青春夢醒後的現實
已經年過70的曾心儀,和我記憶中(30多年前)的樣貌自然有所差距,講話速度與反應都變慢了,但是當她去找在鄭南榕喪禮上自焚的詹益樺好友「耀伯」(戴振耀)時,和幾個老戰友聊起當年抗爭點滴,她拿出保存了30年從街頭撿回來的紅色名條,臉上的熠熠神采,彷彿又回到年輕時候走在隊伍前端那個勇敢女子的飛揚狀態。
關於康惟壤,片中有個畫面令我格外印象深刻。那是他和幾個群眾雜誌電台時期的老友睽違20年的餐敘,出席的全是60歲上下的男人,話題從彼此近況轉到下一代身上,最後以「孩子到最後都是抱怨爸爸」作結。聚餐結束後,幾個阿公年紀的男人合力抬起必須靠輪椅代步的其中一名戰友,吃力走下樓梯,未料一個步伐不穩,差點摔成一團。
以上兩個片段,是《狂飆一夢》最打動我的時刻——一去不復返的青春,以及無法避免、無可抵抗的逼人現實。
我忽然想起《狂飆一夢》的英文片名「The Price of Democracy」,直譯是「民主的代價」。所以這部紀錄片是要討論兩位民主老兵為了推動台灣民主而付出的慘烈代價嗎?並不是。廖建華拍攝此片本意不在探討台灣民主化的經過,也不是真的在討論政治與社運,選擇曾心儀和康惟壤作為主角,更不是為了做出諸如「知識份子vs.草根江湖」、「女性vs.男性」等表面對比。
與其把《狂飆一夢》當成政治紀錄片,不如把它看成一部成長電影,廖建華緬懷了成長階段的激情時刻,然後感嘆了之後的滄桑、時不我與。

後悔與否,已不再重要
在典型的傳記片裡頭,主角無論怎麼歷經波折,他們終究是自己生命的英雄。然而《狂飆一夢》卻是相反,沒有所謂larger than life(在此或許可譯成非同凡響)這回事,這也是《狂飆一夢》和記錄田孟淑(人稱田媽媽)生平的《牽阮的手》最大的不同之處。廖建華其實並沒有真的要求曾心儀跟康惟壤面對鏡頭,回答「為社運抗爭付出這麼多到底值不值得」這個問題,而這也從來不是這部紀錄片的拍攝緣起或中心思想。
參與黨外運動,是曾心儀和康惟壤這兩位被攝者年輕時逃離家庭,尋找歸屬感的方式,時至今日,他們後悔也好,繼續茫然困惑也罷,《狂飆一夢》的存在,為的不只是追憶他們青春年華曾經的慘烈與美好,更是為了將夢醒之後恍然發現青春不再,除了面對現實別無他法,那種不上不下的尷尬局面,鉅細靡遺地記錄下來。
就這點來說,片名「狂飆一夢」四個字真是傳神。有點悲切,有點殘酷,卻又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