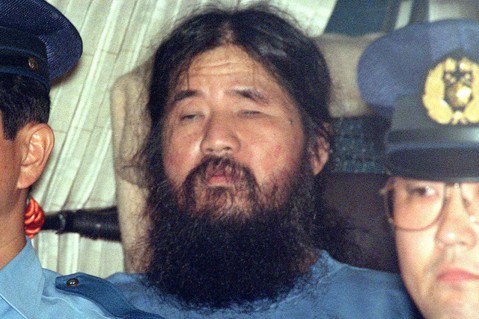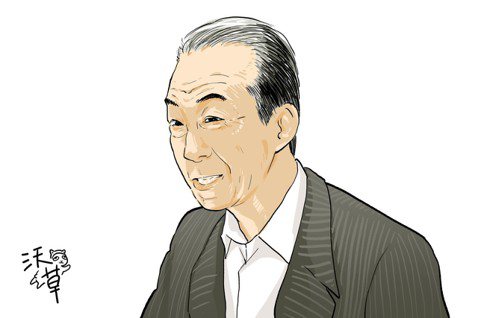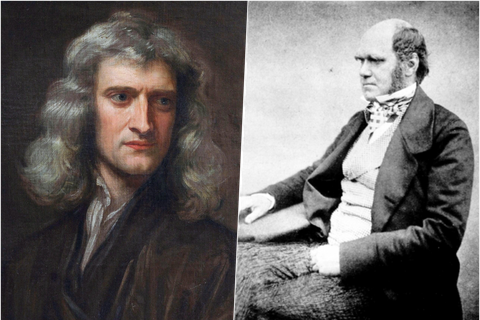「悔改而死」是為了死囚,還是為滿足國家控制死亡的權力?

裁判員審判中第10個死刑判決案例,是大阪此花區的小鋼珠店縱火殺人事件。
這個事件中,辯方展開絞刑違憲論的論述,著眼於絞刑是憲法禁止的「殘虐刑罰」。《日本國憲法》對於死刑既無特別肯定也不否定,不過第36條中明確禁止殘虐的刑罰。
判決中認為絞刑不算是「殘虐刑罰」,符合憲法。不過另一方面,也稱不上最佳的死刑方法,對現狀丟出了一定程度的疑問(大阪地方法院2011年10月31日判決)。
絞刑違憲論——著眼於日本現行刑法執行死刑的方法只規定了絞刑這一點——企圖對死刑方法提出異議,來抑止死刑判決或死刑執行。姑且不管死刑的存廢與是非,或者死刑是否合憲這些根本問題,這個論點將焦點鎖定執行方式絞刑上大作文章。
這麼一來,假如絞刑被視為一個問題(被認定殘虐),在現行刑法中「死刑……以絞刑執行」,僅規定死刑執行方法的現狀下,將反射性地無法進行死刑判決或死刑執行,這種法律技術企圖獲得這樣的效果。
因此,這種論述就算可以迴避該審判的死刑,可以暫時阻止不久將來預計執行的死刑,然而一旦採取立法措施因應,增加絞刑以外的執行方法,此法將立刻失效。由此看來其實是一種偏離本質的討論。
然而這其中也包含何謂不殘虐的死刑、何謂人道死刑等問題。這些問題看似與死刑存廢論、是非論的討論次元不同,其實在深層密切相關。
其中有何種關聯,就是本章要討論的主題。
日本的死刑法制史
在日本,如同大家所熟知,分為切腹與斬首,斬首反而是一種恥辱。切腹和斬首都是只適用於武士階級的刑罰,而對當時的武士階級來說,切腹和斬首的差異好比天與地。切腹是「得以自裁的武士」之象徵,「所謂武士道,就是對死的覺悟」之精神性。切腹作為一種死刑,其特殊性甚至讓人懷疑其刑罰性。
那麼武士階級以外呢?江戶時期的刑罰規定是典型的身分刑法,武士階級與除此之外的庶民階級運用的是完全不同的刑罰體系,而武士以外的庶民階級適用的死刑也有所區別。
比方說,庶民刑法中標準的死刑就是「死罪」,比此輕的死刑為「下手人」,更重的死刑為「獄門」。同樣是剝奪生命的刑罰,「死罪」在處刑後遺骸歸公,作為試砍和解剖之用;如為「下手人」,遺骸可歸還家人;「獄門」的情況表示首級會懸掛在獄門儆示。
這些對庶民執行的死刑,皆用刀斬斷首級,卻與武士階級的「斬首」不一樣。對武士的斬首會在特定刑場,於白日下實施;對庶民的斬首則會在牢內執行,因此刑罰上並不稱之為「斬首」。
死刑也包含死亡方法,其刑罰的性格會受到執行方法所左右。
也就是說,所謂死刑,並不是單純剝奪生命的刑罰。這是一種以特定方法賦予死亡的刑罰,而該特定方法中,存在著刑罰的重要意義。所以,本於人道死刑這個概念,嘗試藥物注射等讓死刑無色化,不免讓人產生疑問。若進一步讓死亡方法無意義化,只會更加失去其刑罰的本意。
換句話說,死刑是以一種被賦予特定意義的方法,強制死亡的刑罰;反過來說,該特定方法即是問題之一。
那麼強制「死亡方法」還有其他哪些問題呢?或者並沒有問題?
死刑的感動與啓發
現在日本死刑的樣態與江戶時代不同,具備特殊的意義。
日本的死刑如同前述,執行方法規定為絞刑,但是除了執行方法的問題之外,整體看來具有極特殊的一面。
最能明確佐證此特殊性的,就是到死刑執行為止的期間。日本有意識地讓死刑確定後到執行為止,間隔相當長的時間(統計上平均為7年10個月)。
儘管在《刑事訴訟法》中規定,死刑判決確定後,6個月內必須執行死刑——說得更詳細是6個月內發布死刑執行命令,之後5天內必須執行絞刑(《刑事訴訟法》第475條第2項與第476條)——卻還是有這樣無視法律的常態。
至於為什麼要這麼做,可能是因為希望死囚最後能悔改,再接受執行。在這段期間中,會有所謂「教誨師」的虔誠宗教家協助教化。現在的宗教教誨由於宗教自由,只在本人期望時進行,不過戰前則是強制執行。
日本的死刑當局(審判相關人員、監獄相關人員)抱持著什麼樣的死刑觀?那就是「唯有洗心革面後再接受死亡,才是最高的代價」。他們認為,死囚要先面對自己的罪行、深刻自覺,也就是洗心革面。洗心革面後再接受死亡,這樣才有贖罪的意義。這就是他們所認為的「以死償還」。
所以,他們也會談到死刑的積極意義,例如認為因為有死刑,犯人才能真正更生云云。
這樣的死刑觀認為,死刑在刑罰的感動與啟發上,具備無期徒刑等其他刑罰所沒有的戲劇性改善效果。犯人透過面對死亡,才終於理解自己所作所為——剝奪他人生命——的意義,也才真正了解做出這些事的自己。其他的刑罰,絕對無法期待有「洗心革面」等如此戲劇化的更生效果。
這個觀念從好的一面來看,或許可以說是藉由死來肯定生,或者也可以視為藉由死刑來肯定人性。

死囚與哲學家的對話
很諷刺的,品川風俗店命案相當可以象徵日本死刑現狀。這是一樁發生在阪神大震災、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的同年(1995年),於東京都風俗區發生的特殊殺人案。
一間店鋪擴及品川區和港區的風俗店(SM俱樂部)男性員工殺害老闆和店長,將店占為己有。老闆和店長每個月靠經營風俗業有超過一千萬日圓的暴利,而眼紅的員工找來自己的雙胞胎哥哥和曾經混過幫派的人,引發這次事件。
簡單來說,就是一樁圍繞著風俗行業的豐厚油水,在瘋狂價值觀中產生的社會暗處弱肉強食命案。這個事件的主犯員工被判死刑(東京地方法院1998年6月5日判決、東京高等法院2001年9月11日判決、最高法院2005年10月17日判決;其雙胞胎哥哥為無期徒刑)。羈留期間,在獄中發生戲劇性的變化。
面對死刑,他開始內省「自己有沒有求善之心」,思考蘇格拉底思想中「何謂活得良善」,開始和某位女性哲學家以書信往來的方式,進行關於殺人、死刑、「生與死」等各種哲學對話。對話對象是前女性雜誌模特兒的年輕新銳女哲學家,因而造成話題,兩人之間往來的書信同時刊載在週刊雜誌上,後來發行單行本,還數度再版(池田晶子=陸田真志《死與活——獄中哲學對話》新潮社)。
書中提到,被告人表示「死刑制度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有像我這樣的犯罪者」「犯了罪的人說要廢止死刑是不對的」,甚至斷言「自己獲判死刑是好事」「可以帶著幸福的心情接受死刑」。單行本出版後第十年執行死刑,這個時候曾經與他心意相通的女哲學家已經早逝。
「悔改而死」的欺瞞
現在日本的死刑執行概況大致如上。最理想的狀況是死囚重新自省犯下的過錯、悔改、接受自己的死亡,當局也預設在這個前提下執行死刑。
然而,「死囚面對死亡、自覺罪行,洗心革面」「洗心革面成為『好人』,接受死刑,然後赴死」「這才是最高的代價」等理念,實在太美好也太虛假。從品川風俗店命案來看也可以知道,其中實在太不自然,而且完全無法保證當局是否如此希求。或許只是想以國家所希望的特定方法來強制死亡而已。
舉例來說,在執行死刑前的拘禁期間,採取徹底的防止自殺措施。如果死囚在死刑執行前嘗試自殺,即使是瀕死狀態,或者即使可能留下嚴重後遺症,都必須盡量搶救。救回這條命後,執行死刑。
這種現象不僅限於日本。不過,這也是一面映照出日本死刑執行之欺瞞的鏡子。如同前面所說,國家絕不會讓死囚自殺,企圖以死刑來斷絕其生命。即使死囚靠個人的力量面對死亡、自覺罪行而嘗試自殺也一樣。不能縱其自殺,必須鄭重以國家之手來執行。
也就是說,日本的死刑執行希望「死囚自覺罪行、洗心革面」「洗心革面,接受死刑,然後赴死」「這才是最高的代價」,這其中偽裝成「為了死囚」,就是一個謊言。不見得考慮死囚或罪與罰的本質,也並沒有考量到被害人的心情;或許多半是國家的思考、盤算,是日本國家如此期望。
連死亡方法的心態,都必須絲毫不差地符合國家想法,豈不是連死亡的時間和內在都必須依照權力的意欲?在這裡,真正的意圖或許只是希望死囚能依照國家的意思死亡。
光是強制死亡本身還不滿足,這樣的做法可以說試圖跨進個人內在,強制控制其「死亡方法」的精神面。不僅如此,從死刑的確定到執行之間的時間,到死之前如何度過最後的人生,都受到權力方的控制。
日本的死刑執行是讓死囚依照國家期望的方式活著,然後死去。整體的色彩無疑充斥著「個人(死囚)該有的樣態」之國家精神。
控制死亡方法的貪婪權力
這麼說來,這種樣態可說就是傅柯所謂的規訓權力。因此,我們不該單純地把當局想法當成正當的理念。假如照單全收,或許只是順從死刑權力那雙「看不見的手」。
日本死刑執行的現狀有明顯特徵:採用「密行主義」,當天早上突然告知即將執行(早餐後告知、上午執行完畢,也不通知家人);不允許接觸他人,實行「晝夜完全獨居制」(運動、入浴分別在單獨運動場、單獨浴室中進行);以穩定心情為名目,限制面會、通信等。這些都與日本死刑執行的精神主義相關。因此,儘管受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勸告、國際社會的譴責,也始終不更改,反而強化其特性。
傅柯批評,近現代國家介入人類的生命,企圖將個人改造為對國家方便的存在。他也提出警告,國家權力出於這個目的,甚至開始規範個人到「該成為什麼樣的人」的自由層次。
日本的死刑執行尋求極為特殊形式的「死亡」。
這和該採用絞刑或斬首刑,或者該尋求更加「人道」的方法,轉移為電椅、毒氣室、藥物注射的討論又不同;並非客觀執行方法的討論,而是更加敏感且深層的問題。
所謂死刑,是以一種被賦予特定意義的方法來強制死亡的刑罰,在「賦予死亡的方法」上也有重大意義。不過現代法治國家中,並不允許採用殘虐的死亡方法。那麼死亡方法的內在又是如何?可以對死囚強加倫理概念嗎?可以強加國家精神嗎?
死刑問題包含「國家可以涉入個人內在多少?」這個與個人內在自由相關的論點。其中可能發生傅柯所強調的人類自由危機,也並非杞人憂天。
像日本當局一樣,將死刑視為終極的代價,並認為這是一種人性尊嚴的想法,也很接近我國固有的共通情感「物哀抒懷」,我們確實也很自然而然地接受。另外「罪行—制裁—死亡(=救濟)」這個循環,令人想起注定與死亡密不可分的人類存在之編劇手法,從深處撼動了我們在人性根源處,希望從自己的死亡中找到救贖的願望。再者,儘管是有罪的死囚,人確實也會藉由自己的死,奇蹟式地成就其主體性或者守護自己的尊嚴。
然而,將內在願望疊影在他者的死刑上,或許只會導致自他生死觀的界線模糊。沒有任何人能保證,這不是一種單純的幻想。
我們不應該肯定日本死刑執行的一切,反而應該察覺到在這其中權力的貪婪技術。
※ 本文摘選自《死刑肯定論》,原文標題〈第十章:絞刑、電椅、毒氣室、藥物——死刑執行的方法論〉,更多內容請參本書。
《死刑肯定論》作者:森炎譯者:詹慕如出版社:光現出版出版日期:2018/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