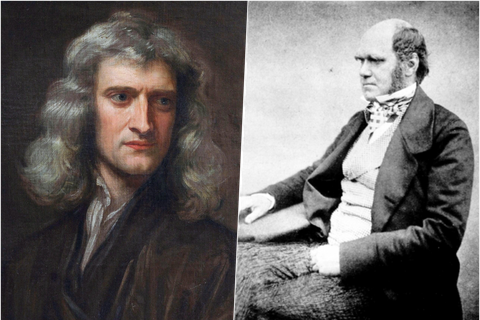左派早星陳映真:他的最後一次動搖,與最終獻祭

在「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前的整個1980年代,是陳映真文學影響力最輝煌的時期。在小說創作方面,陳映真發表了「白色恐怖三部曲」〈鈴鐺花〉、〈山路〉、〈趙南棟〉三個中短篇,是他的高峰之作。其中〈山路〉更是毫無疑問的台灣文學經典(雖然他本人不會喜歡這個歸類)。這些作品既保留了陳映真獨有的憂悒、神祕氣質,又有非凡的歷史意義,見證了一段被官方湮滅的左翼故事,一掃此前「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所引來的「意念先行」之譏。
陳映真與《人間》雜誌
更為影響廣大的,是陳映真在1985年創辦了《人間》雜誌。《人間》雜誌是彙集了陳映真此前累積的所有經歷,全力施為的結晶。比如從「大漢計畫」以來,對各種媒介的興趣;以及1983年到愛荷華大學參訪時,所接觸到的「紀實攝影」,這都促成了《人間》雜誌極為經典的報導攝影風格,影響了無數同世代及後代的媒體工作者。而陳映真深厚的文學修為,與他身為左派知識分子對底層民眾的關懷,也讓他能夠帶領一批年輕記者,把台灣的「報導文學」提升到空前的高度。
如此秀異、深沉、精緻且不媚俗的圖文組合,使得《人間》雜誌幾乎成為台灣歷史上,「良心知識分子當如是」的標竿。他們報導主流媒體不願意處理的議題,並且透過高品質的圖片與文字,時時引動輿論,乃至促成某些政治改變。在許多議題上,《人間》雜誌的報導都是先鋒性的,包括但不止於同志議題、環保議題、農民議題、工人議題、二二八事件、原住民議題⋯⋯比如創刊號以「在內湖垃圾山上討生活的人們」為題,就引領人們關注了一個近在咫尺、卻長年遭到忽略的「底層」;該刊封面是一名衣著破爛、神情瑟縮的少年,全幅的黑白照片,至今看來仍十分震撼人心。接下來幾年內,《人間》雜誌會繼續創造更多震撼:追蹤原住民受壓迫的「湯英伸事件」、報導環境運動的「鹿港反杜邦」,以及關注罕見疾病「白化症小孩」的專題⋯⋯
苦熬多年,四處尋找實踐可能的左派早星,終於找到了發光的方式。
《人間》雜誌與1980年代人心思變、社會力湧動的風潮結合起來。在經濟成長到一個階段,人們開始有餘裕思考溫飽以外的問題時,《人間》雜誌提供了一道完全不同的窗口。政治不再只是教條的國共之爭、遙遠的左右之爭,台灣也不是只有統獨之爭一個重要軸線。陳映真多次不無得意地說,《人間》雜誌做到了許多本土派都沒能做到的,真正深入去瞭解台灣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事情,這是即便他的論敵都必須承認的。
沒錯,他確實有得意的本錢。在台灣的歷史上,恐怕沒有哪一個雜誌曾經發揮過這麼全面且深刻的影響力。如果你現在去調查四十歲以上的教授、記者、文化人甚至是政府官員,問他們對陳映真的印象是什麼?很可能既不是〈我的弟弟康雄〉、〈山路〉這些小說,而是《人間》雜誌。而他們之中最具理想性的,可能還有很多人會告訴你:我就是看了《人間》雜誌,才決定走上這一行的。

深陷統獨焦慮的陳映真
不過,陳映真本人的政治孤獨,並不是《人間》雜誌的成功就能夠化解的。他抱持著左統的理念主持這份雜誌,但它廣大的群眾卻未必與他同調。這使得《人間》雜誌始終面臨一種尷尬的局面:當它又報導了某些不為人知的議題時,便會收穫一片喝采;但當它偶爾在某些文章,表露出陳映真的左統立場時,讀者來函的反應就會非常直接——「貴刊的社會性報導很好,應少談政治。」
畢竟在1980年代,社會力的湧動並不只會助益特定的陣營。甚至可以說,由於「鄉土文學論戰」結束之後,並沒有任何陣營受到政府的直接清算,因此各方的知識分子都更敢於試探政府的底線,一點一點講出真心話。陳映真的「白色恐怖三部曲」,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而本來勢力弱小的台獨、本土派陣營,更是在這段時期急速擴張,逐漸在社會運動和知識分子的圈子裡占有一席之地。
面對此一局面,陳映真的統獨焦慮是更加深刻了。他不厭其煩地在文章與訪談中駁斥「台獨」,不只冗長地重複他所認知的台灣史,更創發了一套獨特的論點。這些論點大致如下:
- 在台灣,真正的問題是階級問題,而不是族群問題。
- 在社會各部門中,本省人與外省人是可以和睦相處的,並不像日治時期,日本人跟台灣人有明確的族群界線。
- 如果台灣持續跟中國分治下去,未來確實有可能形成一獨特的共同體。但是,從歷史來論證台灣族群的獨特性,是不可能成功的;此刻台灣也並沒有這種條件。
在某些層面上,這些說法言之成理。不過,即便是在論述第一、第二點時,陳映真也注意到了「政治的高層都是外省人」,但他往往會用「政治的底層也有外省人」來辯解,實際上這並無法解消「政治的高層沒有本省人」的歧視性事實。更何況,是否擁有明確的族群界線,並不是一個國家能否獨立的關鍵——他在1981年接受新加坡媒體訪談的〈人性・社會・文學〉裡,便毫無保留地稱新加坡「絕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好像美國文學從英國文學傳統中脫離而成長」;上述理論很難解釋為何新加坡可以獨立,而台灣不行。
最有趣的是第三點,這其實透露了陳映真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意了台灣獨立是有可能性、甚至是有正當性、會隨著時間自然發生的。當他說未來可以、目前不行的時候,實際上並未提出足夠明確的標準,來說明「目前」為何不足以獨立。
——這或許,正是他在1960年代接觸台獨運動者,所留下的某些思想遺痕吧。
另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狀況也令他感到焦慮。在1970年代以前,台灣不容易取得海峽對岸的消息,陳映真尚能對「祖國」保持一定程度的幻想。然而隨著兩岸的訊息逐漸彼此滲漏,陳映真開始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一個會整肅異己、壓制民主運動人士的政府。比如1979年的「西單民主牆事件」,民運人士魏京生繫獄,陳映真便不斷在各種場合聲援,並且多次表達了他的困惑。
如果祖國沒有想像中那麼好,那該怎麼辦?最能代表此時陳映真在統獨議題上「內外交迫」之感的,當屬1984年〈陳映真的自白〉這篇訪談。他再次重複了對台獨的批判,但同時也以罕見的直白批評中國政府:
⋯⋯問題在於目前居然把矛頭指向人道主義、指向社會主義內的異化,這些提法,我是反對的。
所謂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是相對於過去幾十年來中共各種鬥爭中對「人民內部」的不可言喻的殘暴、非人作風而來的。在過去幾十年,人——受到了最不可置信的摧殘。把人當作人看待,反對人與人間瘋狂的相殘相殺,如果是什麼「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那麼,讓一切有良心的人民、知識分子全是這「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者吧。
這時候的陳映真,還不是當代讀者印象中的那個,對所有中國的惡行都不置一詞的陳映真。他仍然衷心相信左派理念,但他也很明白不應當袒護中國的所作所為。但是,內有台獨勢力增長,外有祖國革命的墮落,統一大業究竟要如何堅持呢⋯⋯?

19890604:一顆橙紅早星的忽明忽滅
陳映真最終如何調適他的心情,外人是難以得知的,我們只能看到最終的結果。解嚴後的1988年,陳映真和一群堅貞的統派共同創立了「中國統一聯盟」,陳映真擔任創黨主席。隔年,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中國以坦克鎮壓學生運動,震驚了全世界。台灣的知識分子大受震動,幾乎一面倒地批判中國。而在這起事件後,陳映真確實也發表了若干「批判」的聲明,但他的批判卻是各打五十大板式的,固然批判了中共當局不應血腥鎮壓,卻也批判學運一方的主張將引入西方的資本主義,反而無法爭取到自由——這當然是左統人士才會有的獨特思路了。
在此,陳映真對「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袒護」,或許有著連中國官方都未必明白的考量:對他而言,這起屠殺最可怕的後果,是幾乎斷絕了統派在台灣的發展餘地。當坦克輾過學生之際,不管你用什麼說詞、建構多少理論,都不可能說服台灣人跟這樣的國家統一了。陳映真在事件之後的種種發言,其實都帶有「修補統一可能性」的「苦心孤詣」。
由此來看,就不難理解為何陳映真會在隔年做出驚人之舉。1990年,陳映真以「中國統一聯盟」主席的身分,率團訪問中國,並且受到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的接見。統盟連續發表了〈中國統一聯盟大陸訪問團抵京聲明〉、〈中國統聯訪問團與江澤民的對話錄〉等文件,宣揚統一思想。
宣揚統一思想,這大家都很習慣了。但是,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在中共屠殺學生的隔年,率團去給江澤民摸頭,讓中共官媒可以做出一則〈共話祖國統一:江澤民總書記與台灣著名作家陳映真先生的談話〉的報導,這可突破了絕大多數台灣人的忍耐極限。即便是數十年的老戰友如尉天驄、黃春明,也都難以理解他對六四天安門事件,乃至於文化大革命的態度。2007年,尉天驄隔海憶念他與陳映真共同經歷的那個時代,寫下〈理想主義者的蘋果樹〉一文,文章的最後也是凝結在這一點上的:「但願他在病癒後能夠細緻地、深入地認清中國幾十年來的歷史和現實,在經歷連番的歷練後,再一次展現自己。」
然而,陳映真從1990年代起,恐怕就已經沒有打算回頭了。他決意要把一生的聲譽和影響力,統統獻祭在祖國統一的祭壇之上。如果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發生,會讓台灣人對統一失去信心,那陳映真一心所願的,就是動員自身所能動員的一切,縫補海峽之間越來越大的裂痕,為窘迫的中國政府解圍。即便這麼做,會使自己沉沒在海峽政治無盡的漩渦裡,也在所不惜。
於是,「1989」幾乎可以視為「陳映真的最後一年」。這一年,《人間》雜誌不堪財務壓力,在第47期停刊。這一年,他站在了坦克的那一邊。人們甚至難以確定,他夢裡是否還有那顆橙紅橙紅的早星。

※ 本文摘自《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戒嚴台灣小說家群像》第八章〈山路是這樣走絕的:陳映真的文學、政治與孤獨〉,該段落原標題為〈最後一次動搖,與最終的獻祭〉,大塊文化授權刊登。
《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戒嚴台灣小說家群像》作者:朱宥勳出版社:大塊文化出版日期:2021/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