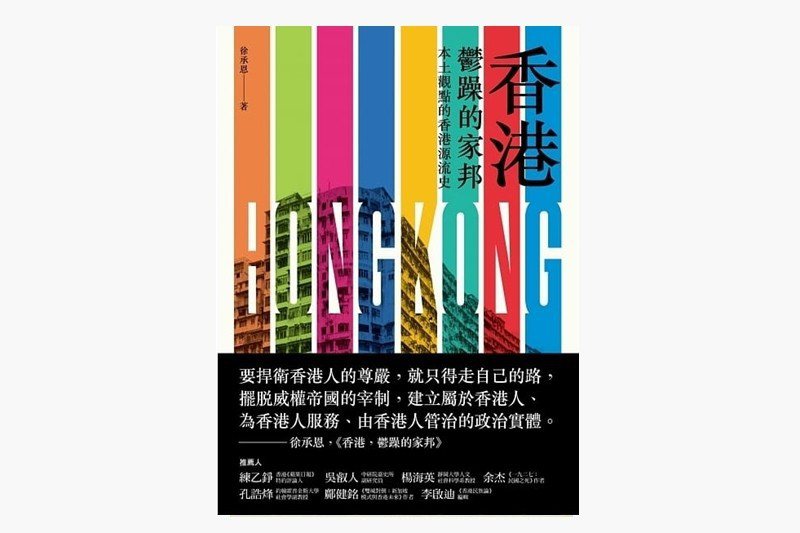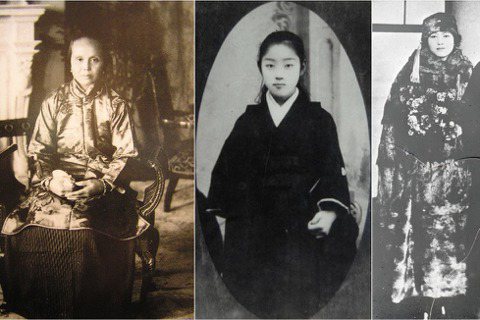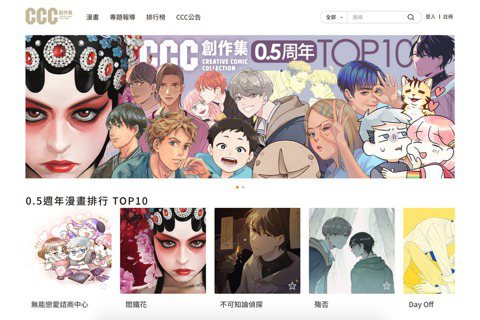何必再當想像的中國人?評《香港,鬱躁的家邦》(上)

2017年,本業為醫生的青年民間學者徐承恩,憑藉對家鄉的真切摯愛,以及社會科學的紮實訓練,花上數年的工餘時光,完成了40萬餘言的《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下簡稱《鬱躁家邦》)。
聽出版界的朋友說,該書在台灣的銷量並不理想,這或許是因為,台灣書市太過偏食主流歐美典範,而輕忽自身東南亞脈絡。然而,在香港反送中運動迭遭頓挫的此刻,這樣一本獻給民族大眾的前瞻性歷史著作,更加值得我們細細捧讀。
顯然,《鬱躁家邦》立志為香港這一新興海洋民族寫下自傳。為了展現出帝國邊緣的「海洋香港」與中央集權「大陸中國」在長達千年之時段中,無法忽視的發展分歧,這本書繼承了近年香港國族主義運動的思想成果,試著為了今日躁動不安的700萬人民,在未來可能出現的歷史機遇中,找到一處足以援引、依恃的往日記憶。
也因為如此,《鬱躁家邦》並不從政權興衰之傳統角度,去談將相王侯與攻掠征伐,而是藉由述說往事,謹慎地在歷史中,建構一個足以支持「公民國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運作流通的社會基礎。
就這點來講,同樣面向大洋、地處貿易要衝,並且承受近代帝國主義剝削殖民的台灣讀者,很容易在一海之隔的香港姊妹身上,看見許多具啟發性的異同。綜觀《鬱躁家邦》的治史策略,有四個面向尤其值得深思,分別是——海洋民族源流、商人自治傳統、公民社會與國家政權的競合,以及作為兩面刃的文化中國想像——以下且讓我們逐一討論。

海洋民族源流
首先,本書肯定了香港人在文化與基因上的駁雜出身,並追溯他們漫長的「海洋民族源流」。若我們回顧早期歷史,比漢族更早馴化稻米,在飲食、語言、風俗、性別權力位階等面向都迥異於中原的「百越」族群,一直是嶺南地區的主要文明。
而長久以來專注在北方平原權力鬥爭的「中原帝國」,一直到15世紀前,都不曾有效控制這塊「蠻荒化外之地」。明代以後,隨著中原帝國持續擴張,以及漢族本位的種族迫害與圈地運動,嶺南地區的原住民族群最後採用了易宗改姓、虛構族譜等「偽裝成漢人」之生存策略,或者主動選擇避居江海,成為舟居水行的蜑家船民。
另一方面,由於大陸南緣多山多岸的地理因素,嶺南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東亞海上貿易網路的重要輻輳點。然而,面向海洋航路這種經濟型態,卻與中原帝國那藉由徵收穀物來確保國家資源積累的農耕文明,存在相當的緊張關係。也因此歷代中原王朝皆透過禁海令、鎖國政策,嘗試壓制嶺南社會內部「向海洋開放」的潛在不穩定因素。
這些不斷逃離中央管制、鑽營空隙、生機勃勃的沿海地帶,甚至還收容了許多試圖逃離中央集權的北方移民。而該區所容納的那些「拒絕國家的人」,正好共同譜寫了海洋城邦的史前史。

商人自治傳統
本書第二個重要面向,則是去勾勒了一個有具有自利性格、透過宗族鄉黨等民間組織所實現的「商人自治傳統」。
早在唐宋時期,大陸邊緣的底層平民,便因為與東南亞海域間蓬勃的走私、運輸、地下經濟,而逐漸成形與中央政府互相拉鋸的交易網絡。鴉片戰爭後,中原帝國正式將香港交託給英國殖民者,於是,這塊窄小卻豐饒的土地,理所當然成為庇蔭海洋貿易族群的聖地。他們將在此延續、並展開與大陸型封建帝國截然不同的歷史命運。
香港正式開埠前後,英國殖民當局高度仰賴在中國貿易的洋行商人,敦請他們作為政策諮議的對象。然而,對於遠渡重洋的英國企業家來說,官家管制與自由貿易之間,實際上總有利益衝突。
這種情勢也意味著,「商人階層」將於往後的100多年,在香港社會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此後,隨著香港越加繁榮,英國殖民當局更進一步明白,如果要有效降低殖民地治理成本,他們就需要與本地的華人商會積極合作,並開放參與公共事務的權限。
1868年成立的「南北行公所」,就是這一理解下的直接產物。殖民地政府授權並鼓勵地方仕紳進行民事仲裁、團練招募、消防隊訓練等項目,華人商會也籌辦具有公益性質的濟貧醫院,以分攤香港急迫的社會福利需求。
自香港建城以來,商人階層始終保持著充沛活力,組織糧食救濟會、協調勞資緊張、參與愛國主義罷市罷工運動,可以說他們是英國式「開明專制」殖民體制中,與統治當局保有微妙距離的民間政治勢力。
儘管香港華商確實維持了一處並不完全從屬於國家或政權的半獨立空間,用以進行有限的地方治理,但《鬱躁家邦》並沒有忽略「商業菁英自我管治」模式所存在之侷限。由於商人階級必然追逐利潤這一基本取向,國家方面常以經濟獎賞為餌,打造政商聯盟,並聯手壓制勞工大眾與市民權利。
港英時期的買辦集團、主權移交後的親中紅頂商人,他們均在香港歷史進程中,扮演了與帝國主義共謀的不光彩角色。或者成為外來統治者「以港治港」的工具,或者出於條件交換,而在議會中阻撓全民普選的實現。

公民社會與國家政權的競合
也因此,上述「商人自治傳統」的侷限,無可避免引出了第三個攸關「香港本土性」的重要議題:資產階級的有限自主,要如何上升成為制衡國家權力、具有批判性的公民社會?
為了補充「本土公民社會」中更有活力、更具批判性的另一側面,《鬱躁家邦》歷數了近200年來,香港公民運動的本土傳統。作為一個工商業繁盛的殖民都市,普羅大眾在資本主義經濟下所體驗到的壓迫與反抗,其實就是香港本土意識中,不可或缺的核心部分。
1844年開港初期,底層苦力因為不合理的人口登記費用,而發起迫使當局屈服的大型集體抗爭;1920年「香港華人機器總工會」則引領了莫之能禦的工會組建風潮,後年甚至成功組織了12萬人規模的大型罷工(約為當時人口的五分之一);而1970年代亦發生數次白領工潮,專業階級如護士、教師等聯合起來,促使港府在強大壓力下,允諾社福教育體系之內部改革。
本書讀者不難理解到,某種訴諸公義、籲求人權的「香港價值」,就在公民社會與國家權力的漫長競合中,成為一般香港人民的基本共識。
香港之所以存在這種「人權優先」傳統,顯然受到西方文明的正面影響。早在1920年代前後,英籍進步派人士就注意到了華人社會中普遍的蓄婢、童工、人口買賣狀況。於是他們在體制內持續對港府施壓、亦與保守華商周旋,並在1930年代後成功立法,以確保所有香港住民的最基本人權。
做為東西文明交界之地,香港從來都不只是受盡壓迫、飽嚐剝削的「被殖民地」。事實上我們必須承認,不管是民生富裕、言論自由與公民權利(儘管缺乏較積極的民主問責)各方各面,香港社會在20世紀大多數的時間內,都是整個東亞國際社會僅次於日本的佼佼者。這得歸功於歐洲文明所帶來的正面遺產,而港英政府也不斷地在制度內落實「人道、平等、自由」種種普世價值。
▍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