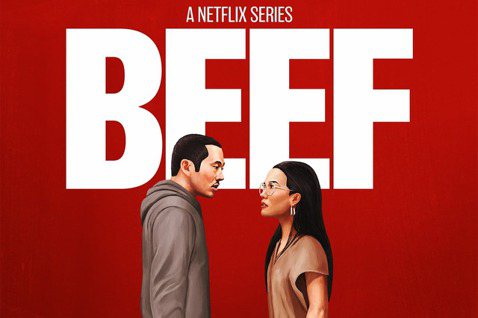無家者與他們被抹去的面孔——評金惠珍小說《中央站》

在偌大的車站中,人潮洶湧匆匆來去,有這麼一群人,你總是能一眼識出他們的不同,然後在下意識或許不到半秒的時間,你在腦海中模擬過一遍他們的人生,下一秒選擇避開。我們稱他們「遊民」「流浪漢」,或好聽點的「街友」,事實上便是「無家者」。
南韓作家金惠珍的小說《中央站》裡,也有這樣一座車站。
對人們而言,車站是分別是離散的地方,然而對他們來說,車站則是歸屬與安頓之處。故事開頭,一名男子拖著行李箱來到這座車站,即便在都市最繁華的地帶,夜深後的光景與白天人潮熙攘大相徑庭——有一群人以紙箱為床,以衣服為枕,日日夜夜「定居」在這方車站廣場中。
車站本身便是一個小型階級社會,無論是年齡、先來後到的順序,無處不是規矩。這名新來的青年似乎還血氣方剛,卻又孤懸於外,為了證明自己的不同,一心想與街友劃清界線,以證明自己還有翻轉人生的可能。他在泥洞中一再往上挖掘,卻只有更大的石礫落下,阻擋前路,也遮掩光線;直到不得不手心向上,才發現自尊終究是填不飽肚子的。
失去過往與未來,拋棄時間與空間
本書的副標寫著:「失去過往與未來,拋棄時間與空間」,這些無家者曾經擁有的大概只剩下過往。每個人大不相同,但像是必備的入場券般,大家幾乎都有一段轟轟烈烈的故事,談著過往的風光明媚——誰曾是公司老闆呼風喚雨,誰曾年輕有為背滿眾人冀望,但也都是曾經了。樓起樓塌,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那些虛幻的過去成為笑柄,也不再有人聽信。
於是,連僅有的過往都失去,無家者這才真的一無所有了。
男主角說:「覺得已經置身谷底了吧?不,地面根本就不存在。就在你以為抵達地面的那一刻,又會再次朝無底深淵墮落。」又說:「在年輕健康的我面前,這地方表現得最吝嗇冷酷,因為我所擁有的年輕,被視為了不起的本錢。沒有人明白,必須消耗的年輕多到吃不消,有多麼無助。」
此時,就在他的人生已無光芒之際,他遇見一名女人,女人騙走了幾乎是男人所有資產的行李,他也不在意。那是愛嗎?他說:「女人和我並未選擇彼此,令我們相遇的是街頭的人生,是聚積在車站內的時間。」或許是不是也不那麼重要,他只害怕她的離開,害怕他不能給女人更好的,以憤怒為形的焦慮,背後是兩個疲憊靈魂的同病相憐。
再多的希望依然將他打回原形,那是弱弱相殘,是自我剝削。這個社會宛如Netflix電影《絕命大平台》裡的層層階級,上層吃剩的食物才落下來,到了最底層已寥寥可數。面對這些稀缺的資源,只有最無情的人才能搶奪,最終導致他們的永不翻身,且愈加淪落。

刻意空缺的姓名,被抹去的面孔
我曾經在台北看過一個展覽,內容是邀請某街區的街友分享自己的故事,以及他們為何會成為街友。
結果出乎意料,大家既定認知中的「因為偷懶,不認真工作才會流落街頭」並非解答。反倒是許多街友都有固定工作,也都嘗試想進入勞動市場,但大多數的他們缺乏專業能力,只能做些薪水不高的體力活。有些曾經是中產階級,因為遭遇突如其來的人生變故而一夕失去所有;有些則是在產業變遷中被洪流吞沒,因而成為勞動市場中被犧牲的弱勢。
在資本社會的金字塔上,要爬上去太難,墜落卻容易得驚人。他們先遭到社會驅離,遭到朋友驅趕,一直退一直退,最後是自我放逐,把自己給弄丟了。
書裡的主角都沒有名字,男人是「我」,女人是「女人」,彷彿被抹去面孔一般。名字是希望的象徵,是祝福的文字,然而他們或放棄名字,或被剝奪名字,僅剩不被賦予祝福的生命。閱讀過程中,也迫使讀者將自身放入角色,如果我是「我」,我會如何選擇?我想,我們都不再能趾高氣昂地說:「他們墜落是活該,他們的遭遇是咎由自取」。
除此之外,作者也暗示著,我們似乎從來沒有好好了解這些面孔,車站中央是一群人的交通樞紐,是另一群人的邊緣地帶。社會稱他們為「街友」,諷刺的是,別說當作朋友,多少人甚至不把它們作為一個人看待。
一場不浪漫的流浪,一次無罪的放逐
南韓作家金惠珍用文字關注那些社會的離群者(outlier),上本小說《關於女兒》探討中年母親面對同志女兒的不諒解,把「擔心」包裝成「憤怒」與「恐懼」,但卻在這些世代歧異中,看見彼此的人生課題。
《中央站》則以車站作為人生修羅場,隱性的彼此戰鬥、爭奪,是社會底層的生活日常。本書也提供讀者看向這些模糊面孔的一個視角,思考他們因為什麼而失去家園。結構性的層層殘酷,回歸至作為人的質地,我們並無太大不同,只是因為運氣,因為機遇而造就天壤之別。但誰都可能墜落,每個人生的轉折都發生得毫無徵兆、不可預測,卻像地震引發海嘯,摧毀只需半晌時間與功夫。
這是不浪漫的流浪,這是無罪的放逐。我們直視貧困樣貌,在絕望中學習如何變得更溫柔,如何給予那些身處黑暗中的靈魂,一絲理解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