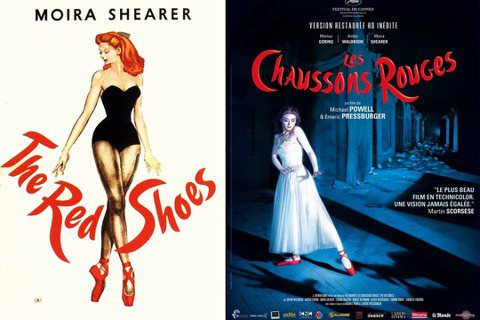《阮玲玉》看影史(四):再談費穆與吳永剛《神女》

嚴格說起來,我並非阮玲玉這位女演員的「粉」。在表演方面,她確實是個天才型的演員,但很多時候,眉眼之間,舉止之餘,總會閃過一絲絲不怎麼「正經」的態度。
正是這份態度,讓我卻步,讓我沒辦法完完全全欣賞、懾服在她的角色詮釋之下。很多時候演著演著,她嘴角就多了一抹笑意,手也就勾著勾著,勾到男主角的胳膊上來。想來,這也就是大導演卜萬蒼所謂的「妖裡妖氣」之形容吧。
然而,在「妖」之外,阮玲玉的模樣又有一分能勾住你記憶的魔力,一種難以言喻的「X因子」(X factor)、「明星魅力」(star quality)。不管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她就是在那裡,發著光,誘著你看她用那張臉龐和她嬌小的身軀,訴說故事。
真要看阮玲玉的電影,卜萬蒼的《桃花泣血記》或者《戀愛與義務》之外,當屬《神女》。吳永剛導演把阮玲玉妖饒的、邪佞的、衰弱的、堅強的、嫵媚的、崇高的所有特質,完美集成於一部電影當中,以「神女」來寫「女神」,讓阮玲玉永遠不朽。

重看《神女》
《神女》有過全部無聲的版本流通,也有過把字卡上台詞讀出來的版本。究竟它的原貌如何,很難判斷。總算在很後來的後來,國際影壇開始陸續將經典默片重新配上合適的音樂,《神女》也有幾個不同影展為它配樂,更強化了它的推廣價值。
吳永剛導演在聯華影業那群創作者當中,出身比較不一樣。他並非名門正派的優秀學校畢業,也不曾喝過洋墨水。但他由做中學習,從美工練習生做起,輾轉幾家不同的電影公司,也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半工半讀。《神女》是他的第一部劇情長片。
故事描寫阮玲玉這位「站壁」的流鶯,拚了性命要將自己的兒子撫養成人。她將辛苦所賺得的皮肉錢供養兒子上學,學習做人做事的道理,兒子品學兼優,表現出色,卻遭同學家長、校務董事等集體霸凌。老校長慈悲為懷出手相助,阮玲玉不堪肉體及精神折磨,在得知辛苦存下的學費被同居流氓竊走後,憤而將流氓殺死,入獄服刑,兒子由老校長代為照護,她在獄中憧憬著孩子光明的未來。
同樣是「窮人受壓迫」的題材,同樣是「被社會遺棄」的故事,《神女》的氣質與眾不同。它沒有激憤高亢的怒吼,而是不避醜、不揚美,忠實誠樸地將一個街頭流鶯呈現在觀眾面前,讓她母性的光輝自然而然地感動我們。
電影前段她為了躲避巡佐的取締,躲入流氓所住的小屋,心知自己今晚難逃惡霸的魔掌,之後那一股「豁出去了」的姿態,既淫蕩,又傲慢,既潑辣,又脆弱,藉由踩椅登桌、煙視媚行的舉止,戳破道德的假面具。
這是一場兩個風塵老玩咖的對決,而且,女的註定要輸。既然註定要輸,那就算了,「老娘不必跟你裝」。就是這姿態,她討了一根煙,叼了起來,抽了一口,徐徐吐出。

在《神女》片中飾演阮玲玉愛子的天才小童星,不是別人,正是聯華負責人之一、香港及上海電影先驅者黎民偉的愛子黎鏗。黎鏗模樣可愛,表演清澈不油滑。《神女》裡他有段表演節目,唱〈賣報之聲〉,可惜聲音不存。黎鏗日後成為著名演講家,口條清晰一直是他的強項。
至於吳永剛導演,《神女》等於向整個世界展現了他的才華,之後的力作包括《浪淘沙》、《壯志凌雲》等等。在1950年代後期,他因故被打為右派,好幾年無法拍片,待及重回工作崗位時,他和當時很多創作者一樣,以「避世」的心態,選擇遁入傳統戲曲的懷抱,拍攝戲曲電影,只專注琢磨藝術,不論時政。
這個階段的吳永剛依然拍出佳作,京劇《尤三姐》和越劇《碧玉簪》,盡皆迷人。前者由名伶童芷苓主演,後者不單是金采風的代表作,更啟發了李翰祥導演拍攝《狀元及第》。
吳永剛在文革期間受盡折磨,還好保住一條命,沒有像蔡楚生等老同事一樣命喪黃泉,文革結束後重拾拍片工作,擔任名作《巴山夜雨》的總導演,獲頒第一屆金雞獎的最佳故事片大獎。

再談費穆
至於前文曾經提過的費穆,雖然英年早逝,但其藝術成就極受後輩影評及論者推崇。在抒情與言志之間,費穆總能拿捏住優雅的分寸。
抗戰爆發之後,上海成為所謂的「孤島」,租界區內一方面紙醉金迷、歌舞昇平。一方面又因為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氣,而成為所有人精神的寄託、良知的依歸。電影產業在這個階段瘋狂而畸型地蓬勃發展,因為《木蘭從軍》的賣座,致使古裝愛國電影突然之間流行起來,一時之間《霍元甲》也好,《楚霸王》也好,紛紛開拍。
費穆置身這樣的狂潮當中,他也拍起古裝,也拍起愛國電影。但他的古裝和他的愛國跟別人又是不一樣的方式。
他拍的是《孔夫子》。

《孔夫子》不是多年後周潤發演的那部《孔子》。全片洋溢著理想淑世之情懷,以孔夫子與學生水濱閒話。「盍各言爾志」揭開故事序幕,演到結尾之前,周遊列國、陳蔡絕糧、顏回病歿時,老夫子四望徒兒,個個歷經滄桑,回想自己為了一個摸不著的理想,拉拔大隊人馬走了這許多年,究竟為的是什麼?這樣的敘事力道和厚度,不僅深刻,而且令人回味。大格局故事裡的人情味便油然而生。
周潤發那部《孔子》,不叫《孔夫子》,難怪少了這一層理想的瑩輝,多的是缺筋少骨但肉厚脂肥的情節,不需太花精神就能獲得娛樂,但如果觀眾企圖從影片中再多得到一些什麼,可能就沒有了。
記得《孔子》影片結尾是老夫子回到魯國,城門外千萬人迎接,孔子下車之後痛哭流涕,淚流滿面,然後接到電影開場時白髮老仙人作完《春秋》逝世。《孔夫子》的結尾呢,老先生帶著大隊人馬離開魯境,最後死的死、散的散,回家之後,杏壇庭院已空,夫子遙想當年與弟子射箭、訟詩、言志,不禁老淚縱橫,崩倒於樹下。
此刻,孔門成就最高的弟子子貢率領門徒舍人等前來請安,一個一個鮮衣燦冠,頓時一改寂境,原本的空庭瞬間成了桃李滿門,個個是「君子」,有的報效國家,有的富甲一方,有的安居樂業,有的貧病不改其顏色……以此為結,理想和哲思便自然而然流瀉出來,這就是費穆的精神,這就是華語電影裡最珍貴的文人氣質與人文精神。
把我高高掛起
在邱剛健所編寫《阮玲玉》的電影劇本裡,有一場戲最終未拍,紀錄在這裡,恰好為這一系列從《阮玲玉》看電影史的短文做個結束。
它寫的是阮玲玉在聯華酒宴結束、與唐季珊前往匯中飯店跳舞時,汽車途經卡爾登戲院門口,幾個工人把電影《國風》的預告看板掛起來,畫著阮玲玉執筆沉思的特寫。阮玲玉叫停了汽車,搖下窗,凝望著高高的大看板上,自己的形象。醉態可掬的她指了一指,說道:「我!」
車子重新開動,工人整理一下繩子,看板左右晃一下,開始上升到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