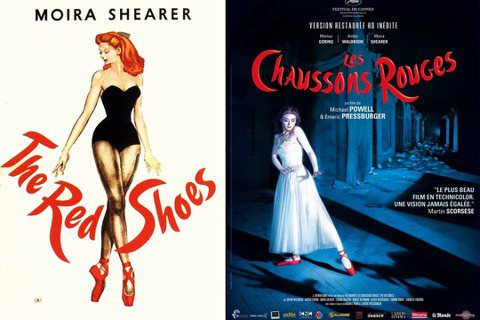一氣呵成的《1917》——談「一鏡到底」的美學與迷思

(※ 本文有雷,斟酌閱讀。)
最早知道這部《1917》,是因為跟網友聊起它的導演山姆曼德斯(Sam Mendes)企圖要以「一鏡到底」式的視覺效果,完成這部小傳令兵在戰場上送信的劇情片。
朋友大加讚美曼德斯導演稍早在007電影《惡魔四伏》(Spectre, 2015)開場,一顆長鏡頭拍出墨西哥亡靈節遊行場面的技藝;我則憶起幾年前看《鳥人》(Birdman, 2014)、《神鬼獵人》(The Revenant, 2015)時的種種不適惡感。聊到最後,我又酸又澀地回了他一句「《1917》保證難看」。當然,俗諺說得好:「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我們千萬不要因為表相、因為廣告,而忽視了值得欣賞的作品。
今年年初在海外旅行時,恰好有機會看到《1917》的半夜優先場,還自己一人獨享高級影廳的設備,看完只覺得激動萬分,「一鏡」的炫技成分雖然是有的,但除了場面調度技巧超群卓越,創作團隊對於戲劇起伏的掌握,更是贏得我心的奧妙所在。
打開電腦,悻悻然卻也施施然,給網友回覆了一句:「好吧我錯了,《1917》深得我心,有機會快去看!」

「一鏡到底」的迷思
「一鏡到底」是這幾年很受年輕電影愛好者追捧的攝製技術。長鏡頭的運用在以往大師經典作品裡雖然不難得見,數位時代的觀眾對於這類調度華麗、視覺語言繽紛奪目的敘事「元素」,也有其自成一格的鑑賞標準。
更有報導指出,導演山姆曼德斯由家中晚輩喜愛的電腦遊戲得到靈感,決意用「一鏡到底」的視覺效果,來經營「一氣呵成」的緊張感,以求使觀眾盡享身歷其境的全方位感受。
如果說電影是靠一個又一個「鏡頭」組織起來的敘事藝術,在某種程度上,每個鏡頭就好比是一篇文章裡一個又一個的句子。有的句子長,有的句子短,句子與句子之間的連接要靠標點符號,而鏡頭和鏡頭之間的連接方式、對比差異,也彷彿標點符號一般,在我們隨著這篇敘事,走上高低起伏的旅程時,因為長句短句,因為標點符號,形成不一樣的節奏律動。
我喜歡把一個很長很長的鏡頭,比喻成一個很長很長的句子。或許有理論專家不同意這樣的說法,但至少這是我欣賞作品、感受敘事起伏律動,以及自己進行創作時的標準依據。
在一個很長很長的句子裡,敘事者的邏輯要很清楚,孰主孰從、動作是什麼、時間和地點是什麼、因果關係是什麼,還有怎麼形容、如何修飾,層層次次,結構起來便有一種引人入勝的張力。怕的是言不及義卻又長篇大論,贅字過多形成冗句、話瘤,為長而長,徒然浪費篇幅、浪費閱讀這篇故事的人的時間。
長鏡頭最忌「為長而長」
這幾年來,有些刻意標榜超長鏡頭的作品,其中有不少都落入這種「為長而長、浪費篇幅」的炫技窠臼。尤其我們肉眼從凝視左邊的A物,快速轉移到凝視右邊的B物時,中間的過程是一閃而逝的。這種刻意標榜長鏡頭的電影作品,卻往往強迫觀眾「看到」原本應該一閃而逝的中間過程。
如果這些「中間」的段落有其敘事上的意義或者藝術上的美感,倒也還好,但許多時候這些「中間段落」只是為了延續「一鏡」而刻意拉出的贅字篇章;或者,就像很多影迷喜歡找的「剪接點」——是為了隱藏長鏡頭和長鏡頭之間的連接點,以便達成「看起來像一鏡到底」的完整效果(這次《1917》也是以這種方式剪輯而成的)。
以奧斯卡獲獎的《鳥人》為例好了,《鳥人》為求「一鏡」的效果,中間安插相當多主角穿過黑暗長廊、走入黑暗樓梯的空鏡頭畫面,這些空鏡頭畫面把原本已嫌喋喋不休的冗句長篇,又拖拉得更加漫長無節。人物的進場退場、戲劇的起承轉合,如果只是強迫中獎似的手搖攝影,真的會讓人完全失去耐心,看得不知所云,煩不勝煩。

一氣呵成的藝術
當長則長,當斷則斷,這應該是投身敘事藝術的創作者心中自然存在的標準。時時刻刻,每當在做藝術抉擇的時候,這個標準應該會自然浮現,自成依據。除非,「一鏡到底」成為命題作文的中心德目,那我們——包括創作者和閱聽人——似乎更應該去思考「一鏡」背後的實際目的:追求「一氣呵成」的效果。
過去幾天,愈來愈多朋友欣賞了《1917》,大家也再度聊開了話題——除了前文提過的「電玩」之外,大家不約而同說到影片本身透露出的強烈「劇場」感,一種獨特且清晰的「戲感」(theatricality)。
常常跟那些特別著迷「一鏡到底」電影的好友開玩笑說:「那麼喜歡『一鏡到底』,那應該來舞台劇啊!」如果我們把舞台鏡框視為電影景框,舞台上呈現的所有東西視為觀眾視線所及的電影畫面,舞台劇的一「場」(scene)幾乎就可以視為電影裡的一顆長鏡頭。
舞台的多焦點特色,同樣可以運用到電影上;劇場裡運用燈光和場面調度營造出近似「特寫」、「溶接」的視覺效果;或者以布景變換、演員流動的技法調理出場上不暗但「移步換景」的劇場魔術,是過去近一個世紀在世界舞台上,尤其在商業劇場裡,多少技術人員、設計師、編舞家和導演等等,努力耕耘的目標。
這門藝術,同樣可以在「一鏡到底」的電影裡,經營出「一氣呵成」的戲劇張力。
每一次鏡頭的移動,都揭露出新的戲劇元素,或者是人物,或者是背景,或者是裝飾,或者是戲劇重心。這些訊息有輕有重,強弱不一,觀眾視覺焦點停留在它們身上的時間長短也不一,於是,視覺上的訊息,加上台詞和演員的表情、肢體,加上音效、音樂,點點滴滴,交織然後結構起一整場不斷流動的戲劇,這就是《1917》深深吸引我的極大魔力。
分分秒秒、時時刻刻,它都在說故事。沒有浪費掉的「中間」空鏡頭,沒有刻意的漆黑走廊。就算要隱藏「剪接點」,也都經過巧妙設計,讓這些遮避畫面的黑暗斷點,成為戲劇的一部份。
觀眾被戲劇張力繃緊、帶著走,但與此同時我們並不像「電玩」一樣,變身成為奮勇抗敵、使命必達的主要角色,這部電影更多時候讓我們保持一定的審美距離,「觀看」這場殺戮戰場上的人性戲劇。

內斂而自制之美
《1917》於農曆春節假期之後在台灣上映,趕了個早,到IMAX影廳再看一次。這次放下「看技術」的高姿態,讓自己被吸入故事裡的那個世界。它以一個黑畫面,像傳統舞台劇一樣,把戲劇分割成上下半場。英國人特有的內斂和自制,壓住所有可能潰堤的外顯情緒,莊重自持地一路拉到旅程終點。
故事的開端是如此輕鬆、簡單,就只是偷得片刻休息的兩名戰友,接得任務後一路前行,穿過無人區時的緊張、慘淡,行經農場時見到被砍倒的櫻樹、屋簷下的奶桶、房門口的髒娃娃,緊接著是意外來襲,情緒緊繃卻滴淚未落,然後將承諾化為執著。
夜裡,燃燒的照明彈照亮如地獄般的孽火空城,這是即將影史留名的最佳攝影得獎專場!地底藏身的村姑、女嬰,也為全片帶來難以名狀的調和,更有甚者,讓我們親眼目睹主角與「家庭」告別的場面。
急流和瀑布幾乎淹沒主角的求生意志,逝去的英靈則化為水面落花,滴滴溜溜,將之輕輕托起,促使他爬過堆疊成堤的屍身,在林中終於發出全片唯一一次的乾嚎。從這裡,到他側向橫衝過火線的段落,不僅是全片最高潮,更是捨身止戰、悲憫大愛的具象展現。
導演山姆曼德斯精心調理的「一氣呵成」藝術,在全片結尾也同樣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兩人握手,隨即我們見到遠方一棵樹入鏡,於公於私,任務都告完成,樹的亮相,直接預告了「旅程終點」的來臨。
尤其,故事起於樹下小憩,也收在樹下小憩,飽滿的情感,還是那麼內斂且自制,兩張照片,一個眼神,一行字,一個吻。
一顆(好吧,兩顆)長鏡頭,一部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