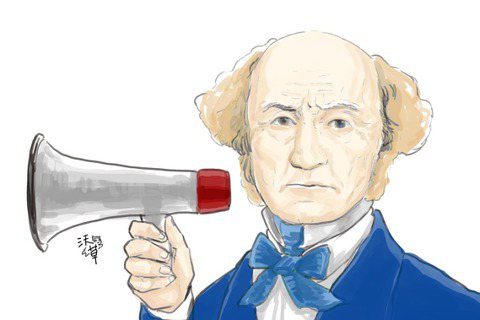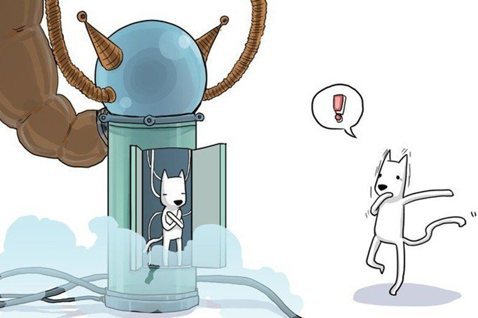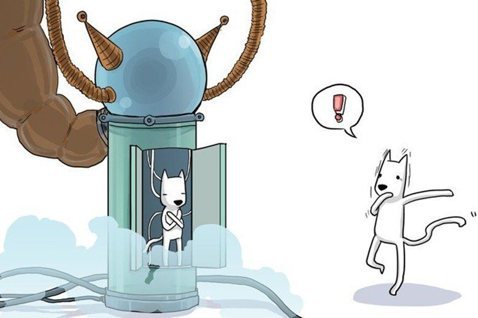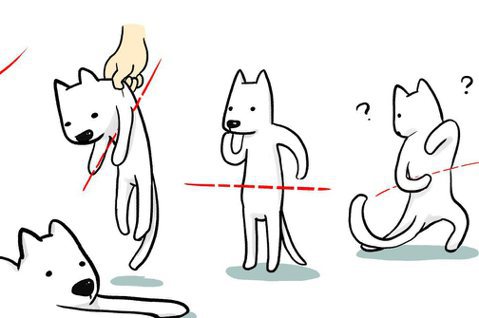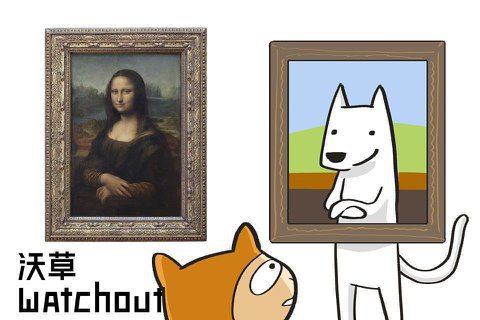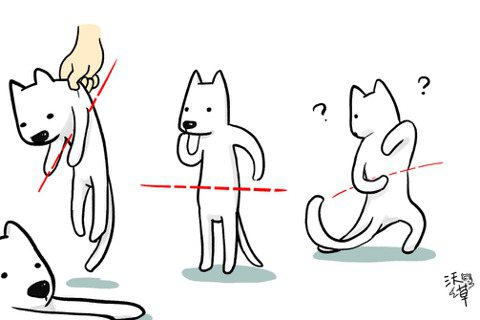劉維人/「二二八屠殺未曾發生」?假訊息與仇恨言論該受保障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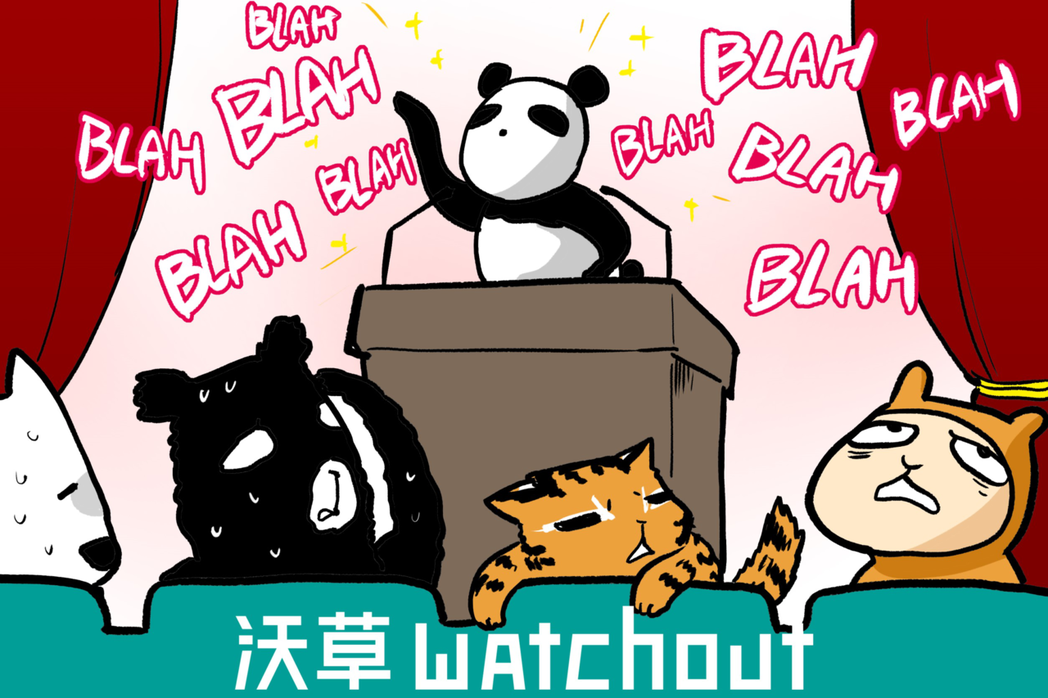
民主國家幾乎都守護言論自由,但言論自由保障的範圍和方法卻一直有爭議。假訊息和仇恨性、傷害性言論到底受不受言論自由保障?這些老問題在網路時代更加急迫和劇烈。
我們應該都聽過有人聲稱「二二八屠殺從未發生」,是捏造出來的,或者當時國民黨政府並未下令屠殺。這種「屠殺否定論」各國都有,例如歐美就有不少人否定納粹大屠殺。德國、奧地利、匈牙利等國都立法禁止這種言論,同時也禁止仇恨言論。某些國家甚至更進一步,立法禁止那些承認種族滅絕,但為其找理由辯護的言論。
許多人批評這種法律侵犯言論自由,批評者中甚至包括辛格(Peter Singer)、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等著名哲學家,而最常聽到的批評方式就是彌爾(J. S. Mill)的論證。彌爾認為人類容易集體犯錯,不僅犯過很多次道德錯誤(例如各種歧視),也集體犯過很多次知識錯誤(例如地心說),為了預防這些悲劇,我們必須讓每一種言論都有權存在,能夠彼此討論。而且如果沒有討論,即使我們目前知道的是真相,也會逐漸淪為教條。
彌爾的這種說法很有道理,但似乎還是有哪裡怪怪的?
言論會造成哪些傷害?
因為這類言論和錯誤的醫療資訊、詐欺性的投資說詞、以及COVID-19疫情或疫苗的假訊息一樣,都會在當下造成傷害。
錯誤的醫療資訊會讓人錯過黃金就醫時機,甚至在發生悲劇之後誤解醫護人員而胡亂提告。仇恨言論則會影響人們的社群認同和政治判斷、讓不同群體進入平行世界,難以彼此理解與尊重。有時候這些言論還會讓人相信那種禁不起檢驗、素樸的唯權力論,以為歷史完全是由勝利者書寫,何為正義也是由有權勢的人決定,各種議題都只是利益團體之間的鬥爭,可以完全用對誰有利、對誰有害來解讀,所以真假一點也不重要。
當然,這些傷害都不會永遠存續,人們可能會在未來學到教訓。
但要花多久?學到教訓的機率有多高?學到教訓的人跟犯下錯誤的人是同一群人嗎?如果不是,我們可以為了使子孫學到教訓而讓當下的鄰人受傷嗎?甚至可以為了讓未來的鄰人學到教訓而讓當下的鄰人受傷嗎?
總之,為了保留犯錯的權利而放任眼前可預見的錯誤,在道德上是負責任的嗎?如果是,它是對誰負責呢?
我認為這些問題在思考仇恨言論與假訊息時非常重要。
首先我們暫時回到彌爾。彌爾守護的言論自由,是否真的強烈到允許人們用言論彼此實質傷害,甚至用言論分裂族群與國家,可能需要再討論。事實上,彌爾沒有說行動可以像言論一樣完全自由不受拘束,甚至還在《論自由》中直接列出這項但書。他認為那些足以煽動惡行的言論需要被懲罰,例如在報紙上聲稱糧食商人害窮人餓死是一件事;去跟一群圍住糧食商人住家的暴民說同樣的話卻是另一件事。所有不具正當理由而傷害他人的行為都該被干預,無論干預的方式會不會讓你覺得不舒服。
此外,彌爾似乎並不認為言論對情緒上的負面影響真的能造成傷害,而這可能影響他判斷報章雜誌上的言論可以完全自由流通。當代已經陸續證實語言對心理、社會、政治都有許多實質影響力,如果彌爾讀到這些研究結果,還會認為我們應該保障仇恨性言論與傷害性言論,在公共場域和其他言論擁有同樣的露出度與影響力嗎?
還是他可能會認為,我們不應該消滅任何假訊息和仇恨言論,但很多時候還是得限制這些言論,以免它們立即造成傷害,或讓討論無法進行,或讓人們仇視那些意見相反的人,根本不願意與對方繼續討論下去?當代的彌爾會不會認為,當某些假訊息和仇恨言論破壞了言論自由的目的或賴以存在的先決條件,就不能完全自由地散播,以免有人用這些言論來操弄人民?他會不會認為也許這些言論不能下廣告,或者在社群網站上出現時必須調降觸及率?
但這種想法顯然還是會讓人不太舒服,尤其當我們將言論看成言論市場時,「干預市場」的想法更是讓人聯想起各種干預造成的扭曲。但干預1真的值得禁止嗎?有幾個理由可能值得我們重新思考:
干預言論的四個理由
1. 言論市場的現狀就是各種干預的結果
反對一切干預的自由市場派,往往忽視或不面對「理想上的自由市場從未存在」這件事。無論是經濟市場還是言論市場,都是各種強制力與硬實力形塑的結果。以言論市場為例,各方言論所買的廣告、雇用的公關公司與說客,都是因為保障私有財產權以及相關法律以某些方式撰寫才得以存在。我們對各種言論的接受程度,明顯受到學校教材的影響。當代的同溫層現象,則主要受到社群媒體撰寫的演算法所決定。
如果我們應該禁止干預,我們可能就也得處理那些目前影響力甚大的干預,例如學校和社群媒體。這顯然不太實際。
2. 自由放任市場加劇機會不平等,造成道德問題
反干預論者假定資訊流通時沒有摩擦力,無視「每個人當下的選擇能力與判斷力並不相同」這件事。然而,在現實世界中,人們的判斷力與資訊環境嚴重受運氣影響,而且大幅不平等。決定你是否知道哪則資訊最可信的主因,經常不是你有多努力查資料,而是你智力有多高、出身在哪個家庭、受哪些教育、平常跟誰交往、做什麼工作。這些都跟你的資本有關,資本越多的人判斷越有利,資訊環境與教育資源不佳的人更容易聽信假訊息,亂吃藥結果搞壞身體,甚至可能因此亂告醫護人員。
仇恨言論這時候造成的問題更大。很多相信仇恨言論的人,都完全不信任持相反立場的人,甚至直接不信任其他族群。他們會反對在道德上正當、但有利於其他族群的政策,甚至會支持直接傷害其他族群的政策(即使不說二二八,也可以想想同志爭議)。仇恨適合用來凝聚群體內共識,政治人物或利益團體經常會來聚集選票,導致社會更常撕裂。
也就是說,仇恨言論以及某些假訊息,會讓資源越少的人,越容易在自己難以改變的狀態下集體做出道德上嚴重錯誤的行為,也使有心人士越容易操弄他們。這是一種社會上的嚴重道德危機,以台灣的狀態來說,有時候甚至會被中共利用來傷害國家安全。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在讓各種言論自由討論的情況下防止這類危機(目前有很多都沒有辦法防止),這類言論可能就需要干預。
3. 金權與監控資本主義的影響力
當代有權勢的人影響言論市場的能力很高,他們可以買廣告、可以聘公關公司帶風向、可以讓政治人物或評論者以對業主有利的方式討論影響公共議題。如今的網路巨頭甚至可以直接刪除我們的發言、讓某些爭議報導無法露出、甚至藉此在選戰中影響候選人的支持度。這項機制和上一項聯動時,會加劇社會的集體道德危機,讓沒有資源、教育程度較差、或工作太忙沒有餘裕參與討論閱讀資訊的人更容易被操弄。
自由市場很難阻止這類影響力,而且通常還讓它們更強大。想要抗衡這樣的影響力,勢必得用其他方式干預。
4. 如果在傷害之後很久才能學到教訓,放任人們彼此傷害可能就會有道德問題
就如本文之前所言,人類在受傷後通常會學到教訓,但在集體犯錯的狀況中,通常都是我們年輕時受傷,老了以後才學到教訓;或者我們一輩子都學不到,而是由我們的子孫學到教訓。有些時候甚至更糟,利益團體會把我們的集體錯誤怪在其他事情的頭上,造成連續數代無法彌合的傷痕。
這時候因為受傷的人和學到教訓的人不同,從錯誤中學習是否「值得」就變得很麻煩,在道德上是否正當則更麻煩。我們似乎不太能為了讓未來的人類更有智慧、更加和諧,就在你不知情的狀態下放任你受到傷害並傷害別人。即使是為了讓你在老了之後學到教訓,應該也幾乎沒有人會買單。
而且現在的人因為仇恨言論而彼此分裂,互相傷害之後,未來是否能學到教訓和諧共處,真的沒有那麼肯定。看看轉型正義有多難做,族群仇恨有多難解,我們會對此更加保守。
以上幾點應該足以讓我們為了抗衡某些傷害,而允許某些時刻干預言論市場。但無論如何,即使只是改變言論的露出度,也會影響人民自主發聲,以及自己做出決定的能力。這部分又該怎麼辦?
仇恨言論的特別之處
根據楊劭楷的這篇簡介,德沃金(Ronald Dworkin)給了一個禁止干預的好理由:如果你壓制甚至禁止我發表言論,即使事實上你是對的,也會讓我無法表達自己的意見,更難了解我到底錯在哪裡,而且顯然更難獲得我的同意。這種無視人民同意或繞過人民同意的施政不具備正當性,實際上也會引發各種政治問題。
但仔細看看就會知道,這項理由要保障的重點並非言論本身,而是以發表言論的方式參與討論、讓他人了解自己的狀況理由與感受、以及接近真理、尋求共識的討論過程;同時,這項理由也是要保障那些願意彼此理解跟彼此尊重的人,而非用言論壓制別人表達意見,或者操弄他人的人。
但言論的意圖與效果有很多種。並不是每一句言論都是想要與其他人一起討論,也不是每一句言論都有助於討論進行。有些言論甚至已經嚴重不尊重他人、不平等對待其他討論者。
仇恨言論就是這類言論的典型,它讓各方陷入激情,難以彼此同理,甚至因為失去信任而開始曲解彼此的意見,同時也會讓具備操弄能力的人,擁有不成比例的話與影響力。既然民主政治需要盡量讓政治決定獲得每個人民的同意,那麼那些操弄他人心理的仇恨言論,讓人更難知道自己到底「同意」什麼、「相信」什麼,也更難讓人自己決定什麼是正義,可能就傷害了政治正當性,同時也會因為激發分裂,而讓人民更難形成集體決定。
當然,無論是德沃金還是彌爾的論證,都指出必須讓每個人都能表達自己的意見。只是「應該讓每個人都能發聲」、「應該讓每種意見都能討論」既不能推導出「應該讓每種意見在每種狀態下都擁有相同的擴散能力」,也不能推導出「應該以相同的效力去保障同一類意見的每一種討論方式」。
如今假訊息、言論操弄、仇恨言論造成傷害的主因,都是言論與受眾所處的環境,以及討論的方式。不過因為篇幅的關係,本文無法繼續著墨哪些討論方式可能值得干預,只能簡略地說,那些妨礙釐清真相、不尊重他人、讓人更難理解其他發言者的討論方式,是需要阻止,甚至需要禁止的。許多公共討論版的「版規」也都是根據這些準則而制定。
重要的不是真假,而是效果
請注意,以上兩大類的判準,都與言論內容本身的真假值無關。一串內容為假,但努力提出理由說服他人,認真回應質疑,而且平等尊重其他討論者的言論似乎通常不該干預(有例外,見下文),因為它會讓其他人更了解發言者搞錯的理由,很多時候甚至會顯露出發言者所處的真實困境;而且發言者在討論過程中會逐漸轉而相信真的東西。
相反地,一串內容為真,但不斷傷害討論過程的言論,許多時候卻需要被噤聲。現實中就有許多憑恃客觀真實不斷攻擊別人,用各種無法理解的理由拒絕公開資訊、認為只有自己的專業才是專業的言論。我們都相當了解這種言論把討論過程搞得多慘。
這種「保障討論品質與討論意願」的判准,也許就能跳脫在充分討論前無法得知命題真假的問題,同時可能也既能使每個人發表個人意見,又不會讓言論市場陷入無視真假、無視彼此尊重的反智狀態。
最後我們還可以額外討論一個問題:為什麼在某些公認的「緊急狀態」下,絕大多數人直覺上都會允許某種言論管制?例如絕大多數的台灣人從COVID-19開始傳播以來,可能都會願意讓政府與社會大眾去壓制關於疫情的假訊息。大部分的人也都會同意在飛機上禁止大喊「有炸彈」、「劫機」這類話語(至於要怎麼處罰就有歧見)。這類傾向究竟是怎麼來的?只是遠古遺留至今的保守威權心理傾向,還是可能有別的原因?
我個人的猜想是,社會願意接受的言論自由度,跟言論造成的衝擊風險有關。那些人們可以接受管制的狀況,幾乎都會在很短的時間框架下造成大量傷害,而且是該群體無法處理所造成傷害的言論。例如疫情萬一散播開來,台灣社會就勢必遭受經濟與生活方式上的衝擊,飛機一旦因為炸彈戲言而返航,造成的損失也無法從開玩笑的人身上求取。
相對的,那些大部分人都認為要保障言論自由的狀況,提出異議的少數派都沒有訴求當下的巨大改變,留給社會的時間框架很長,足以讓眾人在討論與體驗中處理;再不然就像是環保、人權、國安、資安的爭議那樣,少數派所要改變的對象,比少數派的改變方式更可能造成當下衝擊,例如讓二氧化碳排放量超過臨界點、使關鍵物種消失、使國家的經濟或資訊安全出現重大漏洞、使同志因心理壓迫加劇而自殘等等。
如果這個猜想屬實,那麼也許社會一直都有在用成員願意因為言論而承受多高的風險,來判斷要不要容忍某些言論。我們某一部分的直覺,也許比我們以為的更有智慧。
- 「干預」通常都僅指政府的行動。但基於當代的大型企業對公領域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甚至成長為監控資本主義;以及社會中許多機能都需要公私部門合作,本文將「干預」的意義擴張至各種限制或改變自由市場的行動,其中可能包含人民自主發動的社會制裁。也就是說,本文主張個人與團體在面對社會「圍剿」的時候,有時候不能以言論自由當擋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