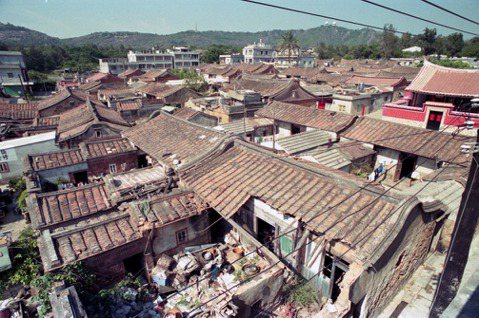從「失語」到「喧賓奪主」:白浪,現在輪到你們聽我們說

2015年,《鐵獅玉玲瓏2》的預告片中,將《賽德克巴萊》中的對話,以台語諧音的方式,將莫那魯道的名字,KUSO成為「摸蛤兼洗褲」,接著隨便亂咕噥起一段話,字幕則打上「某種母語」;而意指「真正的人」的 “Seediaq bale” 變成了「屎就放肚內」,在賽德克文化內具重要意義的bale觀,變成肚子裡一坨屎。
到了2016年,《大尾鱸鰻2》抗議核廢料的達悟族人同樣講了一些觀眾聽不懂、也不是達悟語的「胡言亂語」,漢人對著族人說「肖仔!」便轉身走掉。
我聽不懂你的語言,你就是「肖仔」?
今年民進黨議員王孝為在臺北市議會要求原民會主委陳秀惠就使用族語備詢致歉,他認為議員說中文,陳秀惠就應該用中文回應,「你沒有說你要用阿美語,你忽然間爆出這幾句話,我也聽不懂啊!」最後,陳秀惠九十度彎腰道歉。
無獨有偶——英語「野蠻人」 這個字的來由也和語言與關。“barbarian” 來自希臘語,用來指涉埃及人、波斯人、印度人、賽爾提克人等等這些「胡言亂語的人」(barbarian),因為在古希臘人的耳裡,這些不是說希臘語的人們就是在「胡說」,他們聽起來,這些人只會發出巴拉巴拉巴拉(bar bar bar)的聲音,所以叫他們「巴拉巴拉的人」(barbar+an)。
「失語症候群」描述了在文化心理上,對於失去言說能力的「閹割焦慮」。「閹割焦慮」是佛洛伊德所創造的術語,指男性對陽具被閹割的擔憂,到了後結構主義和女性主義的文化理論中,指的是「對於某種父權文化中心地位喪失的不安。」在國家的脈絡中,「失語症」則是「漢語的強勢力量遭到西方語言衝擊時候的反應」。而不論是英語的「野蠻人」,亦或原民會主委道歉事件,都展現出此種因聽不懂其他族群語言焦慮。
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將單一語言視為凝聚國家共同社群的重要管道,這個有限的想像共同體,透過想像將一輩子可能都不會有機會互動的彼端人們,連結在一起,成為一個整體。
那麼誰來決定什麼語言可以拿來連結你我?——統治階級。
面對原住民族近年來引用「語言權利」的基本人權概念,以及原住民族權利運動的日益壯大,某些漢人開始罹患了「失語症候群」。因為多元而異質的語言,威脅了漢人長久以來位處此想像共同體核心且不可動搖的重要地位,遂而產生了「閹割焦慮」——你怎麼可以說一些我聽不懂的話——接著搬出各種道理試圖證明「相互理解」才是語言的本意。
遇上「為什麼不是漢人去理解原住民族語」的質疑時,再搬出中華民國的通用語言為「國語」(Mandarin)回應,不過在沒有任何法律基礎規範何為官方語言/國家語言/通用語言的狀況下,最後乾脆說使用「國語」是默認許可的。總之,漢人是文明的,漢人要求原住民族使用漢語,有千百萬種經得起考驗的理由,並且這不是歧視。

我們教會了你們說話,你們不要抵抗我們
莎士比亞的傳奇劇作品《暴風雨》(The Tempest),有一場普洛士帕羅與卡力班之間的對話,卡力班是一個島上的原住民,他敞開心胸幫助了落難的米蘭公爵普洛士帕囉。這一段橋段完整地詮釋了被殖民者,如何反過來使用殖民者教授的語言顛覆殖民者:殖民者的語言,對於被殖民者的唯一好處是——教會了被殖民者如何詛咒殖民者。
普洛士帕羅:可恨的奴才,你心裡,『善良』留不下半點痕跡;壞事兒樣樣會!我看你可憐,費了神教你說話,不斷地教你這樣,又教你那樣。野蠻人,那時你連自己說些什麼都不懂得,只會像一頭畜生般嘰咕叫喊;我教你怎樣用語言去表達心裡的意思。你學是學了,可是下流種,怎樣學也本性難改;美德的種子,休想落進你心田;把你關進在石洞裡那也是應當──其實關禁你還算是寬容了你。
卡力班:你教給我語言,我得到的好處就是懂得了怎麼樣詛咒。紅瘟病毒死你──你教我說你們那種話!1
520就職大典,站在蔡英文一旁是歌手巴奈,她還是領唱《美麗島》的歌手之一,手中舉著反核旗。參加「誰的總統就職」典禮,一向政治,搞得不好會被中國封殺。巴奈的到場,應該十足顯現了她對蔡英文政府有所期待,如同她昨天受訪所說。
而8月1日蔡英文總統向原住民族道歉,歌手巴奈也在總統府之外,只是當日她不再站在總統身邊,而事怒罵蔡英文政府處理「不當黨產」卻不處理「不當國產」,此舉是「只圖自己的利益,丟臉!」
巴奈的批評,惹來一片罵聲。有人說:「巴奈不配被稱原住民,是番仔。」有人說:「原住民不要得寸進尺。」有人說:「我們繳的稅金 可以養活多少原住民 知道嗎?」
巴奈罵了蔡英文政府的道歉形式,網友輿論抨擊她是「無知原住民」,質疑原住民族團體為何不去罵真正的欺壓者國民黨政府,還反而「把選票都投給壓榨他們的國民黨」,如此一來,馬英九對原住民說「我把你當人看」,是咎由自取。——呀,果真是本性難改。我們給你們資源、我們留你們特權、我們教你們說話,結果美德的種子(不要投給國民黨)始終落不進你們的心田裡。現在我要把我們賜你們的封號——「原住民」——拿回來。
不過,很抱歉,「國語」早不是漢人的語言,漢人不再能對「原住民」三個字應該怎麼被定義說三道四。現在,他們要用國語「為他所有遭噤聲且蒙受羞辱的先祖們狠狠地重重一擊」2。


「第三語言」將重啟與殖民者的談判?
ina常常在這邊呼喊我的名字叫我去那邊的雜貨店跟Pilaw買一包檳榔一條沒有禮貌的山路開過我家大門它跟我一樣有座號它是11號 我是9號
去年,Kacaw的狗來找我玩時被撞死在路上ina說:「只是小狗沒關係,還好不是人。」從此以後,四鄰的路口多了一根凹凹凸凸的鏡子—對著Pilaw的檳榔攤照我們以為是Pilaw愛照鏡子還躲起來偷偷笑她 但其實我們小孩子才會一直跑到鏡子前面看我們的臉變形變大變得很好笑ina說以前才沒有這條馬路整個部落都是連在一起 可以跑來跑去我們的路走在沙灘上阿公沿著沙灘到水璉去傳教海浪會記得他的腳印 不會把他淹沒現在山路載來了好多都市的人也載走我們的檳榔、魩仔魚海灘就漸漸消失浮了好多肉粽上來我跟Kacaw都會爬在上面玩躲貓貓還可以抓Kalang我們的路走進了山裡沿著路穿過兩座山就會來到我家門口路的另一邊有雜貨店和教堂很多老人到現在還以為是從前過馬路就像在散步車子就會搖下車窗來罵人說我們馬拉桑了啦但是阿公才不會穿西裝把導係他是要去那—邊的教堂馬路沒有很寬只是車很快所以我們都要排隊見上帝
——黃岡,〈是誰把部落切成兩半?〉
黃岡這首詩獲得了第八屆「林榮三文學奬」新詩首獎,詩中使用了許多阿美族語詞彙,有些以羅馬文字呈現、有些則以漢字呈現,不懂阿美語的讀者或許難以馬上揣摩其意,這首詩講述原住民族土地如何遭到「外來者」的撕裂與侵害。
使用著「外來者」的語言——近些年來,原住民詩人使用漢語做詩不失為一種控訴的方式。黃岡的詩中雜揉著阿美族語呈現的「文化混種」——事實上,正顯示了潛藏於殖民關係中的顛覆性。後殖民學者Homi Bhabha認為:「混種介入威權的操控」……「混雜策略或混雜論述開啟的談判空間,其中的權力是不平等的……但這類談判既不是同化也不是合作。」
正是在兩種文化的夾縫間,所生成的「第三語言」,重新解讀了來自於兩種文化的符號與意義——好像是國語又不是國語、好像是族語又不是族語。
當中華民國代表蔡英文與原住民族代表達悟族長老夏本.嘎那恩站在台上,由蔡英文發表道歉演說時,夏本.嘎那恩像是罰站般站在一旁;而輪到夏本.嘎那恩以達悟語發表演說時,就換成蔡英文尷尬地站在那,一個字也聽不懂地尷尬微笑。而夏本.嘎那恩躬身,雖然蔡英文不知道鞠躬的意思為何,但反正也跟著躬身。
翻譯是可能的嗎?
這場道歉演講上,達悟語的翻譯像是柔水,慢慢地、溫和地,將長老富有情緒的達悟語翻譯成冷靜的漢語,對於不懂達悟語的人們,一邊著急她翻譯得慢、一邊又懷疑她到底是不是翻得傳神而精準。
長老與翻譯間不言而明的默契,像是透過遊走在達悟語與漢語之間,展現原住民族對於漢族中心霸權的顛覆性。雖然語言之間必定無法全然對譯,但就是在那個無法對譯的空間中,產生了文化與文化間的「裂隙」,而這個裂隙正是Homi Bhabha所講的足以顛覆殖民權利的「潛在談判的空間」3。
也許整件事情對於原住民族並非如此樂觀地具有顛覆性,但當談判空間得到剪綵式的引人注目,主流群體的失語症候群將被誘導而發作,湧上手邊網路設施留言轟炸原住民,「閹割焦慮」既然產生了,必然須要被解決與滿足,話題開啟了的這個時候才是戰場的開始。
唔,達悟族人從《大尾鱸鰻2》中走出來了,一樣講著聽不懂的語言,現在站在總統府裡,你還有自信能說了一聲「肖仔」,就走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