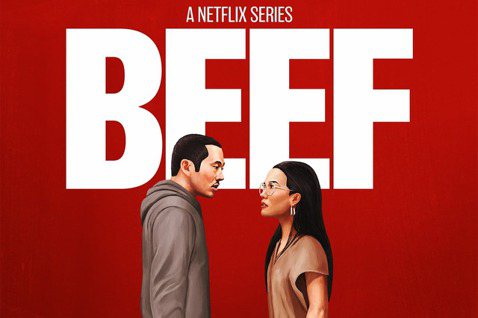諾蘭電影的前衛與古典——讀《諾蘭變奏曲》

英國導演克里斯多福・諾蘭(Christopher Nolan)或許是這一代少數作品能叫好又叫座的作者型導演(Auteur Director),被譽為「諾蘭電影聖經」的專書《諾蘭變奏曲》出版,我花了一週時間閱讀,同時搭配著諾蘭的電影相互對照,在影評人Tom Shone的訪談梳理中,他談及導演的成長經歷、創作啟蒙、豐富的文本參考,包含文學、繪畫與電影,以及種種與觀眾、與團隊、與自己的相互溝通。
極簡和極限的對話
時間,是諾蘭電影一直讓我相當著迷的重要存在,也是諾蘭總能巧妙運用的概念,在時間的玄虛中玩弄華麗戲法,但本質上背後支撐的從來都是再簡單不過的人性。「用極簡主義模式創作的極限主義」,書中這樣形容《星際效應》(Interstellar, 2014)給予我們一個清晰的理解。事實上,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極簡和極限的交融。
當我們想起諾蘭,浮現的可能都是近幾年的大作,於是便輕易和「大規模」、「大製作」劃上等號,但若我們回看最早期格局較小的《跟蹤》(Following, 1998)或《記憶拼圖》(Memento, 2000),一直到《針鋒相對》(Insomnia, 2002)才第一次和艾爾・帕西諾(Al Pacino)、羅賓・威廉斯(Robin Williams)等一眾好萊塢大明星合作,縱使早期創作規模比不上成名後的大成本製作,作品裡清晰可見的生猛和純粹,絲毫不會輸給後面所謂的「鉅作」。
諾蘭說,《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 1968)是「第一部展現電影可以成為任何樣貌的片子」,相同地,他的電影其實同樣遊走於藝術和商業類型的模糊邊界,其中格局大小的轉換也每每拓寬戲院體驗。
例如《黑暗騎士》三部曲(The Dark Knight Trilogy, 2005-2012)仍是我至今認為最棒的超級英雄電影,《敦克爾克大行動》(Dunkirk, 2017)的簡約則跳脫我們一如既往對戰爭片的期望,《星際效應》是前衛科幻與極致古典的集大成,而《全面啟動》(Inception, 2010)和《天能》(Tenet, 2020)劇本線的複雜精細,一再又一再挑戰觀眾對電影的理解。


作品從何而來:英美異文化的成長背景
對我來說,此書令人想反覆咀嚼的特點在於,它讓我們看見作品從何而來,創作者又怎麼樣與之抗衡,與之對話,與之共存。
作者多次談到諾蘭的雙重國籍,衍生出他對「家」的複合認同——在英國傳統公學校如軍旅般的嚴格生活,給予他重重限制,卻也轉變成養分;在倫敦大學學院(UCL)與背景紛雜的同儕互動中豐富生活體驗,在社團裡學習硬知識,或是在這座本身就是大型博物館、美術館和圖書館的倫敦城裡,與歷史、繪畫和文學相互碰撞,進而在作品中展現許多維多利亞時代的蹤跡。
相對地,在海洋另一端的美國,任何事物都是如此巨大,大到當他再度回到狹仄的英倫時,都感覺自己又長大了。穿梭於英美異文化之間的成長歷程,那些不適與衝撞,都變成日後電影中的靈感,有的是一幕致敬場景,有的是對白,有的則是核心命題。

容忍劇情的未解,反而帶來更深層的理解
身為優秀的編劇,劇本寫作的「複雜性」可能更常被觀眾注意到,如《全面啟動》多度空間的時間軸該怎麼理清頭緒,如《天能》裡的「熵」應當具備足夠的物理知識基礎。然而,這本書告訴我們,從不只是那些表面上的費解令人苦惱,而是又回到最純粹的人性面——要如何在《敦克爾克大行動》讓觀眾感受到窒息感?如何在《全面啟動》中讓觀眾在乎夢境?如何讓《星際效應》裡的時間牽動家庭羈絆,成為一種「距離」?
這或許也解釋了我每每在看完諾蘭電影後,讓我久思的不是那些非線性劇情線,而是故事裡的元素,例如《敦克爾克大行動》最後出現的報紙、《星際效應》中關鍵性的手錶、《頂尖對決》(The Prestige, 2006)裡觀眾看見魔術「被變回來」的表情,或《黑暗騎士》(The Dark Knight, 2008)宛如預言般的哥譚市社會,往往都使得諾蘭電影不只是冰冷和理性。
儘管如此,許多人仍嘗試在他的電影中解謎,人們對於「真相」的癡狂已經到了歎為觀止的程度,對於「曖昧」的容忍程度愈發降低,所以我們看見無限版本的《全面啟動》和《天能》解析,人們卻仍不滿足於此而一再辯論,或是台灣發行商將《記憶拼圖》剪成「按照時間排列的正常版」的荒唐故事云云。
電影中幻想和真實之間的交錯,往往才是最迷人的,正如《頂尖對決》早就告訴我們——「現在你正在尋找戲法的秘密,但你是找不到的,因為你其實並不想知道,你想要被騙。」魔術和電影是一樣的,我們信仰眼見為憑,不願被騙,但也享受被騙的過程,其實容忍劇情的未解,有時反而會帶來更深層的理解。


從觀眾到導演:在大銀幕上看見真實,創造幻象
記得諾蘭多年前的一次訪談讓我記憶至今,他談及自己對大銀幕的著迷,他說自己小時候會跟著家人去倫敦萊斯特廣場劇院(Leicester Square Theatre)看經典電影,也談到他對「真實」的偏好,例如《星際效應》從沒有使用任何綠幕特效,一切都是實景搭設,也呼應了本書中對「看電影」的精準形容——「不用頭盔的虛擬實境」。儘管諾蘭早已從獨立電影界躋身好萊塢名導,他所保有的古典依舊存在,並深深影響著他的作品。
雖然我此刻不在台灣,沒辦法親自感受這本書的重量和紙張質地,但我試圖走訪書中提到諾蘭在倫敦生活過的蹤跡,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一站我到了倫敦西區的布盧姆斯伯里劇院(Bloomsbury Theatre),這座劇院的地下室就是當年倫敦大學學院電影社的辦公室,而諾蘭則是彼時電影社的社長。數十年後的平日下午,街上幾乎無人,我推開大門,裡頭坐著兩位工作人員,可惜疫情關係,戲院的門仍舊緊鎖著。
他問了我「你想去戲院嗎?」
我點頭回應。
他先是皺起眉頭說「現在還沒開放。」……接著臉上露出一抹微笑「不過很快就會重開,我也很想念電影院,到時見!」同時雙手做出祈求好運(fingers crossed)的動作。
諾蘭電影中的「變奏」(variation),在於類型,在於劇本,在於時間,但變化萬千背後所本的樂章,仍然是對電影的熱愛,對戲院觀影的信仰,而《諾蘭變奏曲》這本書細緻托出這層面容——在走上得獎臺之前,在成為導演和編劇之前,在被大家認識之前,那位和無數人一同坐在戲院裡視野被打開的觀眾——他的電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