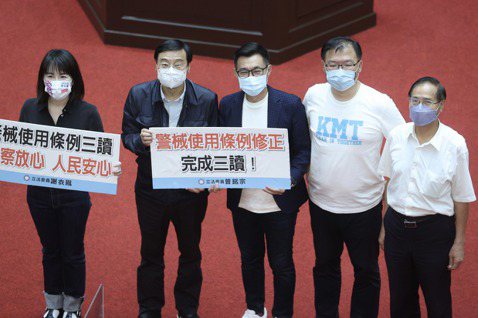律師抄個資遭檢察官當庭轉被告:偵查庭爭議的制度問題

日前有媒體以「檢察官好威 律師抄筆記遭斥責 幫被害人打官司當庭變被告」入標,報導一起士林地檢署偵查庭內檢察官與律師發生衝突的「違反個資法」案件。其後在司法實務圈內「炎上」,而在媒體與社群網路中論戰。士林地檢署則回應該事件於去年(2022年)12月在「檢律聯繫座談會」中經律師代表提出,目前該署正在「行政調查有無違法不當」,並「籲請各界避免臆測、推論,以免引發對立」。
據媒體報導,一位第一次開庭的新手律師擔任一起愛情詐欺案件的告訴代理人,因不諳偵查庭規矩,在蔡姓檢察官對於關係人(被告之配偶)進行人別訊問,偵查庭筆錄螢幕顯示該關係人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時,擅自將被告配偶電話號碼抄錄於自己的筆記紙上。
報載該律師的說法是「做為日後談和解時連絡用途」。然而檢察官當庭發現後立即喝止他抄錄其他關係人電話號碼,並當庭指控該律師違反個資法,除了當場查扣律師筆記,並詢問詐欺案關係人「是否要對律師提告」,在該關係人表示要提告後,又當庭將律師轉為「違反個資法」案件之被告。
對此,全國律師聯合會(下稱「全律會」)於今年1月1日發表聲明,尖銳地譴責檢察官的行為屬「不當訴追」、「粗暴行為」,並控訴檢方且妨害律師執行職務及不當限制律師合法權限,違反國際規範及憲法法庭判決意旨。
由基層檢察官組成的檢改團體「劍青檢改」則於1月3日發表意見截然相反之聲明,指出事件源由是擔任告訴代理人的律師在偵查庭未經檢察官許可,且未經被告同意,趁機偷偷抄下被告配偶個資和聯絡方式,當場遭查獲,「其行為嚴重違反律師倫理且有觸法之虞」,並強調律師行使「告訴代理人」與「辯護人」之職權有別,不應予以混淆。
檢改團體並指責全律會將辯護人之法定權限「滑坡挪給告訴代理律師享受」,進而讉責全國律師聯合會「混淆視聽,不思糾舉移送調查,反而公然包庇,律師倫理不斷沉淪」,呼籲全國律師聯合會「勿為一人毀全律」。
在筆者來看,以上看似爭鋒相對的聲明內容,實際上根本是各自站在本位出發的兩條歪斜線。

告訴代理人權限與檢察官偵查庭指揮權
關於律師於「偵查中」擔任「告訴代理人」,是否得於偵查庭中筆記的問題,於我國刑事訴訟法等「法律」位階並未有具體明文之規範。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所肯認的辯護律師在場「筆記權」係從辯護權中衍生而來1,因此該判決僅處理律師擔任「辯護人」時有筆記權,若不服檢察官之限制時,在《刑事訴訟法》修法前得準用《刑事訴訟法》第416條所定程序救濟;然而該憲法判決並未處理律師擔任「告訴人」時,是否有筆記權的問題。
至於在行政命令的法位階部分,法務部依檢察行政監督而發布之《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91點第1項後段規定:「告訴代理人不論為律師或非律師,於偵查中,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不得檢閱、抄錄或攝影卷宗、證物。」然而該規定僅禁止告訴代理人閱覽偵查中卷宗、證物等閱卷權,將告訴代理人律師與辯護人律師區別對待,區別之理由在於「偵查不公開原則」,因此縱然告訴代理人為律師,亦不得抄錄偵查中卷宗資料,但偵查庭中所參與或見聞的「偵查筆錄」是否得抄錄,從文義上來看並未有明確的禁止。
但從以上規定來看,律師擔任「告訴代理人」時,由於角色與職責與辯護人有所不同,本質上並不涉及辯護權,在偵查不公開、當事人隱私權保障等公益考量之下,權限亦與「辯護人」有所不同。
或許正是因為憲法法院判決、法律並未明言「告訴代理律師」的偵查中筆記權,因此全律會聲明的推論才無從引用具體法規,而是迂迴又長篇大論的引用聯合國原則等抽象規範,並有意無意混用「辯護人」職權之概念而套用到「告訴代理人」身分上,卻忽略了告訴代理人並不以律師資格為必要2,且偵查程序中,告訴代理人並「未」有如辯護人之在場權。
全律會忽視被告與其他關係人的權利保障與偵查不公開的公益,以及現行法規並未有明確規範,身為「在野法曹」應該敦促有關部門注意或立法的使命,反而片面主張告訴代理人無所節制的偵查中筆記權限,其論述也過於跳躍與狹隘。
若全律會要將偵查中在場權、筆記權等從辯護權推導而來的權限,「類推適用」到告訴代理人身上時,恐怕在法理上會面對很大的挑戰,也需要更進一步的詳細說理,而非在聲明中混用兩個不同的角色概念,從這點來看,「劍青檢改」聲明第二點的質疑,並非無據。

個資法解釋與檢方程序爭議
從被告或其他關係人的個人資料保障來看,以及「舉重明輕」之法理來看3,檢察官自得本於其偵查庭中的訴訟指揮權,禁止告訴代理人抄錄他人之電話等資訊;此外,依《個資法》第19條第2項之意旨,告訴代理律師在經檢察官制止後,自應刪除該關係人之資料。因此,如若本案檢察官發現告訴代理人律師所抄寫的內容為「關係人之電話號碼」等個資時,基於保障個人隱私權或偵查不公開等理由,當庭禁止告訴代理人筆記、或要求其立刻刪除,這樣的程序倒也不至於產生爭議。
問題在於,報載本案檢察官又更激進的當庭指控律師成立違反個資法的「犯罪行為」,並訊問關係人「是否提告」,其後又將律師當庭轉為被告。在這裡就會遇到我國立法技術「複雜」又充滿爭議的個資法解釋與適用問題。告訴代理人「取得」關係人個資的過程,源於檢察官未進行分別訊問,又將他造的個資顯示於筆錄系統螢幕上,使在庭之告訴代理人得以共見共聞,從而也產生檢察官於偵查庭指揮權限濫用或不當的問題。
首先,偵查程序與審判程序有所不同,並未要求公開審理(法律反而是要求不公開),在證據調查程序上亦未要求對質詰問,因此,偵查檢察官本就得以依照案件調查需求,決定分別、隔離訊問。其次,對於被告或證人等進行人別訊問時,重點在於調查其人別身分,並不需要讓所有在庭者共見共聞他人的個資。
因此,縱使告訴人與被告、其他關係人有同庭訊問需求,但在技術上仍可以分別進行人別訊問、或是使用「個人資料陳報單」的書面陳報、筆錄螢幕或檢察書類適度遮掩個資等方式處理。這些做法,並非筆者「憑空幻想」,而是實務上早已踐行已久、筆者過去從事檢察實務工作時曾經採取的做法,部分地檢署在送達傳票、或當事人報到時,特別說明如不欲同庭者得知個人資料,可以向檢察官陳報以個人資料陳報單的書面方式處理,並在檢察書類隱去除姓名以外的個人資料。
然而,本案偵查檢察官在偵查程序中,並未採取妥適的遮掩個資作法,使得告訴代理人得以知悉關係人的電話號碼。從這點來看,檢方對於個人資料的處理,不無值得檢討之處。此外,檢察官雖然在發現犯罪時有依法主動偵查的權限,但前提在於檢察官要先具有身為「法律守門員」(Gesetzeswächter)的使命感4,本於正確解釋法律的專業,進行妥適的程序,而非在一時意氣之下濫行發動偵查,浪費偵查資源。
誠然,告訴代理人在未經檢察官與關係人允許的情況下,貿然抄寫他人的個資,在他人權利保障與律師倫理上不無可議之處。然而,由於《個資法》第19條客觀構成要件複雜又不夠明確的立法技術問題(例如所謂的「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在實務上時常有爭議並引發詬病,而該條規定又因結合同法第41條有入罪化的規定,導致產生破壞刑法明確性的危機。因此本於刑法謙抑原則,在解釋上應該要更加謹慎。

此外,在《個資法》第41條附屬刑法的規定來看,在經驗上除非有其他事證得以佐證律師抄錄他人個資的行為目的在於透露或散布給他人,否則單憑告訴代理律師在當庭見聞他人個資後出於和解聯繫之用的抄錄行為,很難說構成《個資法》第41條所謂「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的主觀要件。
在實務上,一個具有「職業常識」的律師想要取得或抄錄對造個資時,會禮貌地徵得對造與檢察官的同意。本案律師採取的「偷偷抄錄」作法或許可能使在庭的關係人產生被冒犯的感受,從而間接對於訴訟後續發展產生不利影響(例如因為冒犯對造而平添衝突或影響後續和解可能性等)。
但這等因為「新手律師」經驗不足而產生的無禮或冒失行為,是倫理層次的問題,「專業倫理」和「犯罪」是兩回事,不見得能夠劃上等號。檢察官必須釐清自身的定位——究竟是法治國家從事刑事訴追的司法人員,還是自命代表國家秩序利益、守護倫理風氣的道德警察?
從「檢察官定位論」檢討濫行偵查之問題
從實務經驗來看,本案承辦檢察官以充滿爭議的《個資法》刑罰規定之罪名,貿然當庭將律師轉為被告,不只無端製造偵查庭中的兩造衝突關係,更製造檢方與律師的對立關係,恐怕比抄錄他人電話號碼的新手律師更為冒失,且令人質疑檢察官的角色定位與職權。
我國「檢察官」制度繼受自德國法制,卻在繼受過程中產生定位不明的問題5。事實上,在德國,檢察官定位論亦是從上個世紀60年代爭論了數十年的問題,特別是在歷史教訓的脈絡、現代刑事政策的改革之下,檢察官的定位也隨之變遷。從最初「法國大革命之子」(Kind der Revolution)6破除「糾問制」的司法改革,但同時又淪為君主制下,行政權所把持作為控制司法的工具7,因而被譏為「俾斯麥政府的僕從」(Büttel der Regierung Bismarcks)8。
其後德國經歷納粹時期、前東德時期,檢察權被濫用而淪為警察權附庸9的血淋淋歷史教訓後,1955年時任黑森(Hessen)邦檢察長、德國轉型正義史上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檢察官Fritz Bauer10於演講中指出,「檢察官」在德文以"Staatsanwalt"(Staat係指國家,Anwalt係指律師,直譯為「國家律師」)一詞稱之是不適合的,該辭源來自專制時期,已經不適合當代刑事訴訟,因為「檢察官不是國家的律師,也不是國家利益的代言人;檢察官代表的是人民與社會存在的權利,並防止權利遭到國家或其他私人的恣意侵害。」「檢察官受到法律的約束,其中最重要的是為人權所拘束。」11這段對於檢察官定位的重塑,成為德國近代檢察學重要的一頁。
檢察官維護法治國的重要任務,便是對日益強大的警察權進行合法性的控制,且不得淪為警察權的一部分12。

如果爬梳檢察官制度的歷史縱軸脈絡,可以發現,不同於我們台灣人過去在公民與法律課本中讀到的「破除糾問制的包青天司法」如此光風霽月、理所當然,檢察史其實是在歷史的創傷與教訓中蒙上濃重陰影,而不斷改革、轉變為符合當代法治國原則的「法律守門員」的角色。
在上個世紀曾有少數見解主張檢察官為「純粹行政官」,為追求國家秩序中重要的共同利益而生的國家行政手足13,但並未被德國聯邦憲法法院14與通說採納。當代的檢察官,必須擺脫其歷史的陰影而堅守其法律守門員的客觀義務,更必須自我節制,不能淪為魯莽的「秩序警察」、「道德警察」,不能任意揮舞著自行想像的正義之劍而懲罰那些其心目中認為危害國家秩序與道德倫理的人。
然而在台灣,檢察體系在沉痾已久的體系文化之下卻似乎反其道而行。首先在於我國司法官訓練的分科訓練階段中,並未強調「檢察學」的教育,以至於檢察官的圖像在司法實務工作者腦海中始終模糊;再加上檢察體系那套長官紅人至上、與媒體相互為用塑造例如「維護治安」、「戰功」等警察化的「正義形象」為主流的英雄主義「升官圖」潛規則,使得「要升官,首先要忘記信念」15,而逐漸迷失,錯把「維護社會秩序」、「守護國家利益」的正義形象當成檢察官定位。
因此,造成部分檢察官為了獲得社會大眾崇拜英雄、上級政治紅人「器重」、或在個人素樸正義觀裡自詡為伸張正義的救世主,因而時不時「暴衝」,濫行發動無意義的偵查,或透過不合理的偵查行動來惡整不符合自身(或上級指示)倫理價值的「敵人」,這些個別檢察官自損檢察官尊嚴的行為,勢必將會繼續引發檢察官到底是行政官、還是司法官的定位爭議16。
這個檢察官的定位爭議,在我國2016-2017年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期間到達白熱化17,如果筆者的記憶沒有錯,基層檢察官因應當時檢改問題而生的「劍青檢改」,基本主張便是以檢察官的司法官屬性做為出發18,主張其客觀性與獨立性,並對後續許多時事,例如監察院干預檢察官獨立行使職權「干預司法」而為針砭。
在面對這起檢方與告訴代理律師的偵查庭內「茶壺風暴」事件時,如果檢察體系對於當事人/關係人的個資如此重視,那麼其聲明光是站在本位立場,而劍指告訴代理人的「律師倫理」,要求年輕律師「應以高度自律、嚴謹倫理自許,端正行事,刷新律師風氣」,卻忽略檢察官自身的「法律守門員」定位,檢討法規面的問題(例如呼籲法務部提出修法)、體制與設備(例如筆錄系統)對於民眾個資保護之不足。
此外,該聲明亦未顧及本案承辦檢察官採取類似於「道德警察」的行為妥適性,此種立場片面而未能反求諸己的論述,難免讓人疑惑其是否仍堅守檢改最初的主張,因此在律師界產生更大的反彈,使得爭論更加劇烈而失焦。
在筆者來看,全律會各自僅基於律師本位、劍青檢改基於檢察本位的立場出發,因此雙方聲明雖然火花四射,讓媒體與外行人看了一頓熱鬧,但實則根本是意氣之爭,在訴訟法制面根本沒有交集。而本文以上所提及的法律與制度面的缺漏問題,便被忽視了。

- 參見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理由欄【16】。
- 《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91點第1項前段:「告訴人於偵查中,得委任代理人,該代理人並不以具備律師資格者為限。」至於偵查中之辯護人,依《刑事訴訟法》第29條本文規定:「辯護人應選任律師充之」。
- 依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2項規定,檢察官對於行使辯護權且具有在場權之「辯護人」,猶得在公益考量下得限制或禁止其於訊問時在場、筆記或陳述意見之處分,那麼對於不具有在場權之告訴代理人,自然得以限制或禁止。
- Beulke, Werner / Swoboda, Sabine (2020): Strafprozessrecht, 15. Auflage, Heidelberg: C.F. Müller, §5 Rn. 88; Kindhäuser, Urs / Schumann, Kay H. (2019): Strafprozessrecht, 5. Auflage, Baden-Baden: Nomos, §5 Rn. 1; 林鈺雄(2000),《檢察官論》,台北:學林,第95頁以下;吳忻穎(2021),《扭曲的正義: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走向崩潰的檢警與媒體》,新北:聯經,第41頁以下。
- 林鈺雄(2000),《檢察官論》,台北:學林,第13頁。
- 此一稱呼源於前柏林檢察長Günther於1973年的著作。Siehe dazu Günther, Hans (1973), Staatsanwaltschaft- Kind der Revolution, Versuch eines juristischen Essays, S. 23 f. 然而對此則有不同意見,布蘭登堡檢察長Rautenberg教授則認為,德國檢察官制度固然是以1789年法國大革命後的拿破崙式檢察官制度作為藍本,然而,當初普魯士引入此制度時,其實是國王試圖控制日益獨立且不受君主控制的法院系統,而出於政府需要的利益,引入受到行政權控制的檢察官制度,瓜分了糾問制下本屬於法院的偵查權並與法院分庭抗禮,從而控制司法;此外,德國與法國有所不同,在19世紀德意志統一後的第二帝國之前,德國並非中央集權的國家,檢察官制度最初在各地區有不同走向的發展,但基於君主的利益,多數地區都不約而同效仿普魯士透過指令權控制檢察權的作法,只有在符騰堡(Württemberg)王國於1869年2月1日至1879年10月1日具備獨立而不受行政指令權干預的檢察系統。Siehe dazu Carsten, Ernst S. / Rautenberg, Erardo C. (2015), Die Geschichte der Staatsanwaltschaft in Deutschland bis zur Gegenwart, 3. Auflage, Baden-Baden: Nomos, S.567 f.
- Carsten, Ernst S. / Rautenberg, Erardo C. (2015), Die Geschichte der Staatsanwaltschaft in Deutschland bis zur Gegenwart, S.567 f.
- Haft, Fritjof / Hilgendorf, Eric (1992), Die Bindung der Staatsanwaltschaft an die höchstrichterliche Rechtsprechung als Beispiel topischer Argumentation, in: Ostendorf, Heribert, Strafverfolgung und Strafverzicht, FS zum 125-jährigen Bestehen der Staatsanwaltschaft Schleswig-Holstein, S. 279, 283; Carsten, Ernst S. / Rautenberg, Erardo C. (2015), Die Geschichte der Staatsanwaltschaft in Deutschland bis zur Gegenwart, S.124.
- Carsten, Ernst S. / Rautenberg, Erardo C. (2015), Die Geschichte der Staatsanwaltschaft in Deutschland bis zur Gegenwart, S.571.
- 二戰後德國Hessen邦檢察長,在其擔任檢察官任內,對於昔日納粹採取了刑事訴追等重要的法律行動,也包含「奧許維茲審判」(Auschwitzprozesse,包含奧許維茲集中營等罪行的追究),另外在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一書中著名的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中,Bauer在緝捕艾希曼的過程中具有重要一席之地。
- Bauer, Fritz (1955), Im Kampf um des Menschen Rechte, in: Bauer, Fritz / Perels, Joachim (Hrsg.) / Wojak, Irmtrud (Hrsg.), Die Humanität der Rechtsordnung: Ausgewählte Schriften (Wissenschaftliche Reihe des Fritz Bauer Instituts),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Verlag, 1998, S. 37.
- Carsten, Ernst S. / Rautenberg, Erardo C. (2015), Die Geschichte der Staatsanwaltschaft in Deutschland bis zur Gegenwart, S.576.
- Schwerdtner, Klaus-Peter (1970), Staatsanwalt und Strafrichter, RuP 1970, 69.
- 自1950年代以來,聯邦憲法法院對於檢察官定位的見解在文義上不斷遊走,大抵上不反對檢察官在組織上歸屬於行政,但又認為其為「法律守門員」,行使的是刑事司法不可或缺任務,BVerfGE 32, 199, 216. 對此,學說上則有對於「司法權」概念諸多深入的區辨與探討,Carsten, Ernst S. / Rautenberg, Erardo C. (2015), Die Geschichte der Staatsanwaltschaft in Deutschland bis zur Gegenwart, S.544 ff.而目前德國檢察實務則對於自身客觀使命具有高度自覺,在「歐洲一體化」要求檢察官的獨立性與客觀性的呼聲,以及透過檢方終結程序的訴訟經濟刑事政策之下,未來德國檢察法制的走向或可預期更貼近司法屬性。Ähnliche Ansichten z.B. Killmer, Dieter (2020), Eine unabhängige Staatsanwaltschaft- Rückenwind aus Europa, DRiZ 2020, S.304 ff.
- 對此體系文化詳見吳忻穎(2021),《扭曲的正義: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走向崩潰的檢警與媒體》,新北:聯經,第108頁以下。
- 此亦為德國檢察官與學者所呼籲,應檢察史中吸取教訓而避免的亂象,Carsten, Ernst S. / Rautenberg, Erardo C. (2015), Die Geschichte der Staatsanwaltschaft in Deutschland bis zur Gegenwart, S.578.
- 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過程中有諸多辯論,而最後的成果報告勉勉強搶地認為「目前檢察官仍具備所謂『司法官』屬性」,參見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成果報告,第47頁。
- 當時同為劍青檢改成員之(前)檢察官先後在媒體與社群網路發布諸多投書與倡議,例如陳宗元(2017),〈檢察官陳宗元:對檢察一體的錯誤想像〉蘋果日報,2017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