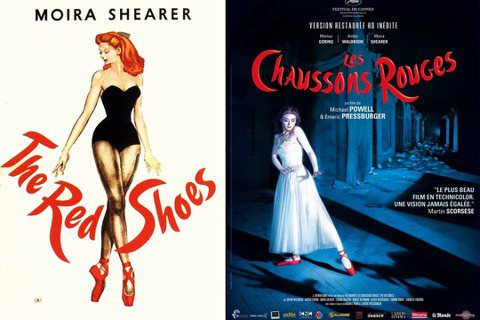蔡明亮《日子》:原來,這才叫做「過日子」

(※ 本文有雷,斟酌閱讀。)
看完《日子》,朋友問起有什麼感受,想了一下,回覆兩個字:可愛。
蔡明亮導演是一個很可愛的創作者。他有身為藝術家執著的一面,求真或求美或求全,更有熱烈想邀請觀眾進到他世界裡的吸引力。上次在光點華山電影館門口巧遇他在賣票,合影簽名幾乎來者不拒,側身一步欣賞他和粉絲之間的互動,早已超越傳統概念裡一個電影(劇情片)導演和他的觀眾。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全方位藝術家,正在和對他經營出的世界感到好奇,或者喜愛流連在那個世界的眾生,往來時激發出一句句的「歡迎光臨」、「感謝您來」。這樣的駐足、流連、停步思考、繼續前行,帶有些許誘惑的磁性,也帶有濃濃分享的誠意,愈想就愈覺得那就像我們在參觀美術館時,會激起的內心悸動。
參觀的人不必喜歡每一幅看到的畫作,但「參觀」、「品味」這些舉動,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喜愛、讓人快樂的思想刺激。
想起幾年前在金馬影展試片會場上初見《郊遊》,刻骨銘心的蒼涼和撕心裂肺的痛,排山倒海而來。不管是狂風裡的一曲〈滿江紅〉,還是吃高麗菜的悲從中來,那時蔡明亮導演的作品,擁有強大的氣場,強大到它衝出了電影銀幕,衝進了美術館,而且立體成型為一場又一場的展演,包納進愈來愈多的元素,原本已經厚實的內涵又愈來愈豐富。
然後,我們等到了這部《日子》。
它樸素,甚至粗糙得像還沒打磨的手工作品。說得不客氣一點,不少網紅的拍攝都比《日子》還要講究,還更雕鑿。
但《日子》就是有一股魔力,吸引你在那麼漫長的鏡頭、那麼久的時間下,繼續看下去。看著看著,居然也看出了親切感,原本被貼上「高冷」標籤的「藝術片」,看著看著,居然也可愛了起來。


這部電影好單純,滋味層次卻又好飽滿,故事寫起來,其實像童話。
山裡住著一個中年男子,終日跟樹林、風雨、山徑、池魚為伍。他得了怪病,脖子會歪,很不舒服。不知是否因此,他的生命幾乎已經靜止成在椅上凝望雨水滑落窗前,有時,連眼睛都懶得多眨幾下。
熱帶大城市裡住著一個青年男子,活動的空間就是一方斗室。他身無長物,所有東西都擱在地上;他在這裡燒飯、洗菜、用餐、沖澡、就寢,午後方才起身上工。看起來,似乎是在夜市擺攤,又或者,除了顧攤位,還另外賺些臨時外快?
中年男子下山進城就醫,又針灸又燒炙,看得旁觀者都心驚肉跳。他在城市裡漫遊,種種不適都寫在臉上。焦躁得在街角抽菸,又在人群裡惶惶而行,癱坐在旅館房間裡,任憑窗外的高樓大廈兀自挺立著。時間,在他們兩人的生命裡,似乎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作用,日復一日,日子,也就這麼過著。
這天,中年男子開始整理旅館的床鋪,好像在等待什麼人到訪似的;而且他鄭重其事把現鈔收妥,看來,到訪的可能是個陌生人?
果然,門鈴一響,進來的是青年男子,兩人隨即上床,由青年為中年按摩、推油,肌膚親暱之際,自然而然發生該發生的事。事後,略帶靦腆的現金交易似乎讓中年男子有些羞怯,稍停半晌,他多給了青年一份小小的禮物。
兩人離開旅館房間,他抽起取電房卡,關上房門,等了一會,亮堂堂的房間啪的一聲燈火俱滅。


之所以用「可愛」形容這部電影,是其中隱隱約約,透露出整個創作團隊在克難、簡素,甚至「低成本(我不願意用『廉價』這個詞)」的情況下,尋找到的那份泰然自若。那樣的自在情狀,帶著我們從「病痛」的張力掙脫而出,原來我們並不是因為名醫高人的醫術有多麼靈妙,金針銀灸是多麼靈驗,而重獲健康的。
我們是因為微光之下,人與人之間的親密接觸,還有,在不起眼的小音樂盒的樂聲裡,感受到生而為人,六慾七情能獲紓解、發泄,甚至因珍惜而顯可貴的方寸神念,於是愛上它的可人情態。
所以才稱它「可愛」。
電影最後三分之一,愈見可愛,而且可愛之外,更得自在。
看他們兩人遊走在熱帶城市的大街,霓虹早滅,街市卻仍藍光璀璨。濕溽的氛圍、周遭的車水馬龍,環抱著的是萍水相逢的兩人,在小食肆對坐共食,一言不發,卻讓人不禁嘴角失守,微微笑起。最後的最後,兩人各自回歸生活常軌。一個回到山裡,一個回到斗室,不經意之間,那份在金錢交易之外多出來的贈予——那個小禮物——在一成不變的生活裡,似乎真的起了點什麼作用。
原來,這才叫做「過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