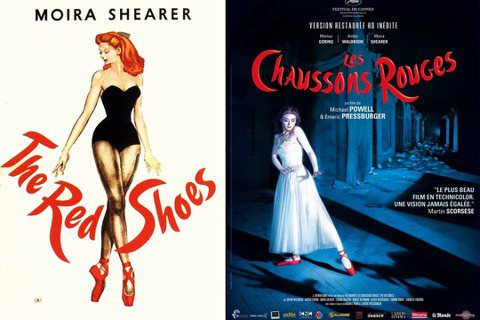《消失的情人節》:陳玉勳白日夢宇宙裡的「急驚風」與「慢郎中」

(※ 本文有雷,斟酌閱讀。)
很早就對「支持國片」的口號失去了熱情,尤其人在迷局裡,愛之深責之切,幾番反覆來回,有時真的氣得在戲院裡白眼翻到險些抽筋。然而,金馬入圍名單一開,還是忍不住關心。
我們的電影產業就只有這麼一丁點大,就算加上香港、中國大陸、星馬東南亞,加上全世界的「華語電影圈」好了,那也是所有人一磚一瓦,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很難因為一兩句「氣話」,說不支持就不支持,說不看就不看的。挑了間格局方正、空間感還算氣派的影院,觀賞這次金馬獎入圍11項、領先群雄的《消失的情人節》。

陳玉勳的白日夢宇宙
回想起當年第一次看陳玉勳導演的電影作品《熱帶魚》,先是跟影癡好友直衝戲院,之後參加金馬觀眾票選時又看一次,邊看還邊「嫌貨」覺得「格局太小」、「瑕疵太多」等等。事隔20幾年,這些缺點早已成為整部電影的「特點」,成為每次重看時都回味無窮的滋味,包括日出時飛向大海的直昇機、笑到岔氣時猛然躍上銀幕的地層下陷海水灌入住屋畫面,以及文英阿姨名留影史不朽的蛇母娘娘。
幾年前在澳門歡度農曆新年,過關進廣東看《健忘村》,好多的失衡、失準、失手,但也有好多突如其來的詼諧、調皮和回甘,那就是陳玉勳導演的正字標記,即便在這樣一部古代背景的合拍片裡,也依舊鮮明無比。
這次的「入圍11項」還是一樣。有些地方「卡卡」不順暢,同時又有好些「這是怎麼想到」的大驚喜,令人擊節,光彩奪目。難得的是勳導依舊是勳導,依舊是打造《佳家福》影集片頭的那位喜劇鬼才,從《熱帶魚》一路而下,沉澱在他創作世界底層的那份憨厚,已然發酵出馥郁的醇味。《熱帶魚》裡在1990年代初期台灣底層社會的小人物善心,於21世紀邁入第三個十年的開端,結晶成急驚風與慢郎中四目交投時,心裡一酸一甜,由衷發出的破涕微笑。
25年前《熱帶魚》的宣傳標語,說的是要把這部電影獻給所有「愛做白日夢的人」,天知道,在2020年的此時此刻,我們的娛樂產業,我們的電影環境,還有我們自己,有多麼需要這樣的能量和動力,去做一場能鼓舞自己、溫暖人心的白日夢!

急驚風李霈瑜
《消失的情人節》男女主角的表現討論度也頗高。據導演本人表示,劇本是自己寫的,他太清楚女主角的重要,主戲都在她身上,男主角要到幾乎故事進行一個小時之後,重心才會轉過去。他早早就鎖定劉冠廷出任男主角,女主角則費了好一番工夫,才相中由李霈瑜出飾。
對筆者來說,大霈身上有太多值得挖掘的潛力,當不經意綻放出來的時候,燦爛可喜;但當她緊抓劇本、台詞,急著想運用「方法」來「演」那個角色的時候,呈現出來的往往是著力過深的跌跌撞撞,而不是一個人物立體成型的存在感。
這恰好也是當前國內許多青年演員的表演缺陷,急急匆匆,忙著「演」,而不是細心梳理一個角色應有的「存在感」。「存在感」這三個字用中文書寫,甚至都還不夠精準,如果用英文指涉,不僅是「existence」,是「presence」,更是「being」,是一種活生生的狀態。
大霈飾演的角色,就是前文所謂的「急驚風」,按照劇本的設定,她做什麼事都比旁人快一拍,快到最後,一分一秒累積起來,積滿一個整天,在陳玉勳導演的白日夢宇宙裡,這個「整天」就消失了,因為都是被她事先預支掉的。
在電影前半部以女主角為敘事主體的段落中,大霈時常把角色的「急」詮釋成「快動作」,但在「動作」(action)與動作之間,她的「反應」(reaction)往往出現節奏的誤差,以致我們看到的人物總是不停在衝撞,接著突然打頓點,然後又衝撞,又打頓點,一連串的頓點打下來,讓人備感吃力。
但偶然之間,她抓對了「reaction」的節奏感,把「急」和「快」連成一氣,比如她和黑嘉嘉在郵局裡酸言酸語彼此拋接互損的橋段,或者她和林美照、顧寶明的幾場對手戲,就顯得相當自在。導演幾次強調「非常難拍的大魔王」哭戲:一場是獨自吃米粉垂淚,一場是郵局櫃台四目相對,她也都是放下了「用力」,放下了「方法」,不再以算計的方式,而是以誠懇換得真心,自然靈動,可圈可點。

慢郎中劉冠廷
至於劉冠廷詮釋的「慢郎中」角色,很意外地打動了我。
不是因為我對他沒有期望,相反地,他應該算是台灣新生代男演員裡,最令人期待的一位。劉冠廷去年在《陽光普照》展現出來的妖邪戾氣,記憶猶新;這次《消失的情人節》改演公車司機,有半部電影甚至還要收起他亮眼的俊帥外型,腫著一隻眼睛慢慢活動,他交出一張遠高出我期望值相當多的成績單。
他在片中琢磨出一種自然存在的怪咖節奏;當然,「硬演」的痕跡也不是沒有,比如在高中拍照時巧遇地震一場,那個過慢的反應,就和戲裡小朋友在鳴槍起跑時過快或過慢的步伐一樣,比較屬於導演方面的安排和算計,鑿痕太深,搏君一粲固然無可厚非,細細想去,還是太過「綜藝節目」了一點。
然而,在郵局裡的諸多細節,像是抽號碼牌、排隊的期待,我們都能感覺到演員把原本所謂「正常人」的「正常節奏」,拉成長線條,成為角色生活步調的一種「慢的正常」。每一個動作,每一個反應,他都完整執行,有條不紊,不但讓角色可信,更運用自身口條的特色——略帶口音但維持著自然、合理的流暢感,沒有過份矯正的標準,也沒有口齒不清的腔調——完整呈現一個可喜、暖心的憨厚人物。
隨著他,我們登上公車,一路開往嘉義東石的海邊,他一邊駕車,一邊向身後的女主角娓娓道出長篇告白,一字一句,不停叩擊我對「愛做白日夢的人」這句老話的共鳴——他居然擔起如此巨大的責任,帶著銀幕裡的劇中人和銀幕外的看戲人,一起進入那個不可思議的白日夢世界。在那邊,有夕照,波光,浪影,還有一切都靜止時,仍然輕輕吹動著的海風。

白日夢的開花結果
回到台北,在女主角獨居的斗室靜坐一夜,他想吻又不敢吻的掙扎,以及最後退步回身,將遺憾化為祝福的那一聲「情人節快樂」,都在協助觀眾儲值和積累,將所有的善念、關懷,以及愛,收藏起來。這個角色的完結點在於走出郵局,突然因為旁人一句「豆花」的台詞,意識到自己任務未了的那一瞬間,那個「慢」的長線條,把角色的戲劇弧線拉到那一刻的驚地裂天,達到最飽滿的高潮。
或許因為對戲的對象,使得大霈頻打頓點的表演,來到劉冠廷面前顯得順暢且穩當,最終四目相對的哭,便是讓我們跟隨角色儲蓄許久的感情一次宣泄出來。男主角的慢半拍更令全場觀眾在他笑著舉起綠豆豆花的贈禮時,已經先落下眼淚。緊接著,他那「有備而來」的信心和體貼底下最柔軟的誠懇,更使他慢了半拍才泉湧而上的眼淚,催得觀眾破涕為笑,在悲欣交集的氛圍中,把白日夢變成用淚水和笑聲灌溉出來的真實,開花結果。
我不是金馬評審,沒有投票權,也不可能在評審會議上幫任何人拉票。但我明白,這位演員不僅值得我喜愛,更值得大家信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