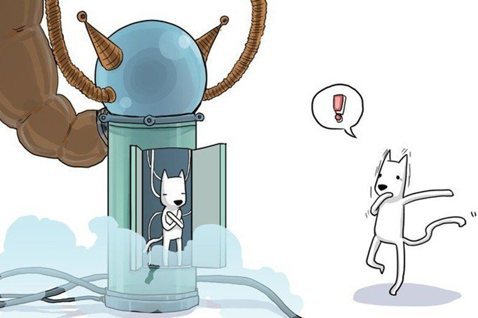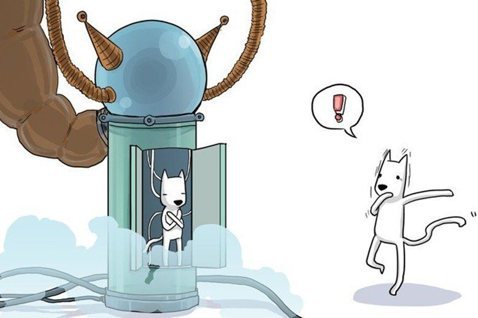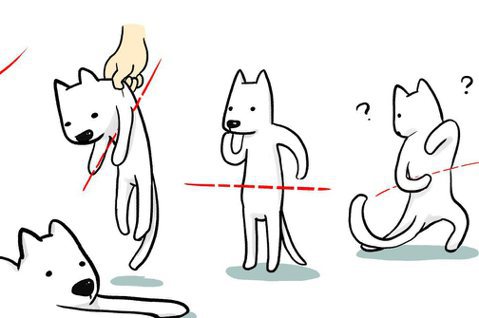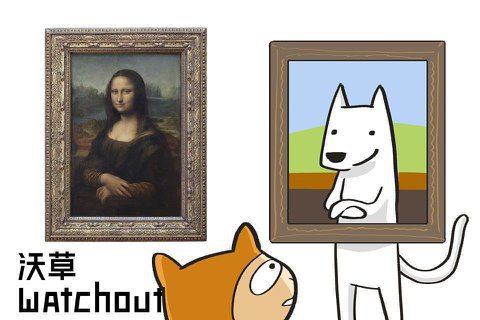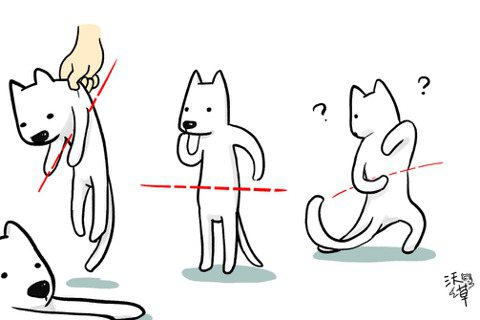豬文/「真正連結香港人的,是痛苦」?——身分認同的哲學思考

過去一年多,香港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風雨。無論從宏觀的國際格局,或是微觀的個體層面去看,變化都翻天覆地。「香港人覺醒」這五個字從2014年的雨傘運動開始在公共領域出現,而「香港人」的主體身分認同,有人則認為是在2019年正式成形。
身分與政治的關係總是糾纏不清。一個人的身分認同,影響了一個人的政治取向;同時政治環境的急速改變,又造就了個體的身分認同。香港有一篇討論區上的貼文,經常被人翻舊帳。這篇貼文是2008年時,一眾網民直播觀看北京奧運開幕式的即時討論,裡面的回覆都是:「正到喊,第一次覺得自己係中國人」、「好感動」、「中華民族加油!」之類。2020年回看,真有滄海桑田之感。如果你現在到連登討論區,你會懷疑這到底是不是同一個香港,因為你只會看到「你才中國人,你全家都中國人」之類的貼文。
從哲學的角度思考這些現象,至少有兩個相關的問題:首先,這些社群身分或國族身分,真的有意義嗎?這個問題牽涉到對自由主義 (Liberalism) 或世界主義 (Cosmopolitianism) 的一個常見批評:不少社群主義者都指控自由主義對政治的理解是錯誤的,因為自由主義對人的理解是錯誤的,他把人理解成一種沒有歷史文化背景與特殊人際關係的抽象物,人像一粒「自由」的原子,與其他原子「平等」地並列在一起。社群主義者認為這個「原子化」的社會無法說明人關心政治與參與政治行動的推動力。
第二,撇開社群身分是否有重要性,我們還要問究竟社群身分的具體內容是如何決定的。也就是說,到底在甚麼意義下,我是中國人、台灣人、或者香港人呢?究竟是所謂血緣、文化、命運、抑或是共同經歷所決定?
這兩個問題都是龐大的哲學問題。這篇文章接下來只希望分享一下,我從過去一年多香港發生的種種而來的啟發與思考。
香港與台灣的距離
上面提到香港人的中國人身分認同高峰,出現在2008年。我還記得那時侯身邊有些同學都熙熙攘攘地說要穿件紅衣,到街上迎接奧運聖火,當時的我完全不感興趣,只覺得這種群眾狂熱很無聊。直到進了大學唸哲學,開始讀了些中國哲學跟新儒家的東西之後,才慢慢成了一個「大中華膠」,信仰著「文化中國」的概念。這種狀況幾乎壟斷著我的大學階段,直到我來到台灣唸碩士。
來台灣後我認識了朋友Y。有一天晚上,我跟Y在台大男一宿舍後面一個小階梯聊了很久。那時候的我還是保持那種新儒家式的大中華世界觀,我一直跟Y說中華文化在神洲大地花果飄零後,就要靠台灣傳承正統的中華文化,希望台灣能守住這點血脈。在當時的我眼裡,台獨的最大問題就是會把中華文化的血脈切斷。
Y那時候回應:「為什麼有共同文化就得是同一種人,組成同一個國家?」「如果分享著共同文化是不能分離的理由的話,那中日韓要怎麼分?英美要怎麼分?歐洲大陸那些國家要怎麼分?」Y再補充:「何況中台真的能稱得上是同一文化嗎?即使我們使用相同的語言文字,有某些方面共同的生活方式,例如過農曆新年,但我們還是有很多差異,台灣文化有其獨特的一面,不應該隨便把他歸納在中國文化底下。」
這算是我自大學建立起的大中華情意結所受到的第一次衝擊,自此愈走愈遠。從哲學的角度去看Y的話,他至少提出兩個理由反對那時候相信的「文化論」。第一,Y指出了共同文化並非共同身分或共同國家的充分條件,這是因為世上有很多有著「共同文化」的國家,也有著不同的國族身分認同。例如英國跟美國,他們也是使用著一樣的語言文字啊,但就並不代表美國人就是英國人、美國應該與英國和平統一,確保大英帝國領土完整。
第二,Y對台灣文化的獨特性的重視,也顯示了怎樣才算是「一個」文化(individualisation of culture) 的困難。文化與文化之間總是互相影響,特別是在全球化的世代裡,每個地方都有一定影響力。既然如此,我們究竟是按甚麼標準去切割開一個一個文化呢?中國與越南都過農曆新年,那他們就是一個文化?英國與美國用同一批字母,那他們就是一個文化?算不算是同一個文化視你需要的分類有多細緻。粗疏地看,中國與台灣可能算是同一個文化,但稍為仔細地看,我們便難以將兩地文化歸為一個文化。
雖然我們認為國族身分可以是兼容 (inclusive) 的,例如我們可以同時擁有中國人跟香港人兩個身分,但很多人也同時認為國族身分是全有或全無 (all or nothing)的:要嘛你是中國人,要嘛不是。若然國族身分是全有或全無,我們又怎能用「文化」這個只能有程度之分 (matter of degree) ,因此難以界定怎樣才算是「一個」文化的概念,去定義國族身分呢?
由痛苦連結的香港人
除了這兩個問題要解決,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也讓我想到第三個問題:文化就國族身分而言,不但非充分條件,連必要條件也稱不上。在這場社會運動裡,有很多少數族裔——尤其是南亞裔——的香港人參與。這些人可能連廣東話也不會 (當然也有很多操流利廣東話的),是虔誠伊斯蘭教徒,按伊斯蘭教教義生活。在香港,這些人都被稱作「南亞手足」或「南亞兄弟」。雖然我們的文化與生活習慣很不一樣,但我們都認為這些「南亞手足」是香港人的一員。
這是為什麼呢?什麼東西使得擁有著不同文化背景的「他們」成為「我們」呢?我認為是共同的經歷與情感。我們即使說著不同語言、過著不同的節日、吃著不同的食物,但我們都曾經共同在過去一年多裡,為著香港這片土地的自由民主而奮鬥。我們都曾經在夜裡為香港躲被窩裡流淚、我們都記得612、721、831這些數字、我們都記得街上硝煙的味道、我們都記得自己心中的憤怒、我們都記得自己在極權面前的恐懼。這些東西就是香港人身分的內涵。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這句話總是被人提起。這句話意味著香港人與台灣人有某種緊密的聯繫,因為我們都要面對相同的命運:中共的壓迫。我並不反對過去一年多讓香港人與台灣人走得更近,但我仍然認為共同經歷比起共同命運,在構成國族身分上更加根本。也就是說,對於斷定一個人的社群身份這個問題來說,過去比起未來更加重要。
我去年底到了台灣一次,這次短短的旅程加強了我這個想法。那時候香港社會運動仍然得到極大量的國際關注,所以那幾天也有很多認識或不認識的台灣朋友,問起我關於香港的狀況。我從不質疑這些朋友,或者因為關心香港而打開這篇文章的讀者的好意,但我也強烈地感受到香港與台灣的距離。
那幾天無論我如何努力跟台灣人訴說香港人的經歷與感受,總是有種隔靴搔癢的感覺。無論他們如何關心我這個香港人,只要他們沒有親身經歷過香港人經歷的,他們也無法真正體會我的感受。在這些真實而巨大的痛苦面前,一切語言都顯得蒼白無力。
我不是想鬥慘,世界上還有無數苦難發生過或正在發生,我只是想指出,共同經歷與感受才是國族身分最堅實的內涵。曾因佔領立法會而後來流亡美國的梁繼平說:「真正連結香港人的,是痛苦」大抵就是這個意思。
香港與世界的距離
不過,即使我認同梁繼平說過去一年多的痛苦鑄造了香港人的主體身分而與台灣拉開了距離,但從另一角度而言,香港人也拉近了與世界的距離。狹義下,台灣人與香港人沒有共同經歷,因為只有香港人曾在銅鑼灣上街遊行;但廣義下,台灣人與香港人也非沒有共同經歷,因為台灣人與香港人都曾經有為民主自由而奮戰的經歷。
這一年過後,香港人明顯對世界各地、不論以往或是現在的抗爭運動多了不少關注。香港會關心白俄羅斯、泰國、黎巴嫩的抗爭、陳菊的遺書成為了連登討論區的熱門貼文、哈維爾的《無權力者的權力》和「活在真相中」成為經常出現的關鍵字,這都是因為香港人經歷了過往一年多的事之後,體會了從前未曾體會過的,才與世界各地的這些人民建立起連結。所以,我認為過去一年多不只是建立了香港人的香港人身分,也建立了香港人的世界公民身分。
誰在吶喊?
回到起初的問題,究竟是社群主義說的社群身分,或是自由主義說的普世價值在起作用呢?或許人本來就是包含著這兩個面向,因而無法給出一個截然了當的答案。正如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一樣,無論你將他定義成一場純粹追求普世價值的運動,抑或是一場純粹的香港民族主義運動,都是殘缺不全的。
如果不是因為對公義、自由、民主這些抽象的價值有所追求,這場運動不可能得到如此龐大的支持。但如沒有具體的痛苦所鑄造出的香港人身分的話,這場運動也不可能如此波瀾壯闊。就在抽象和具體、普遍和殊別的雙管齊下,人才會投入政治。
誰在吶喊?既是香港人,也是在香港的自由人。香港人與台灣人既不一樣,也一樣。
- 文:豬文,好哲學思考,「好青年荼毒室」成員。「好青年荼毒室」為哲學普及團體,目標是把循規蹈矩的好青年帶進哲學的世界。發表內容有深有淺,古今中外,無所不談。在這裏,一切都可以被質疑、反省和追問。實體會室座落灣仔富德樓。Facebook,Instagram,YouTube,Patreon都找到我們的身影,有興趣被荼毒者,歡迎在各大平台搜尋我們。
- 更多:Web|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