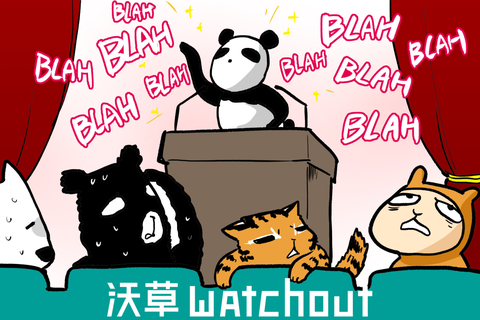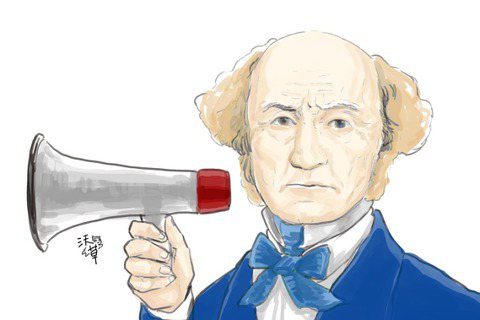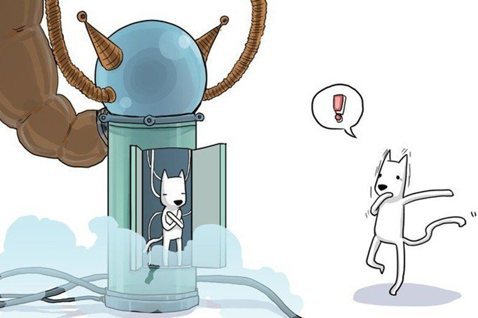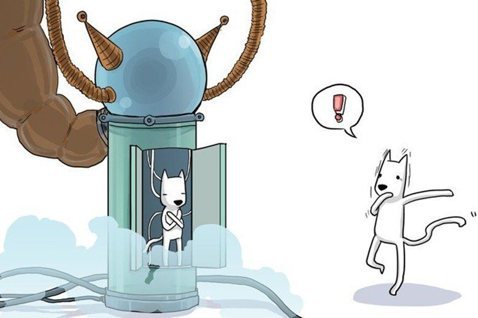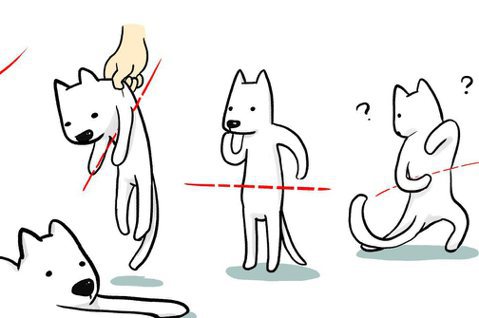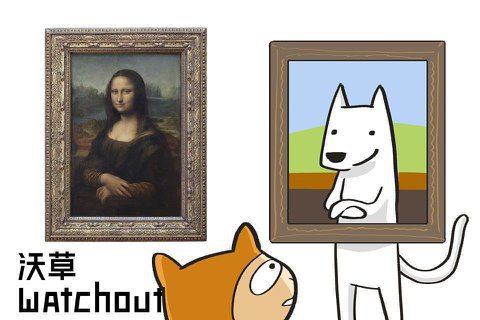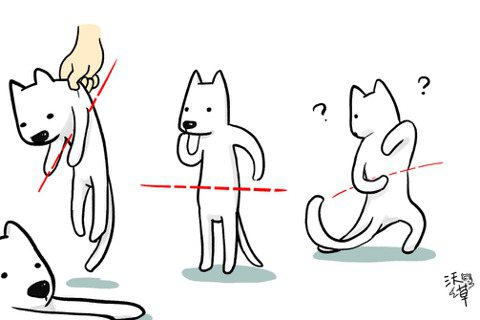楊劭楷/政府能否禁止仇恨言論與假訊息?言論干預的再商榷

先前《沃草烙哲學》專欄刊出了〈「二二八屠殺未曾發生」?假訊息與仇恨言論該受保障嗎?〉一文,作者劉維人主張,給定特定環境和討論方式,仇恨言論、言論操弄和假訊息可能會造成傷害,因此有些時候干預言論是正當的。我將對該文提出一些商榷,希望能引起更多討論,深化審議及論證的公共領域。
本文將分成三部分,首先,我將指出〈「二二八屠殺未曾發生」?假訊息與仇恨言論該受保障嗎?〉(下稱劉文)當中我贊同的論點,並稍微商榷;其次,我會以「傷害」為主軸,指出劉文中從傷害到干預的相關論證忽視了「誰得以決定」的權力問題,而這是彌爾(J. S. Mill)等論者所重視的反對介入的理由;最後,由於劉文提及筆者先前所寫的,關於法政哲學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對仇恨性言論的反干預論證,故筆者欲對此再加以釐清。
是的,有些理由支持干預
首先,劉文中所提出的干預言論的四個理由為:
- 言論市場本身即是干預的結果
- 自由放任市場加劇機會不平等
- 金權與監控資本主義的影響力
- 放任人們言論互相影響會造成負面影響
給定現況,這些理由某程度上皆正確,例如「不干預本身也是一種對政策的形塑」、「每個人在言論市場內的選擇能力與判斷力並不相同」、「有權勢的人可能影響言論市場」等等,由於劉文在此處僅將干預定義成「限制或改變自由市場的行動」,故這些描述自然可以證成某些對言論市場的干預,以矯正這些現狀。如2可能證成介入市場,提供更多的發聲管道;3可能證成對某些言論的要求(如金額限制、揭露來源)。
在此,我欲指出的是,這些理由雖然都是正確的,但所指向的「干預」皆不同,所證成的正當性自然也就大相徑庭。例如:市場本身即是干預結果、市場加劇機會不平等、金權與監控資本主義等理由,並不能證成對特定言論的禁止。
而劉文中,之所以支持干預仇恨性言論、假訊息等言論,是基於言論可能造成某些傷害,而其所指的干預,似乎除了道德譴責和操弄市場之外,也不排除以政府限制、禁止特定言論的手段進行。而本文不擬窮盡所有「干預」,而聚焦在最嚴格的「禁止」、「限制」手段。
是的,言論可能造成傷害
劉文指出,否認大屠殺、詐欺性的投資言論、疫情或疫苗的假訊息,皆可能造成「傷害」,例如「錯誤醫療資訊會讓人錯過就醫時機,仇恨言論則會影響人們的社群認同和政治判斷、讓不同群體進入平行世界,難以彼此理解與尊重」等等。筆者於此部分贊同的是,言論的確可能造成傷害,並證成干預(請再次參拙著碩論中對假訊息傷害的討論)。
但值得商榷的是,要討論言論所造成的傷害問題,應分為兩階段,首先,必須清楚定義「言論類型」,其次才是證成言論造成的「傷害」。如劉文認定仇恨性言論會影響人們的社群認同和政治判斷,並未先清楚定義何謂仇恨性言論,直接討論造成結果的主張,可能會使仇恨性言論的範圍大幅擴張:畢竟我們所發表的大部分言論皆會影響社群認同和政治判斷(如轉發政治文,支持統一或獨立等言論)。言論的類型定義越擴張,造成的「傷害」便可能更寬泛,影響後續干預的正當性。此處不可不慎。
不過,讓認知有限的政府限制言論會很危險
在我看來,彌爾論者反對干預的重要理由,並未在劉文中得到足夠的篇幅:由國家來決定何種言論需要被干預、定義何種言論為造成傷害的言論,皆可能造成政府過度擴權,使得人民發表言論的自由受到過度的限制。
劉文對彌爾的批評可分為兩項,一是認為,為了保留人們犯錯的權利,而放任眼前可預見的錯誤,在道德上是不負責任的;二是認為彌爾的論證不一定會允許人們用言論彼此實質傷害、用言論分裂族群與國家。
從劉文中可看出,其認為彌爾之所以要保護言論,是因為人類容易集體犯錯,不僅犯過很多次道德錯誤(例如各種歧視),故言論自由是種預防,並從中開展第一項放任眼前道德錯誤的批評。
但當代的彌爾論者會如此回應:之所以要保護言論自由,並不是基於此類「結果式的」論證,而是基於認識論式的論證。此論證如下:因為人的認知是有限的,並不可能擁有完整的知識(亦即,沒有人是永遠正確的),那麼就沒有人有權能夠主張,全體人類的意見應該與他一致,進而壓制那類意見1。而由集體人類所構成的「政府」,也會同時受限於這樣的有限性。
此時,若我們允許政府以「不可放任眼前可預見的道德錯誤」而噤聲言論,重點並不是可能審查了真理,讓真理無法突出,而是可能使得政府擴權,恣意、選擇性地審查人民的言論,長遠下來,即造成言論自由系統性的崩壞。
如劉文中提到的分裂族群與國家,在歷史上即曾為統治者壓制異見的理由,故不應輕易允許政府來決定何為「道德錯誤」,但劉文的第二個論證在某程度上仍是有效的,即言論自由不應允許實質造成傷害,不過,此部分仍應釐清、清楚地定義「傷害」,縮小政府擴權的可能。以仇恨性言論為例,近年有主張仇恨性言論的確會對閱聽者造成心理傷害,而並非只是「影響情緒」。而紐約大學教授沃爾準(Jeremy Waldron)更認為,仇恨性言論除了會傷害弱勢族群的尊嚴(dignity),更會危害民主社會所賴以維繫的「公共善」(public good)2。
而在劉文中,認為仇恨性言論產生的影響是:相信仇恨性言論的人完全不信任相反立場,甚至直接不信任其他族群,亦可能會反對道德上正當、有利於其他族群的政策,甚至會支持直接傷害其他族群的政策、撕裂社會,亦可能集體做出道德上嚴重錯誤的行為等等。
筆者並不否認這些現象,但值得商榷的是,若授與政府「判斷何種言論為道德錯誤」的權力,反而更可能使得政府成為「操弄言論」的源頭,政府以道德之名壓制異見,如歷史上以「反共復國」為名,認為異議言論皆不符國族道德的主張。由此可見,劉文所提及的干預的理由,相較於前述仇恨性言論造成尊嚴傷害、心理傷害的論證而言,某程度上,反而是保障我們所厭惡思想的自由之理由。
再探德沃金與仇恨性言論
最後,筆者試圖釐清德沃金反對干預仇恨性言論的立場3。
劉文主張:
- 德沃金反對干預仇恨性言論的理由,並非在保障言論本身,而是保障「發表言論的方式參與討論、讓他人了解自己的狀況理由與感受、以及接近真理、尋求共識的討論過程」
- 該理由會「保障那些願意彼此理解跟彼此尊重的人,而非用言論壓制別人表達意見,或者操弄他人的人」。但由於有些言論影響受眾所處的環境,以及討論的過程及方式(如嚴重不尊重他人、不平等對待其他討論者),導致「各方陷入激情,難以彼此同理,甚至因為失去信任而開始曲解彼此的意見」。
- 因此,「只是『應該讓每個人都能發聲』、『應該讓每種意見都能討論』既不能推導出『應該讓每種意見在每種狀態下都擁有相同的擴散能力』,也不能推導出『應該以相同的效力去保障同一類意見的每一種討論方式』。」
首先,德沃金認為每個人應當對自己的生命負責、對自己的言論負責,才進而主張,透過保障所有人發表言論的權利,以賦予集體生活政治正當性。德沃金正是認為,若允許政府以「人民容易被操弄,故應該限制某些言論的傳播」,是不尊重人民接收、傳達訊息,以決定自己相信什麼、過什麼生活的道德主體性。故德沃金並不是如劉文主張的,是在保障願意彼此理解與彼此尊重之人或討論、接近真理的過程,而是保障「每個人都能發表意見」——也就是言論本身——即便他們不一定願意彼此理解或尊重。
由此可見,某程度上我們也應該確保每種意見都有相同的擴散能力:若允許人基於某種言論有問題(不尊重他人、危害國家社會等)而運用權力大量隱去某些異見,實質上此種聲音也未能自由的發表、發生說服的效果,亦是對道德主體的不尊重
舉例而言:不論是國際上或國內,在某些議題上大量出現的網軍內容,從「認定人民是足以接收訊息、審慎思辨的」角度,亦可能支持允許此類內容流傳,並相信人民能自行慎思此類內容,而不對其禁止。但同前,此時也可以考量此類刻意製造並散布(甚至無法溯源)的內容,是否對公共領域、特定領域帶來傷害。此外,不得禁止,亦不代表不能干預其傳布。
其次,劉文似乎主張,即便我們允許每個人都能發聲,亦不代表「應該以相同的效力去保障同一類意見的每一種討論方式」,並主張:「妨礙釐清真相、不尊重他人、讓人更難理解其他發言者的討論方式,是需要阻止,甚至需要禁止的。」
但這樣的主張,焦點似乎從針對仇恨性言論的「內容」,轉移到針對仇恨性言論「發表的方式」,即仇恨性言論並不是因其對受眾造成的傷害而證成干預,而是因為其「影響討論品質與意願」4。而劉文討論假訊息的部分,亦主張不是依訊息內容真假來分辨,而是視該言論是否傷害討論過程而定。
我認為這裡有兩點值得商榷。第一,這樣的論證,與一般言論自由對仇恨性言論的討論不同:發表仇恨性言論是否會讓各方陷入激情,難以彼此同理,甚至因為失去信任而開始曲解彼此的意見?還是其實大多是針對少數族群的羞辱和攻擊?筆者並不否認前者是當代網路興起的現象,但這是否更多是基於傳播媒介(即網際網路)的改變,而不是特定言論的內容?也就是說,劉文似乎並不是主張仇恨性言論或假訊息應當受到干預,而是「影響討論品質與意願」的言論應當受到干預(更典型的像是網軍)。
第二,劉文中提及,許多公共討論版的「版規」也是根據是否妨礙釐清真相、不尊重他人、讓人無法理解其他發言者的討論方式的準則來制定發表言論的準則。但筆者在此欲指出的是,一般公共論壇所設定的版規,與政府決定哪些言論符合前述標準而予以噤聲,兩者的權力效應完全不同。而這也能在此連結到前述彌爾論者、德沃金論者的主張:筆者很難想像,若授予政府判斷「一個人在發表言論時是否真心想與他人討論」的權力,政府會如何對待異見者?
即政府有限的認知性,除了使得其無法清楚分別外,更可能造成其對異見的壓制(如果少數族群本來在意見市場上即傾向被大眾忽視,又怎能期待其溫良恭儉讓,總是來理性說服他人?),此外,這樣的權限也將人民預設為「無法理性自辯」、無法判斷「何為惡意影響討論」的言論,進而以公權力認定人民無法對自己的生命負責(而由公權力來為其負責)。
結語
值得一提的是,我所提出的反對理由是針對政府「禁止」、「限制」人民言論等傳統言論自由情形,可以進一步討論的是,是否能允許政府採取較輕微的介入手段?我們可以稱這些手段為「干預」言論的手段,但由於這篇文章僅聚焦在最嚴格的限制、禁止,故這些「干預」手段,並不是本文所能全部涵蓋,而值得繼續思考。
另一方面,本文所討論的,其實是人民與政府間的「雙方關係」。但在網路時代,已有學者指出,言論自由問題除了傳統雙方關係外,更棘手的是三方關係:除使用者、政府外,還有掌握傳播權力的網路企業平台5。
也就是說,要討論網路時代的言論自由,除了可以深究私人網路企業對使用者言論可能進行的「介入」(含禁止或較輕的干預)外,也可以探究政府透過要求網路企業介入平台言論、進而間接限制/干預網路使用者言論的情形,這些都不是本文所欲討論,但也是值得更進一步延伸的議題。
- 值得一提的是,當代學者有認為,彌爾所謂的對錯,並不是指客觀的事實,而是指宗教、政治上的信念。可參拙著〈失靈的意見市場:假消息、言論自由與真理理論〉。
- Jeremy Waldron, Harm in Hate Speech (2012), 4-6.
- 但此並不意味筆者完全贊同德沃金的立場,而是正在發展中。
- 我們可以設一例:真心相信A族群為次等民族所發表的仇恨性言論,與因為先前的教育、成長背景而無知,發表A民族為此等民族的仇恨性言論。對劉文來說,重點並不是兩者的言論皆對A族群造成傷害,而是兩者表達方式的不同。
- Jack M Balkin, Free Speech is a Triangle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