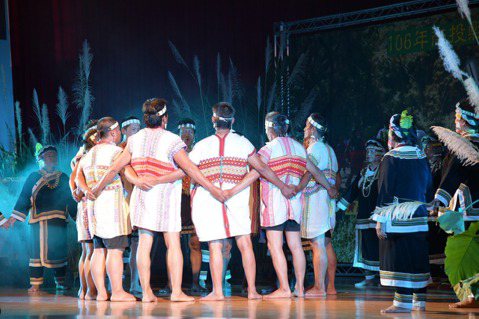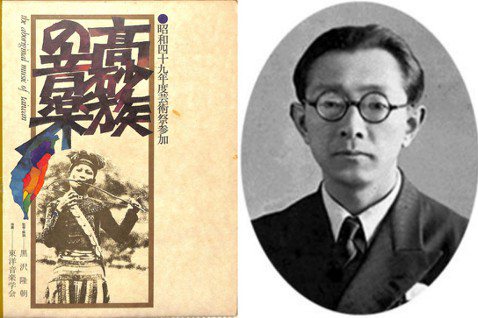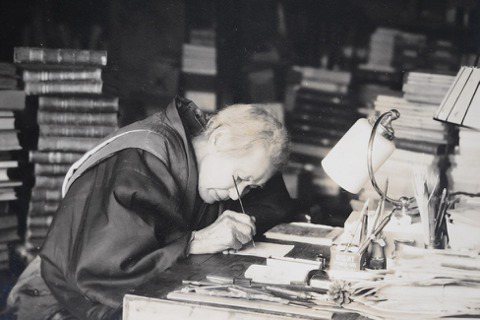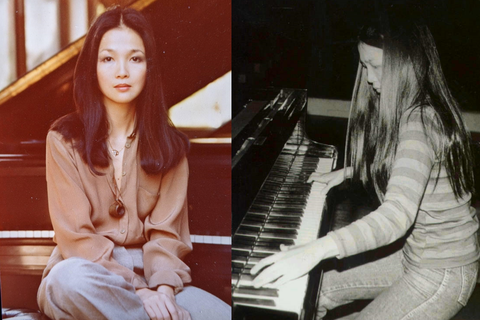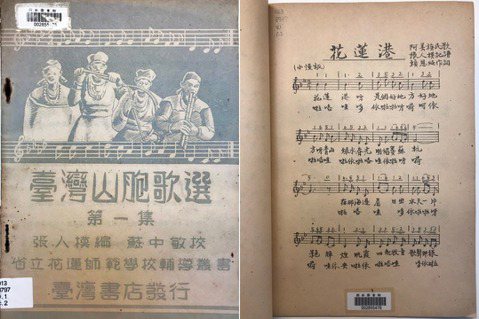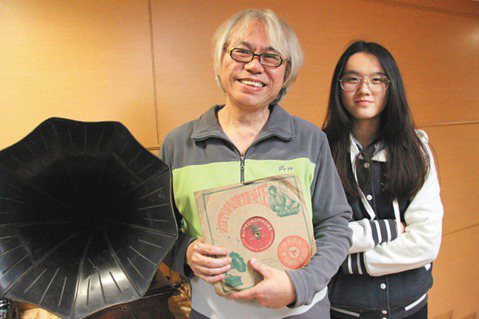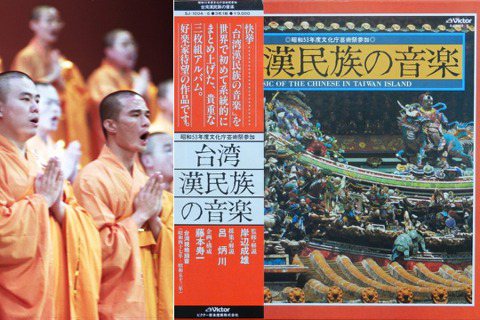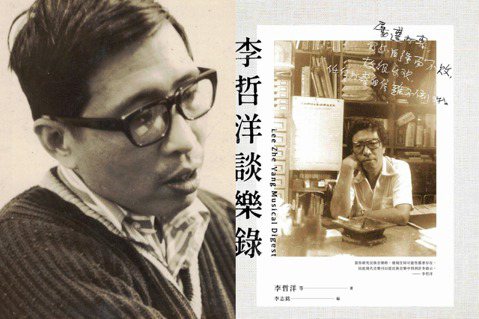當代影劇裡的竊聽者(上):聽筒下的風暴與情愛

前不久,隨著韓國影星玄彬、孫藝珍攜手演繹朝鮮半島南北韓兩地戀人不得見容於世的愛情電視劇《愛的迫降》,近來被廣大觀眾紅男綠女追得風風火火,連帶也使得某些「北韓(朝鮮)用語」在網路上的即時搜索熱度暴增。其中一個詞彙是「耳朵」(北韓語稱「귀때기」),源於《愛的迫降》劇中有一幕橋段:因乘坐滑翔傘被突發一陣風暴吹到北韓迫降的女主角尹世莉(孫藝珍飾),不得已藏匿在當地小村生活期間,某日偶然看見一群北韓小朋友正在欺負另一名弱小同儕,並且圍毆辱罵他「滾開!耳朵的兒子」。北韓語的「耳朵」,指的就是「竊聽員」。
台灣過去在白色恐怖時期,電話被竊聽乃為常見之事,不只包括從事政治或社會運動的相關人士,就連許多一般老百姓也會無緣無故地遭到監聽。
如今,因應當前網路傳播科技的突飛猛進,身處在資訊快速流通、網路聯繫愈來愈密集的時代,人們亦得被迫面對日趨複雜且難以防範盜竊「隱私權」的資訊安全問題。比如前陣子包括教育部等多個政府單位,已將雲端視訊軟體ZOOM當作線上共同會議工具,但後來卻發現該軟體不斷傳出各種資安疑慮,以致談話內容可能會被駭客竊聽而明令禁用。
此外,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為」近來也陸續遭到國際社會質疑,在生產的手機和伺服器等設備中,加裝後門軟體,可將用戶資料傳至中國,遂使各國相繼宣告將其列入黑名單。
對於絕大多數一般民眾而言,個人的隱私遭盜竊,與國安、商業機密被監聽,兩者之間的關係似乎距離有點遙遠,因而每每自覺不以為意。最常聽到的說法就是「我們這些小老百姓的日常對話內容沒什麼重要,駭客根本不會有興趣」,要不就像早年(上世紀70年代)林洋港接受省議員質詢情治單位非法竊聽現象時答覆曰:「白天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喫驚」,也就是說「你平常若沒做什麼壞事,為什麼怕竊聽」?當時即遭黨外人士以美國總統尼克森涉嫌「水門案」1違法竊聽事件下台的國際重大新聞,嘲諷林洋港不知人權為何物。


「老大哥」無所不在
阿根廷作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寫過一則極短篇小說〈論科學中的精確性〉(On Exactitude in Science),內容講述一個古代帝國對於地圖製作工藝非常著迷,當地的製圖師決定要繪製出一張有史以來最詳盡,攤開來幾乎就跟這個國家領土一樣大小的一比一原寸地圖。理論上,這是張完美的地圖:現實世界裡的每個細節都被記錄,圖中每一筆劃也都準確落在實際空間的位置上。然而,正因為這張虛構的理想地圖精確到了極致、資訊量太過龐大,以致於失去概覽功能,根本無法使用。
其後,博學多聞的義大利符號學家暨小說家艾柯 (Umberto Eco,1932-2016)延續這個故事,幽默而戲謔地撰寫了一篇寓言式雜文〈論繪製一比一原寸帝國地圖之不可行〉(On the Impossibility of Drawing a Map of the Empire on a Scale of 1 to 1)。大意是說,我們永遠無法繪製一張與一個地域完全相同的原寸地圖,因為這樣的地圖一旦繪製完成,若是攤開便會遮蔽陽光,地表的植物便會枯萎,地貌便會改變,那麼地圖上的標示與實際的標示便會產生差異。最後的辯證結果,乃是地圖取代了現實世界,成為了帝國本身。
然而,無論波赫士或者艾柯,他們大概都無法想像,爾後到了現今21世紀網際網路數位時代,人們不僅早已突破過去認為「地圖只能存在於紙上」的古老概念(譬如Google Earth虛擬空間),據以實現一比一的(虛擬)地圖已非空想。更甚者,關於「竊聽」一事,亦不必再侷限傳統方法,只針對某特定人士、特定時間和範圍來進行,而是能夠輕易地透過大規模「無差別」搜集所有以網路傳輸的簡訊、語音、電子郵件,就算是看起來無用的資訊,也都全部會被儲存起來。只要國安(情報)人員有需要,隨時都可以直接讀取、監控任何一個人,或是進行所謂「大數據」分析。
這種藉由掌控網路通訊而建立的資訊巨獸,對當權者來說是一種近乎絕對的莫大權力。
2006年,影史上首部將前東德國家情報局「史塔西」(Stasi)搬上銀幕的電影《竊聽風暴》(The Lives of Others)問世,片中講述了柏林圍牆倒塌前五年(1984年)的東德,整個社會籠罩在國家安全局的高壓統治下,人們謹小慎微,就連平常在飯桌上不小心開個玩笑都有可能惹來殺身之禍。
「史塔西」最著名的標語是「我們無所不在」(Wir sind überall),其灌輸給部屬的工作守則為「基本上,每個人都有嫌疑」。據統計,人口僅1,800萬的東德,在長達40餘年的統治期間(1946-1989),一度擁有10萬名正式聘用的諜報探員、1千名電話竊聽員、2千名郵件秘檢員和超過20萬負責通報的非正式合作者(即俗稱線民或告密者),共約有600萬人(達全國總人口三分之一)曾被建立過秘密檔案。
平均每天就有八人以「破壞國家安全」的罪名鋃鐺入獄,每三個人就有一人遭竊聽,包括當時的前西德總理柯爾(Helmut Kohl)都無法倖免,甚至有些西德人民也都在其監視範圍內,堪稱史上最滴水不漏的超高密度情報布建網。不只蘇聯的「克格勃」(KGB)遠比不上,就連納粹時代的「蓋世太保」也要自嘆不如。如此大規模複雜而精細的監控體制,搭配匿名舉報、隨意抓捕、親屬連坐(Sippenhaft)等方式,成功地在東德全境建立一種彼此懷疑、互不信任的社會風氣。在種種壓力的逼迫與利益的誘惑下,不僅鄰人之間會相互告密,就連夫妻、親子、手足和師生彼此也都有可能隨時出賣對方。


竊聽者的自我救贖?
德國新銳導演多納斯馬克(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自編自導首部劇情長片《竊聽風暴》,儼然重現了當時東德極權政府施行全面監控的白色恐怖氛圍,以及在嚴密高壓統治下不得不低頭的人民,乃至他們的人性價值是如何遭到摧殘和扭曲,而尚未完全泯滅的良心,終究也會從暴政壓迫的縫隙裡重新被喚醒。影片本身毋須怒目猙獰,亦不必聲嘶力吼,卻總有一股無所遁形的壓迫感充斥其間,令人不寒而慄。
《竊聽風暴》片中主角魏斯勒(Wiesler)原是一名東德時期對黨忠誠,且監聽及審訊技巧高超的秘密警察,他外表冷峻嚴肅,每每喜怒不形於色,平常言談舉止間的聲音亦不帶任何感情。某天他接獲情報局「史塔西」上級長官指示,奉命監聽被懷疑撰寫反動文章的劇作家德瑞曼(George Dreyman),以及和他同居的美麗女友、舞臺劇演員西蘭(Christa-Maria Sieland)。
於是,他帶著一批特工在德瑞曼的住家布下了天羅地網的竊聽裝置,從牆面、天花板到電燈開關,幾乎無孔不入。衛斯勒甚至還在現場的樓上地板畫出一張一模一樣的對照平面圖,將當時他們的「行動空間」邊聽邊模擬出來,予以更精確地進行全天候的秘密監控。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每天日以繼夜不停竊聽著德瑞曼及其身邊藝文界友人的日常生活,衛斯勒的內心深處竟也開始產生了某種微妙變化。彷彿越來越「入戲」的他,逐漸對德瑞曼的私生活產生了同情,同時也在監聽過程中分享了德瑞曼的內心思想和情感起伏,甚至還愛上了女演員西蘭,這令他在舉發德瑞曼的個人職責與良心之間有了極大的掙扎。甚至到了最後危急關頭,魏斯勒更不惜冒著背叛黨的風險,暗中幫助作家掩護藏匿關鍵證據的打字機,讓德瑞曼能夠順利逃過一劫。
相當有趣而吊詭的是,導演多納斯馬克在《竊聽風暴》拍攝期間,獲得了許多前東德人的協助,讓他得以在當年東德情報局的大樓空間實地拍攝。而唯一拒絕了他拍攝請求的,就是前東德政治犯專屬監獄、現已改為「霍恩施豪森監獄紀念館」(Hohenschönhausen Memorial)的館長胡伯圖斯.柯納博(Hubertus Knabe)。最主要的原因,乃是柯納博認為該劇本內容根本不符合史實。據他所知,回顧整個東德歷史,像衛斯勒這樣「良心發現」而會暗中保護受他監視者的秘密警察,很抱歉,一個都沒有!
▍下篇:

- 1972年6月17日晚上,美國共和黨尼克森總統競選連任期間,涉嫌派人潛入水門大廈民主黨辦公室總部安裝竊聽器遭到逮捕,其後經由秘密線人(代號:深喉嚨)向華盛頓郵報揭露,掀起美國歷來政壇最大醜聞,導致尼克森遭國會彈劾而自行下臺,世稱水門案,同時也是20世紀最著名之違法監聽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