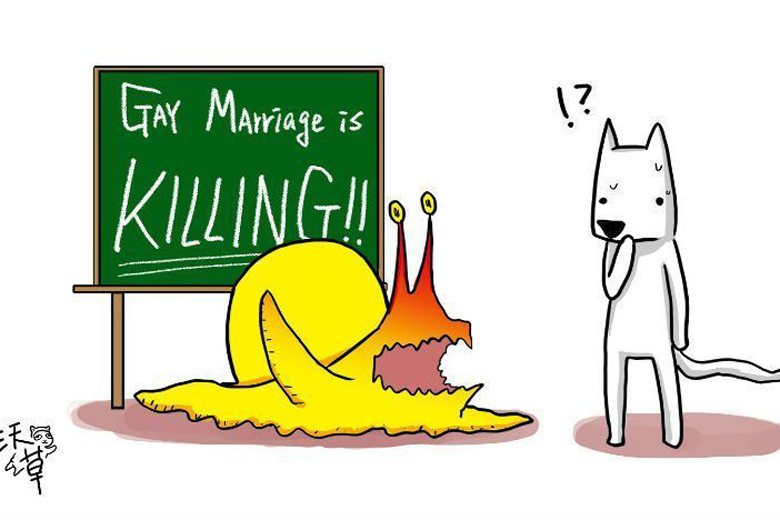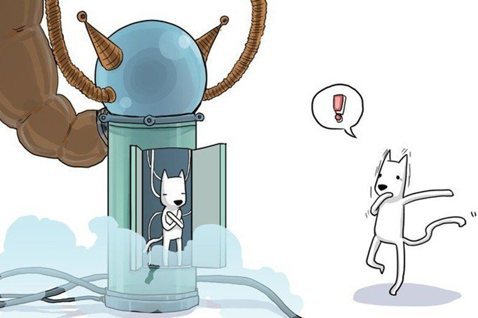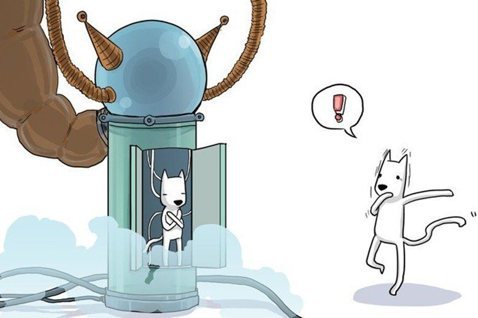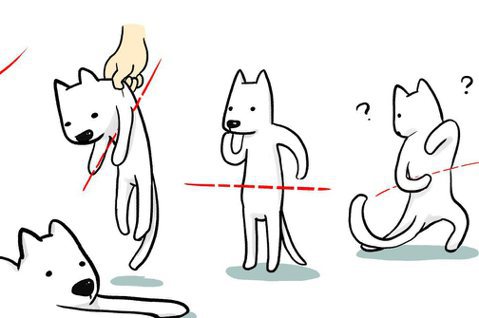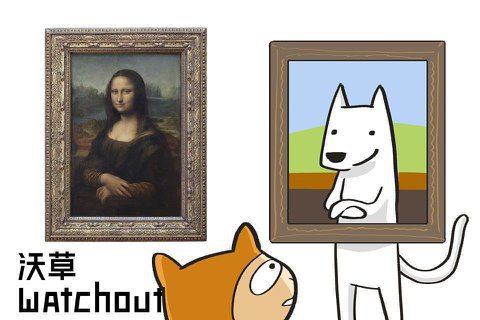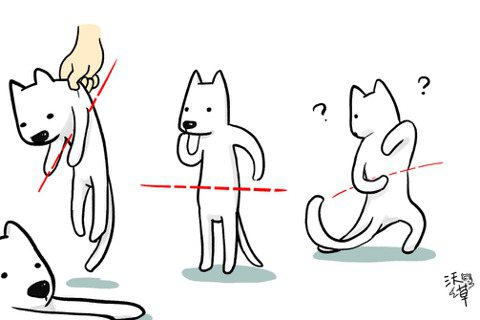賴天恆/我們有可能真誠地為歷史上的不義道歉嗎?

歷史上有許多不義。
日本帝國曾經侵略中國、屠殺中國人。中國國民黨政府曾經侵略台灣、屠殺台灣人。中國各個政權曾經侵略、屠殺周邊各個國家、不同民族。許多政權為過去的不義道歉:1997年英國首相布萊爾為愛爾蘭飢荒向愛爾蘭人道歉;1998年美國總統柯林頓為奴役制度道歉;2008年澳洲總理陸克文向澳洲原住民道歉;2016年台灣總統蔡英文向台灣原住民道歉。而德國亦曾多次為二戰泯滅人性的罪行道歉。
為過去的不義道歉似乎是必須做的:承認犯錯,並承諾以此為基礎建立更好的未來。然而,到底要怎樣理解道歉,哲學上有非常多地方可以談。以下我們將探索一個概念上的小困惑:對於歷史的不義,我們很難「希望歷史上的不義不曾發生」。
希望歷史上的不義不曾發生
樂卓博大學的哲學家湯普森(Janna Thompson)在她2000年的文章〈道歉的悖論〉(The apology paradox)裡,指出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們應該為歷史上的不義道歉;如果我們真誠道歉,就代表我們希望歷史上的不義不曾發生;然而,我們無法希望歷史上的不義不曾發生;因此,我們的道歉最多是虛偽的;然而,我們不應該虛偽地道歉;因此,我們不應該道歉。」1
為什麼會這樣呢?湯普森的想法是這樣的,首先:
1. 我們應該為我們祖先對原住民、黑人、猶太人、愛爾蘭人等惡行道歉。
2. 如果我們真誠地道歉,那我們就對於祖先的所作所為感到遺憾(p. 470)。
3. 如果我們對祖先的所作所為感到遺憾,就代表我們希望他們沒犯下那項過錯(p. 471)。
我們的祖先曾犯下泯滅人性的惡行,這是確定的,沒什麼爭議空間。而我們是祖先的繼承者,雖然祖先犯下惡行不代表我們是壞人,更不代表我們也犯下跟祖先一模一樣的惡行,但是就身份上來說,我們應該道歉。
如果我為自己的過犯道歉,我應該表達「遺憾」。遺憾包括後悔犯錯,以及希望自己沒有犯下這項錯誤。同樣地,如果我們為祖先的惡行道歉,我們同樣地希望他們沒有犯下這項錯誤,我們希望歷史上的不義不曾發生。不論是為自己的過犯道歉,或者為祖先的惡行道歉,如果沒有「遺憾」,沒有希望過錯、不義不曾發生,就是虛偽。
我們無法希望歷史上的不義不曾發生
以上這一切似乎都滿正確的。然而,我們真的有辦法真誠地希望歷史上的不義不曾發生嗎?湯普森認為不太可能。
4. 但如果我們的祖先沒有對原住民、黑人、猶太人、愛爾蘭人犯下惡行,世界的歷史會非常不一樣,而我們大概不會存在(p. 471)。
這點其實不太難想像。若你同意說,只要基因不同,是不同一對的精卵組合而成,就是不同的人,那麼你應該就會同意:若歷史改變,有太多的方式會讓組成我們的精卵不曾相遇。
舉例來說,如果蔣介石沒有被毛澤東打得落荒而逃,我兩邊的祖父、外祖父大概就不會來到台灣;如果蔣介石沒有屠殺台灣人,我的父母多半不會有他們的早年生活;如果台灣仍有固有的原住民王國、傳統領域,那就算我父母相遇,他們婚後的生活也大概會很不一樣。只要有任何的變動(甚至只是晚一秒鐘受孕),生下來的可能就是另一對精卵組合,而不是我。(更不用說,在一些情況下我的父母可能不曾相遇、甚至不曾存在。)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如果漢人沒有屠殺原住民、或者蔣介石沒有屠殺台灣人,我或你(或任何在1949年之後出生的人)存在的可能性到底有多低。(如果你是烙哲學的老讀者,是的,這就是哲學家帕菲特提出的「不同人問題」)
此時我們就得考量:
5.我們當中,多數人大概會很高興活著。我們覺得自己的存在是件好事。也就是說,我們會希望這個世界讓我們得以存在。
6.換句話說,我們的存在(大概)倚賴於我們祖先的所作所為,而我們對那些所做所為無法感到遺憾。這是因為如果那些事情沒有發生,對世界造成的改變(大概)會大到讓我們不存在(p. 471)。
這讓我們必須接受說:
7.因此,我們無法真誠地為祖先的惡行道歉,而我們就不應該道歉。
有沒有搞錯……
當然,這是很荒謬的結論,不道歉似乎是很惡劣的事情。試想,為什麼我國西方那個強大的國家,一天到晚要我國北方那個國家道歉。我國北方那個國家曾經犯下泯滅人性的惡行,不道歉真的很惡劣。
說人無法真誠為歷史的不義道歉,是很荒謬的。但這不代表湯普森的提出的問題荒誕到不值得思考:
如果我們認為某個論述明顯荒謬,但卻說不出它的問題出在哪,或許表示我們自己對某些東西沒想清楚。
湯普森考量了好幾個可能性。舉例來說,有可能道歉不代表「遺憾」,更不代表「希望不曾發生」。湯普森覺得這同樣也很荒謬,如果都不覺得遺憾,不覺得「希望不曾發生」,到底是在道歉什麼?
有些人可能會提議:很簡單,就讓我們同時「希望歷史上的不義不曾發生」以及「希望歷史上的不義發生」吧!至少很多人在道歉時,沒有把前因後果想清楚,只是一方面感到抱歉希望歷史上的不義不曾發生,另一方面慶幸自己得以存在,卻沒有想到自己的存在倚賴於歷史上的不義。然而,我們現在已經把前因後果鋪陳出來了,如果還繼續抱持自相矛盾的信念,可能會讓別人很難理解我們道歉到底在道歉什麼。
另一個可能性是硬吃看似荒謬的結論:不再慶幸自己存在。
湯普森指出許多效益主義者會接受這點,畢竟效益主義者只認為整體來說最大效益才是重點,自己是否應該存在,取決於跟其它可能性的權衡。然而,湯普森認為我們之間大概大多數的人不是鐵桿效益主義者,而且也確確實實慶幸自己的存在。就此而言,此路對我們大多數人大概行不通。(當然,我自己是覺得我們確實應該進一步反省說,我們自己到底有沒有那麼特別、尊貴,以致即便泯滅人性的惡行在歷史上不斷發生,我們仍覺得沒關係。)
湯普森自己則是主張說,或許道歉代表的不是說希望不義不曾發生,而是對於「受惠於不義感到遺憾」。當我們受惠於不義的時候,我們大概會很喜歡享受到的優惠,但是會傾向於希望我們所擁有的並不是來自於不義,而是來自正常的管道。同樣地,或許我們享受自己的存在,但是會傾向於希望自己的存在並不以來於歷史上的不義。
當然,這種想法是否可以理解,似乎還要進一步討論。我們的存在事實上倚賴於歷史上的不義,而如果那些不義不曾發生,到底是需要怎樣的神蹟,我們才可能存在?如果歷史上的不義不曾發生,我們就「不可能存在」,那麼湯普森這種理解方式,似乎也行不通。
受惠於不義
無論如何,我們的存在似乎「受惠」於歷史上的不義。近年政治哲學界有不少「受惠於不義」的討論,2在這邊我無法一一闡述。
然而,我們可以思考一下,即便是「非自願」地「受惠於不義」,我們會因此承擔怎樣的「義務」?應該不是「拋棄優惠」——這等同於要我們自殺——或許我們很難真誠地道歉,那麼就「受惠於不義」來說,我們有可能承擔了相當沈重的「補償義務」。
- 本文主要引用Thompson, J.(2000). The apology paradox.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0(201), 470-475。
- 關於「非自願受惠於不義」,可參考Malmqvist, E. (2013). Taking advantage of injustice.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39(4), 557-580.、Goodin, R. E., & Barry, C. (2014). Benefiting from the Wrongdoing of Others.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31(4), 363-376、Barry, C., & Wiens, D. (2016). Benefiting from wrongdoing and sustaining wrongful harm. Journal of Moral Philosophy, 13(5), 530-552.、Haydar, B., & Øverland, G. (2014). The normative implications of benefiting from injustice.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31(4), 349-362.、Butt, D. (2007). On benefiting from injustice.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37(1), 129-152.、Anwander, N. (2005). Contributing and benefiting Two grounds for duties to the victims of injustice.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01), 39-45.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