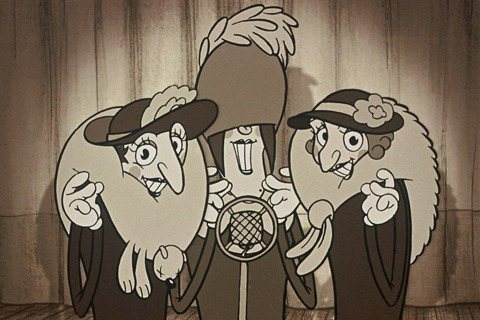從贖罪走向死亡——牟敦芾60年代禁片《跑道終點》

(※ 本文涉及多處劇透,敬請讀者斟酌。)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已在五月四日開幕,國內外許多紀錄片影人帶著他們的作品與台灣觀眾見面。今年的重磅單元「想像式前衛:1960s的電影實驗」宛如在執行「超級任務」,找到多位1960年代影人,在他們影片完成的半個世紀後共聚一堂。TIDF還隨專題推出「台灣切片1960s別冊」,八十頁的冊子囊括了影人訪談、深度分析、從未曝光的珍貴舊照以及未曾公開的書信往來,讀起來興味盎然。尤其是黃貴蓉的專訪,解答了我不少疑惑。
原先我猜想《不敢跟你講》的編劇署名「后方」也許是出品人劉緯文的化名,沒想到「后方」的真實身份卻是黃貴蓉。黃貴蓉之所以擔任編劇,電影開拍後又擔任場記,全力支持牟敦芾完成電影,是因為他們馬上就要結婚。可惜這段婚姻相當短暫,後來以第三者介入告終,黃貴蓉因此沒有參與《跑道終點》的拍攝。
半個世紀之後,在《上山》中重溫黃貴蓉和牟敦芾形影不離的青春美好,或者非常後設地從《不敢跟你講》裡頭正經八百的女老師(歸亞蕾飾)和其桀驁不馴的畫家男友(牟敦芾親自飾演),彼此個性歧異、見解兩極,去猜想黃貴蓉與牟敦芾當時的現實人生——例如片中男方要女方拿掉眼鏡open mind,女方則要男方刮掉滿臉鬍子——不免心生時光難再的百感交集。
我之前已經寫過一篇專文盡訴個人對於《不敢跟你講》的喜愛,不過若要說到牟敦芾生涯最佳,絕對是《跑道終點》。應該說,豈只是牟敦芾創作生涯最好的作品,《跑道終點》在封存四十八年後首度公開(確切原因仍舊未知),我相信看過的觀眾朋友心中的台片影史十佳,將會重新排序。
原因是,這部電影不論是所提出的見解,成熟的技術手法,到美學上強烈的個人風格,皆超越了當時中影或其他隸屬於黨國官方片廠攝製的台灣電影。非但不遜於早些問世的歐陸新浪潮,甚至比晚了十年的台灣新電影更憤怒、更前衛、也更勇敢。如果牟敦芾沒有出走台灣,繼續在台灣拍片,也許會重寫,甚至影響今日的台灣電影也說不定。

詩意地反抗,孤獨的留白
無論是變成「禽獸導演」之前的牟敦芾,或是拍攝虐殺剝削片的牟敦芾,給我的感覺總是極度的憤怒。那種憤怒不是表層的大聲咆哮,也不是疾言厲色的指責,而是一種沉痛暴烈的質問。
牟敦芾在《不敢跟你講》這部片裡,親自扮演一名帶有反叛意識的畫家,這個角色在片中數度提到「威嚴」這個字眼,挑戰威嚴、質疑威嚴、打破威嚴、甚至要與整個中華民族為敵。或許這是現實生活中的牟敦芾,選擇成為一個導演的關鍵原因。
也因此,講述一個敏感男孩與痛改前非的父親重新溝通並和解的《不敢跟你講》,並非擁抱父權;而講述一個純真男孩的罪惡感與贖罪過程的《跑道終點》,也不是要去討論鄉愿的寬恕或是淺薄的原諒。對我來說這兩部片不約而同挖掘出威權體制底下,極其隱微深層的「反抗意識」——大人覺得該好好唸書,大人覺得贖罪行為該適可而止,大人覺得如何如何根本都不重要,自己如何想如何做才是最重要的。
除了反抗意識,《跑道終點》最打動我的原因,莫過於牟敦芾以當時華語電影前所未見的「電影感」,去刻劃滿腔憤怒和反抗意識的原點。原來那出自脆弱敏感的孤獨,是一種接近漫威宇宙的大魔王完成自以為的宇宙大業之後,卻莫名陷入沉思的孤獨。
牟敦芾非常擅長藉由詩意感性的影像構圖,去傳達這樣的孤獨感。例如在《不敢跟你講》片頭打出演職員名單時,主人翁大原側坐,那個由他身體去分隔草原和天空的遠景鏡頭,便暗示了這個男孩的渺小與孤寂,以景喻情的功力令人難以忘懷。《跑道終點》也出現許多將人與自然巧妙合一的完美遠景,比方以俯角拍攝操場跑道,跑道上的永勝在銀幕上只有丁點大,橢圓形跑道那種無路可出的迴圈意象,於是在對比之下顯得更為巨大,定調了此角的悲劇結局。

這次進去永遠都出不來了
《跑道終點》真正的主角是永勝的好友小彤,這男孩的性格跟《不敢跟你講》的大原相當接近。電影的開場是一片漆黑中晃動著的兩道光,光源來自永勝和小彤進入山洞探險時頭上戴的探照燈。不過後來永勝再邀小彤入洞探險時,小彤卻彷彿受詛咒的希臘先知卡珊卓般,小聲說著:「這一次進去永遠都出不來了。」
兩個男孩因此並未走進看不見盡頭的黑暗山洞,他們轉念決定去操場進行一場屬於兩個人的競賽,此舉卻導致了永勝之死。這個轉念,是命運女神對他們開的一次玩笑,引領他們進入更殘酷的命運黑洞,令小彤往後的人生再也走不出來。
黑暗,是《跑道終點》的母題。牟敦芾以非常精彩的場面調度,來表現永勝之死為小彤帶來的人生陰影。永勝死後,滿懷罪惡感的小彤好不容易鼓起勇氣前往永勝家,向永勝的父母說明永勝休克的經過,這場戲的剪接堪稱影史範本等級(片頭演職員名單的剪接欄位打的是牟佳和黃秋貴這兩個名字,不確定牟佳是否為牟敦芾的化名)。
說話的小彤的臉、聆聽的永勝雙親的臉、小彤回憶中筋疲力竭倒臥在小彤面前的永勝那扭曲的神情,隨著小彤說話的語氣起伏,展開一場咄咄逼人,卻也令人心碎的交叉剪接。小彤說到激動之處,臉部特寫幾乎塞滿銀幕,銀幕的其他部份只剩下黑暗,而永勝雙親彷彿不是與小彤對視,反倒更像是望向那個他們缺席、唯有小彤親眼見證的悲劇現場。然後,小彤被永勝的母親趕了出去,他從屋子投射出去的光源中慢慢走出,身影逐漸被闇黑所吞噬。
跑道的盡頭,沒有寬恕,也沒有因為贖罪而出現希望。小彤去永勝的墳前上香,隨後接上一個遠景鏡頭,小彤瘦小的身影孤獨地站立在河邊,對岸灰暗蒼茫,遠方天邊出現一片光亮,然而這光太過稀微短暫,不足以照亮小彤的未來。

從贖罪到走向死亡的黑洞
竭盡所能贖罪的他,以為永勝麵店的開張,可以讓自己重新開始,沒想到永勝母親不經意的那句「要是永勝能看到了那該多好」,終究還是讓他崩潰。回家後又因功課退步而和父親吵架,小彤於是來到永勝墳前,自顧自地說著,他對於世上種種是非黑白充滿困惑,就跟《不敢跟你講》的大原一樣有滿腔的委屈與憤怒,卻同樣無人可以傾訴,無人願意聆聽。所以小彤下定決心放棄一切,他再也不想弄清楚了,便走入那個曾經懼怕的山洞,隱沒在一片黑暗之中。
這是華語電影史上最絕望的一刻,我從來沒有在華語電影中,感受到這麼痛徹心肺的心死狀態。《不敢跟你講》以父子弄清楚講明白彼此和解收場,和《跑道終點》以擁抱死亡作結,猶如牟敦芾掙脫了中華民族的儒家傳統與禮教束縛,針對1960年代嚴密監視的台灣社會所做出的正向與反向結論,兩個結果看似對立,實則是一體兩面、殊途同歸。
我自己喜歡《跑道終點》更多一些,那個瀰漫死亡氣息的謝幕式實在太過魔幻,牟敦芾在此以無比的真誠和無畏的勇氣,展現出創作者細膩敏感又悲情憐憫的一面。走向死亡,不只是遁入黑暗,同時也是對時代最直接的抗議。
《不敢跟你講》跟《跑道終點》這兩部電影,因為種種的時代錯誤,無法正式公映,最終將牟敦芾推向了「另外一種層次的死亡」,逼使他毅然決然走出台灣這個黑洞之島。後來他在香港和中國拍的電影,因為太過病態,為他贏得「禽獸導演」的稱號——或許正是因為他體內部份情感細胞死去了,身為創作者的某種溫度冷卻了。而台灣電影美學的發展,因為牟敦芾的離開,就此少掉一次大幅躍進的機會,必須等到1980年代初期才得見曙光。
(※ 本片將於「第十一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放映,場次為5月12日,放映地點:光點華山電影館,詳參完整場次表。)
▲ 「想像式前衛:1960年代的電影實驗」單元預告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