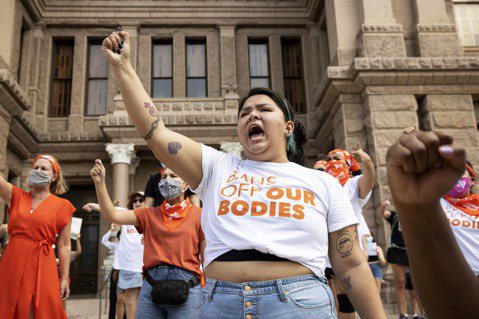許恩恩/一塊失落的女性電影拼圖(三):當《未婚媽媽》遇上《晨曦將至》

▍上篇:
一塊失落的女性電影拼圖(一):遭台灣新浪潮埋沒的《未婚媽媽》▍中篇:
一塊失落的女性電影拼圖(二):四個角度看《未婚媽媽》前衛之處
作為時空條件下的錯置觀眾,我想從去年(2020)在金馬影展看到的《晨曦將至》反推與1980年台灣的《未婚媽媽》對話。
當女人成為母親——成長軌跡的紀錄
這兩部片都以「將照顧小媽媽的身心健康作為最高原則的待產期間照顧機構」為背景,在《晨》之中是「嬰兒接棒」這個組織,影像呈現上以收養的中產階級母親及原生的弱勢少女兩者的故事線平行敘事,在「接棒」處產生交集。雖然這種做法讓節奏變慢且影像時間拉得很長,但也因此傳遞了作者希望並重兩者故事的意識形態,這是在製作上我特別欣賞《晨》之處。
《未》片則側重在三個未婚媽媽的成長與變化,組織是讓小媽媽能夠齊聚的場域,更聚焦在人與人之間的情誼,處理的課題並未像《晨》那麼多,《未》片對於收養小孩的人,只有過一句簡單描述「先生是工程師,太太是音樂教員,結婚十五年一直沒有孩子,兩人身體健康,渴望要孩子。」並未著墨這個角色與情節,不過跟《晨》中收養伴侶的設定,也算相去不遠,都是工作性質上或許相對開明的中產階級。

值得並列評賞的或許是,唯有這種題材才會出現的角色:小媽媽們的「大媽媽」,也就是此類機構的負責人。我曾在部落格撰寫一篇文章,點出了如《未》片「白夫人」角色在《晨》之中的曖昧性,是母親議題之中重要的處理:
《晨曦將至》裡面的收養組織「嬰兒接棒」(ベビーバトン)的創辦人,以慈祥的(生母、養母之外的)「第三個母親」的身份出場。那如救世主一般,使人不安的感覺,實為重要。(光組織名稱就有夠讓人不安了)......從『事情必然沒有這麼美好』的直視不安;到溫暖光線下人們世俗的生日儀式,家庭紀錄片鏡頭式的預告尾聲;到小媽媽重回小島上,看著創辦人一手一手剝掉盆栽裡植物的陳舊老葉 — — 這樣去終結一個片刻的烏托邦的過程,冷靜溫柔。收斂美化及尖銳批判,如末世教主,從容就義。
——〈已經能冷靜溫柔看待那片刻的烏托邦〉部落格《如水回聲》
《晨》中的組織位於一個海上的島,其創辦人在渡船到島上的過程中,為小媽媽披上外套,並且幫小媽媽們在機構內慶生,鼓勵小媽媽們互相扶持,女主角在懷孕後第一次認識到「平安的生產」是重要的事;《未》裡的白夫人則為小媽媽們準備了各種娛樂、醫療、清淨的休閒環境及人生方向上的指點,她說「雖然我不能夠幫你忘掉心底的創傷,因為你身上的孩子每天都提醒你這樣的痛苦,但至少可已給你自由安寧的環境。」兩部片中的大媽媽都是階段性輔助的一種存在。
不過,《晨》中小媽媽的父母便是屬於責罵、為女兒感到羞恥的人物設定,相對地,《未》不但顯得以女兒利益為重,在最後探訪女兒多元成家住處時,也說出「你們又住在一塊,彼此有照應真好。」顯示《未》中將此種機構或小媽媽交集的場域視為一個可以被衍生的生活模式,《晨》之中則除了世代傳統觀念外,更在未交代原因的狀況下讓「嬰兒接棒」機構關閉。實際上,無論是1980年代或現在,這類機構的存在與倒閉,都留給觀眾自行腦補的空間,畢竟墮胎/人工流產議題及生母/養母的倫理議題,至今也仍然是「議題」,這也是為什麼《未》光是題材的選擇上就已經很前衛了。

時代之差,也明顯表現在《未》的其中一幕,出於時代背景,相對於四十年後於日本拍攝的《晨》,《未》顯得更有優勢:當時「懷孕」的醫療化程度較低,因此《未》中的生育環境是直接置於機構之內,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文月在生產時,一群女性焦躁等待孩子出生,每個人都大腹便便,同時有頂著爆炸頭、身著各種時尚服裝的多元樣貌。《晨》之中的小媽媽造型也十分重要,小女主角的好朋友便是披上了朋友的陽剛外套而感覺獲得能量,不過,《晨》並未特別著墨於生育過程,且由於生產還是要到醫院,因此沒有懷孕姐妹們在產房外焦躁等待的情節。
《未》的結尾在忙著照顧小孩、多元另類家庭型態的大合照之中,以及白夫人對小芃說的一席話「雖然我們仍舊有資格享受被愛與愛人,但或多或少是比一般人失去了一些條件,但是別懊惱,幸福是靠我們自己去追求的。」帶有正面樂觀的教育意義,似乎較像面向大社會的觀念之聲。《晨》則細膩於角色的變化歷程與情感細節,用小孩子將兩個媽媽串在一起而能創造同理與同情,溫柔明亮地處理「生」之議題的殘酷性。
幾乎同樣的機構題材,兩片側重之處與處理方式,必然反映了時代規範與國族文化的差異,但重點其實不在「比較」,而是「對話」:我們可以試著想像,四十年前的日本若有這樣的組織,又或者四十年後的現在台灣有這樣的組織,作品又會體現出什麼樣的可能性。

四十年後,想像邱剛健原劇本的《未婚媽媽》
李美彌的三部曲之中,被談論最多的同性戀題材之作《女子學校》,卻也是我從今日看來較為無趣之作,就像是四十年前的《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只是戒嚴時期處理女中內的情愫情誼實屬不易,單單套用了瓊瑤式情節在兩名女性身上,其實已是相當大膽之舉。然而,《晚間新聞》在處理女企業家與其丈夫的張力與情感戲,以及最後被園丁偷襲且欲自殘相殺的張力情節;還有《未婚媽媽》之中三名女性的設定及男角的模糊曖昧感,更是我作為後輩長於解嚴後的觀眾感到驚喜訝異的創作。我認為,這與編劇的角色有相當的關係。林杏鴻〈叫喊開麥拉的女性〉(1999)文中,提到李美彌《未婚媽媽》第一次執導機緣與歷程:
那時候正好未婚媽媽的新聞很熱,而且那時有天主教及基督教的未婚媽媽之家成立,因此,她就請邱剛健編劇,但他的戲劇性太強,亂倫情節出現,新聞局不通過,但他又不肯改劇本,結果又找了孫春華萊編劇,再實際演出時,也修了戲。......第一次送企劃、劇本到新聞局電影科審查時,便以『拜會社會善良風氣』予以退回,後來就把劇本的封面改成《素蘭要出嫁》就准予通過。李美彌藝文界的朋友見宋楚瑜,當時他是新聞局局長,他看了之後,覺得頗具教育意義,因此就准許上檔了。
即使受限於電檢或種種原因,改動後的《未婚媽媽》被視為「僅」是社會議題片,但在觀念與議題皆有所推展的今日,即使劇本受到更動,我們還是可以從《未婚媽媽》當中以三個設定截然不同卻都遭逢不幸的女性設定,以及《晚間新聞》中園丁闖入的情節中,看見被當代認為是前衛藝術家邱剛健的痕跡。

每個時代都有社會議題,也就有「議題電影」,但是什麼樣的片能夠打入當代觀眾的心中,而不只是倡議與說教;又是什麼樣的設定,能夠冠以「前衛」之名,即使過了數十年之後,仍是一部「不僅是議題電影」的價值之作?固然,議題在不同時空的社會中,會因為種種理由而被相對視為是「進步」、「後退」,無法僅從電影創作本位的出發去預示什麼樣的主題才有「前衛」性,如同我對《女子學校》感到無趣之情,自然也是因為同性戀在當代台灣社會已經是自然、受大眾認可的身分。
不過,某些人類社會長存的課題也可能以「議題」的方式承載,或在議題之中試圖拉出更具前瞻性和恆久性課題的層次;除此之外,《未婚媽媽》的某些影像處理方法,在當年也許未必被視為精湛的處理,但在電影工業變革與文化演進之後,我作為年輕一代的觀眾也會有我的盲點與誤讀。這或許也是藝術作品的有趣之處,在本文前半部,我先嘗試盡量將歷史文本梳理盤點,也未必能夠去除掉時代的盲點。不過,觀眾可以有當代的反射性評論,但在脈絡之上(未必能夠在當年脈絡之「內」)進行討論,以作品為本的對話可能性空間應能夠再拓寬。
我們或許能期許一種「往未來走的議題電影」,不是科幻人工智慧題材就叫做「未來」,而是思考哪些議題將以不同形式存在,例如:1980年無法合法進行人工流產的社會裡,小媽媽的處境必然是殘酷艱辛;但在2021年的現在,即使有更多避孕方式,有自主人工流產的選項,小媽媽或是選擇進行流產者,也有其殘酷艱辛之處,也可能有姐妹情誼互相支持的另類關係組合;再過四十年後,避孕、懷孕、流產、生育等課題一樣會存在於人類作為物種持續存在的前提之上,每當思想與規範更往前進,創作與觀看創作的方式也應該並進。

我在文獻回顧的過程中,邊看著戒嚴時期電檢與社會議題的侷限,邊思考著,如果所謂「太過戲劇化的情節、亂倫的情節」在當年除了可能合法被排除退審之外,又或者在議題倡議的角度擔心會模糊焦點、亂開戰場,那麼,四十年的現在,我們就有辦法好好駕馭這樣的題材了嗎?這個問題不僅是丟給創作者,更多是丟回作為觀看與詮釋的人。
我會想像著,如果白夫人也喜歡國全,這種跨年齡的「亂倫」情節出現;如果三個未婚媽媽之間互相有著吃醋曖昧的「同性戀」元素;如果我們還是想要談論以婚姻作為分類方式的「未婚媽媽」,或是衍生到非自願懷孕者、年輕女性的避孕過程或生育抉擇等等題材——我們是否已經可以把當年視為前衛、如今已經在思考與實踐上有較寬廣空間的元素,以一種「好看」的方式說出一則故事,而且與四十年前的《未婚媽媽》一樣,不但增添論述,也淡化某些元素,從技巧上來平衡電影作品作為其中一種呈現形式。
想像現在拍一個未婚媽媽的故事,到了幾十年後看了還是前衛,那會是什麼?身為看片的人,我們期盼或批判著的,是什麼樣的「議題電影」?這些都是我在看完李美彌三部曲,並在爬梳資料、整理思路之後,盤旋於腦內的議題。


▲ 第28屆台灣國際女性影展(點圖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