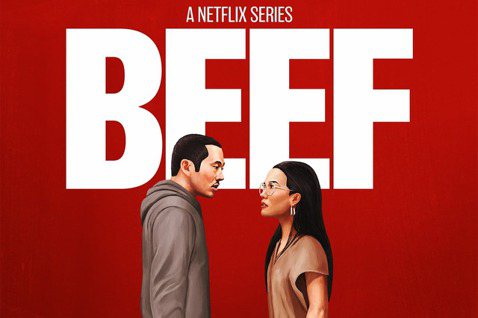《蚵豐村》的出走與返鄉:我們該如何尋找回家的路?

去年某個周一夜晚,台北中山堂的電影放映結束後,觀眾忘情鼓掌好長一段時間,燈光亮起,主創團隊緩緩走向台前,這是台灣電影《蚵豐村》在台北電影節的首映之夜。原以為很快便將正式上映,沒想到這一等,就過了將近一年。有趣的是,這似乎與片中主角的境遇不謀而合,在《蚵豐村》闖蕩數個國際影展之後,終於也回到台灣,回歸這片孕育他的土地。
望向《蚵豐村》的第一版電影預告,二分鐘長的片段沒有任何對話,取而代之的,只有幾段請示神明的保佑,穿插台灣傳統漁村場景和迷幻背景音樂,很快地勾勒出此片與大眾熟悉台灣電影樣貌的區隔。這部海歸新導演的首支電影長片,其實正巧呼應了電影欲探討的命題——出走與返鄉。
「人與空間」的舉世課題
離鄉這件事,似乎總掐住台灣青年咽喉,身處強權大國之間的小島,任何年代的台灣人總對「出走」有著遙望和憧憬,甚至成為一條不得不踏上的路途。島內亦然,從求學到工作打拚,由鄉村移至都市的無數寂寞靈魂,幾乎撐起許多創作裡的核心情感。
於是80年代我們有了《鹿港小鎮》,年輕的羅大佑聲嘶力竭大唱「台北不是我的家」,撫慰多少在霓虹燈間浮沉的游子;於是千禧年後有了《海角七號》開頭那句「我操你媽的台北!」當成功傳奇一次次粉刷人們的都市幻想,那些在繁華邊緣尋不著棲身處的青年,只好被迫迴游。

離家很難,但回鄉之路更艱難。
《蚵豐村》試圖描繪的,就是這麼一位迴游青年盛吉(林禹緒飾)的故事。在台北掙不到多少銀子,反倒淪為大機器中可有可無的小零件,明明是黯然回家,卻被視作光榮返鄉的「大頭家」看待。為了自尊和面子,盛吉只得做做樣子、裝得闊氣,談著那些在都市中不屬於自己的亮麗生活,好像就能不那麼「魯蛇」一些。只是,虛胖話術或許騙得了村民的羨慕眼神,卻瞞不住最了解自身的家人。
出身於嘉義漁村的一戶養蚵人家,他們家仰賴買賣蚵仔過活,原本就是看老天心情吃飯的工作,由於產業沒落、漁村高齡化,此處顯得愈加搖搖欲墜。年輕人在都市失意,卻不願做著沒有前景的漁事,焦慮感膨脹,一天又一天更加格格不入。
不僅如此,世代衝突與溝通不良也同時引爆著。透過祖父孫三代糾結,帶出華人世界中傳統男性的故作堅強,以及傳統與現代、城與鄉,世代與世代之間的難以理解。《蚵豐村》是一篇極具台灣特色的寫實劇,背後核心誠然是考驗著一代又一代「人與空間」的舉世課題。

台灣故事,歐式美學
儘管電影敘說如此本土的題材,但觀眾或能從電影中感受到濃濃的異國風情。電影在配樂、攝影和混音等技術層面,都讓人有前所未有的魔幻感受,例如出現不只一次的巨大濟公佛像,或是融合嗩吶、電子樂與宗教音樂的背景音效,和那些在非海邊場景,卻出現被風拂過的蚵殼聲。台灣傳統漁村頓時披上帶有神祕、魔幻色彩的東歐風情,《蚵豐村》所塑造的衝突與趣味,從敘事到形體皆自成一格。
全片以十六釐米底片拍攝,呼應沙洲揚起的粗礪與沙塵,導演的歐洲經驗如實反映於作品中。技術面上由眾多外國電影人參與,因此我們能看見不同以往的台灣漁村面貌,藉由樂音、畫面與氣氛營造,構築一座魔幻非常的台灣西南沿海村落。
本片導演林龍吟在台就讀政大外交系畢業後,遠赴捷克布拉格影視學院(FAMU)攻讀電影導演研究所,作品曾入選法國坎城影展短片單元、紐約威廉斯堡國際影展競賽單元等國際影展。
即便是新導演,我發現自己第一次接觸他的作品,是在2015年的《遙遠人聲》新聞專題,當時他與記者重返車諾比核災區,製作一連串震撼人心的浸入式體驗報導。回頭來看,當時的車諾比專題,其實也緊扣著類似情結,《遙遠人聲》是被迫離鄉的困惑與無奈;多年後的《蚵豐村》,則是被迫返鄉的別無選擇。

發大財:台灣對成功定義的唯一解
電影有兩位年輕男性角色,除了從城市黯然返鄉的盛吉,另一位就是一直待在鄉村、盛吉的知心好友昆男(陳莘太飾)。相較盛吉父親順明(喜翔飾)承繼父業,終其一生養蚵,年輕人顯然不安於世。於是一個北上打拚,一個成天天馬行空只想出奇制勝,搞出幾個觀光工具和亮眼口號,幻想能就此鹹魚翻身。
片中當兩人走在沙灘上,面前出現的巨大濟公佛像,形成一幅有趣的對比畫面。在灑脫豁然的濟公面前,盛吉與昆男彷彿被塵世困住的肉體,濟公的那抹微笑,除了癲狂,更多了種「我笑他人看不穿」的奇特對望。抑或是片子末端那通巧妙的通話,觀眾似曾相似,片尾反倒回到最初,我們卻都已不再相同。
發財大夢縈繞台灣人世世代代,對於成功的平板想像,讓多少人發瘋似飛蛾撲火。社會氣氛浮躁不安,只好將想望投射於速食口號,宛如寫給現代人讀的童話,然而它們往往不會是真實答案。
《蚵豐村》在平凡的「有家難歸」故事中,側寫台灣現代產業面臨的瓶頸與社會困境:當蚵豐村不再「蚵豐」,留下的人不見得是失敗者,出走的人又有多少能風光歸來?《蚵豐村》不急於給予解答,不貿然定成敗,而是緩緩描繪這群濱海小人物的焦慮與渴望,看他們如何找尋各自生命的出口。